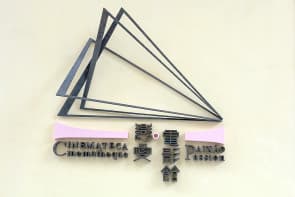每逢周二,傳說中的爛鬼樓會在「論盡媒體」虛擬空間出現,歡迎聚眾圍觀。藝術教育文學創作藝評影評城市議論旅行書寫,凡生活種種與文化連結的,皆可被捕捉定格。在城市金光幻象背後,期望文化與文字逐日沉積,落地生根。未來是浮華還是昇華,城市種種,皆在一念之間。
歡迎投稿,以文字圖像書寫我城。
因應付傳染性極高的武漢肺炎(COVID-19),我們又回到每天都要戴口罩以及擔心買不到口罩的日子。全球口罩荒,口罩已成為各國的戰略物資了,同時將可能是我們以後要長期使用的東西,但現在這種每人每日⋯
「這是一場有我們在其中參與的長遠的演化過程,人類需要思考怎樣與環境共存。」 「疾病、天災都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希望人類可以世代延續下去。」 引起公共衛生危機的新型肺炎(COVID-19),由來自⋯
1. 孩子喜歡的動畫頻道,把冠狀病毒玩成是一場與神的遊戲。「如果人本身就是喪屍,那得到會讓人成為喪屍的病毒其實也不是太恐怖,因為病毒和人類自己相差不遠。我們會覺得恐怖,是因為以為它來自神。神會處⋯
不知名流行病肆虐,全城恐慌,各地政府處理手法尤值得商榷。事情發展得看似迅速,令人措手不及,我還來不及看《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來把裡面的不平等世界和現實作對比——過去在種族屠殺和傳染⋯
作為一名本澳的電影愛好者/影像工作者,戀愛.電影館無疑是筆者最愛流連的藝文空間之一。本人與戀愛.電影館有著極為微妙的緣份:我不僅在這裡跟電影談戀愛;又在這裡跟太太談戀愛;亦在這裡跟太太談電影;同⋯
Break,是破碎,卻也是突破。台灣舞者周書毅,在今年的澳門城市藝穗節中,把《Break & Break! 無用之地》帶來澳門,在路環荔枝碗上演三場,讓作品從台灣延伸至一個更高更闊的層面⋯
打開家中的衣櫃,衣物的款式林林總總,既展示着時尚潮流與衣物主人的個性,也夾雜着回憶——一些與某件衣物有關、或與某件衫裙共同經歷,封塵在心底已久一直未有與人分享,或是美好,也或是悲傷的故事。藝穗節⋯
在12月20日出現的戀愛・電影館「被維修」事件,經過不少電影工作者及文化人的發聲表達關注後,26日上任首天的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即公佈了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註)以作回應: 公佈較詳細的維修原因及⋯
和孩子在戀愛電影館經歷的觀影經驗,現在回想都彌足珍貴。目前電影生命體驗中,以為它是目前珍貴之處,是逐漸實踐觀看的共融環境: 1.嬰幼兒在戀愛電影館開啟電影人生:次子一個多月大的時候,在襁褓中一同⋯
踏高蹺可以變成當代舞?跑酷可以變成當代舞?在藝術的世界,任何事都有萬千可能!將於2020年1月舉行的城市藝穗節設有兩個「穗內有萃」主題行程,其中之一就是以舞蹈為主的《在地》。「因為今年用節的形式⋯
對於我,砌模型是另一種造型藝術。 對於我,砌模型可以使真變假,也可以使假變真。 ——劉以鬯《砌模型》 (節錄) 以上兩句是節錄自已故的香港文學家劉以鬯的散文《砌模型》。劉以鬯生前喜歡砌模型⋯
說到劇場,可能第一時間浮現腦海的,會是台前精彩的演出,可是建構一個完整的劇場,必須依靠台前台後眾人的努力,甚至是不顯眼卻不可或缺的劇場工具。這次筆者訪問到即將於12月底舉行的「Tools B⋯
就在政府各部門為回歸廿周年的大型慶典而費盡心神之時,20日這天同時驚現戀愛・電影館將營運至本月底的消息[1]。這個本地文化地標自2017年開始已策劃過多項高質素的電影專題放映,經營者的用心有目共⋯
《照顧者》是石頭公社剛於周末進行的階段性展演,在改裝為臨時演出空間的排練室內,兩位演員以一張輪椅,配以現場環境的門、窗、柱等,簡單而清晰地呈現了長期病患/長者與照顧者/家屬,共處也是相困於一室的⋯
經過南灣的人都知道,現在的海灣其實不太能稱得上是「灣」。那蒼海有點遠離視線,冷看熱鬧劃破湖面;不太蓊鬱的人工孤島肅立在人工湖泊之中,早被新的鳥群所指認。兩旁安插高低不一的大樓干擾思緒,打擾那試圖⋯
演出結束時,我被一片紅光困罩着,而我只得離開…… 在此時此刻,在澳門舊法院上演這版《此時此刻》可謂巧妙。這作品的場刊不諱言「是次創作得力於兩本重要的時代之作:《一九八四》與《暴政》」,想帶出的訊⋯
日前,本澳建築師呂澤強獲香港「大館-古蹟藝術館」邀請,於館方主辦的首場「大館對談」以「記憶之外-從法國到澳門的建築保育」為題目作公開演講,介紹法國的建築保護歷史與案例,並分享講者在澳門的建築保育⋯
燈光打在舞臺,眼前演員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才發現他們部分是去年石頭公社的《世界和我怎麼樣》,與2016年澳門藝術節中《Disabled Theatre》的演員,於是,各個時間的舞台、他們和我,在腦⋯
我們為何觀看?我們又看到什麼? 是否把一群被認為需要更多「注視」的人群放進劇場,人們便能「看到」他們?或者「注視」和「關注」將會因此提升?何況劇場本身就是一個充滿階級瘡疤的地方。⋯
讀11月12日新鮮出爐的《2009-2019年民生工作總結》、《第三及第四屆政府施政總結》 及 《2019財政年度政府工作總結》,同時香港警察強攻大學校園的影像洗版,完全覺得這兩個相距35分鐘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