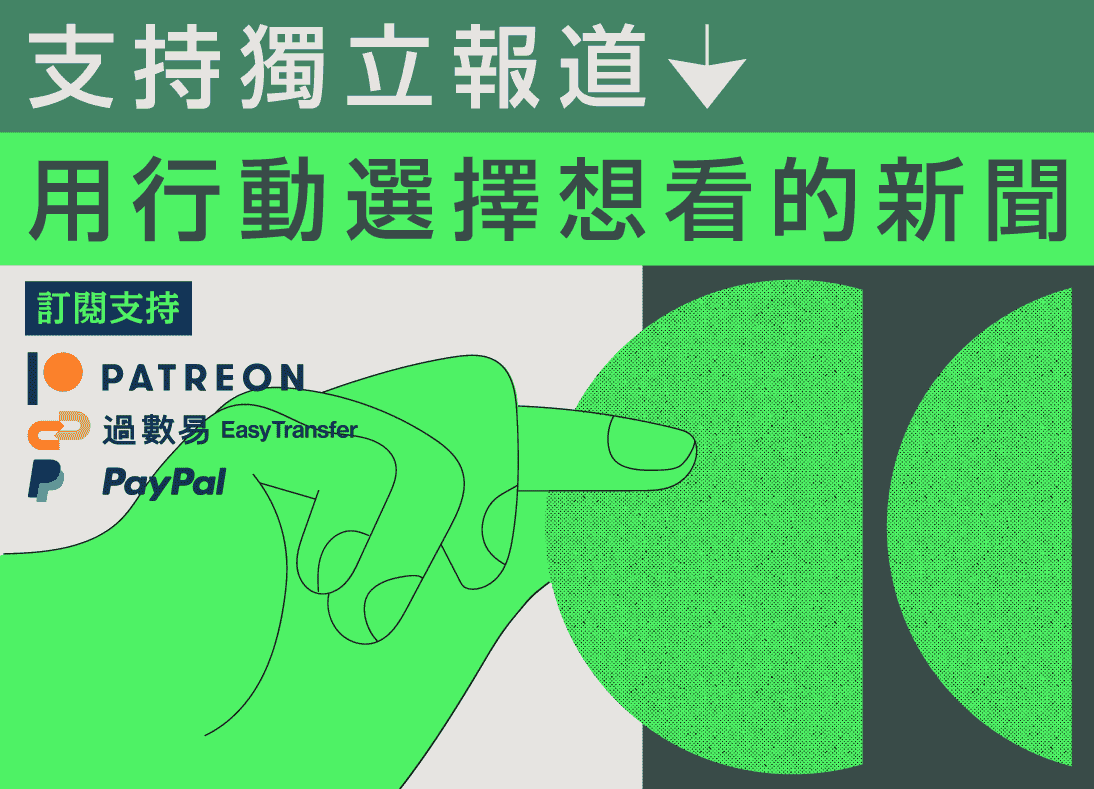朱佑人/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系碩士學位, 畢業作品《亞明的澳門》參加多個影展。九九年完成第二部作品《沉默澳門人我不是》,作品繼續關注澳門人對澳門城市的感受。同年為澳門回歸拍攝了《忘不了, 1999年12月20日》,作品更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
許國明/許國明,別名小鳥,拍板視覺藝術團創團成員,1992年畢業於澳門大學,現職為電影導演、澳門電台〈音樂蒙太奇〉節目主持、iCentre 影視製作課程兼職導師。曾於2002年完成澳門有史以來第一部幕前幕後全由澳門人擔任的長片〈鎗前窗後〉,近年作品有〈夜了又破曉〉、〈堂口故事﹣紙飛機〉,及短片〈壹塊錢〉。
X自十五年前到現在,朱佑人(朱Sir)和許國明(小鳥)每天的生活,幾乎都離不開電影。對他們來說,電影既是夢想,也是一些很實在的工作。
在1994、95年,朱佑人從美國回澳拍攝畢業作品《亞明的澳門》,當時他並沒有想過回來;後因母親病了,來回遊移兩地,直至97年,才決定留下來,這一留,便直至現在。澳門沒有電影的工作怎麼辦?那就自己創造一些工作出來吧。朱佑人留下來後便從零開始,做各種推動電影的工作,搞放映之餘,自己也拍紀錄片,一下子開始熱鬧起來。然後,在98-99年間,成立了電影團體「拍板」,活躍至今,做了許多電影工作坊、放映會,也籌組拍片。
那時候的澳門是怎樣的?
「成長當中,自己是喜歡電影的,但那時沒有參與任何文化活動。我先在台灣讀新聞系,畢業後在台灣工作,然後決定回來蓄錢去美國讀電影,發現那時大部份美國同學都不知道澳門,連香港也不太知道,所以我想用電影來呈現澳門這個地方。那時我為籌拍這部畢業作品,寫了很多信給不同的政府部門,最記得當時文化司(今文化局)的回覆是:拍戲是商業行為,我們只支持藝術活動,而其他申請也沒有回覆。最後我是靠借錢來拍成畢業作品的。這個經歷也讓我對這個城市有更深的體會,覺得值得回來這裡做點事情。但那年頭,真的很難找工作做,回來後有7、8個月沒有工作,去過香港找熟悉的電影人如許鞍華等了解情況,當時香港電影人也生存不易,何況我是澳門人就更難。那是97年,有一些香港回歸題材的電影,於是我就拿過來,與石頭公社一起在綜藝二館,搞了個香港的獨立電影放映活動。」
同一時期,90年代初,小鳥已經想拍電影,但那時條件十分有限,除資源少,還有技術困難,那時未有數碼技術,拍電影還是用菲林,剪接要用特定的機器,澳門沒有。回歸前有段時間小鳥在香港,間中會與同學租用香港藝術中心的剪接室,回到澳門後在TDM工作,數碼影像開始出現,這對影像的處理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使拍攝更普及;小鳥去看了兩次《亞明的澳門》,從而認識了朱佑人,還一同成立了『拍板』。
談到此刻,朱Sir忽然大喊:「係啦,其實今年也是『拍板』成立十五年啊。」竟然這麼湊巧地對題,一個成立十五年的團體,見證著一個地方影像發展十五年,而原來,成立「拍板」的契機竟是與祐漢街市有密切關係。
「回歸前市政廳(今稱民政總署)的文康部裡有幾位活躍的『搞事份子』-大鳥、Erik、Zico、細福等,當時這個部門想在祐漢街市頂樓的社區中心內設置一個剪接室,需要找一個電影團體來運作(那時澳門並沒有),為這事我便和幾個電影發燒友──許國明、鄧耀榮等,成立了『拍板』。我個人其實不想成立團體的,覺得困身。」不過其實一直這樣說的朱Sir,到今天仍未能交棒休息,仍為『拍板』盡心盡力照管著。
一切皆因電腦
「成立拍板後,我們馬上去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買了一台Mac G3,放了在我家,同時市政廳找我們去管理祐漢街市上的剪接室(又是電腦),那時電腦剪接仍屬高科技事物,沒有人會想到這竟設在一個街市的樓上,現在想來仍覺匪夷所思,很有創意,那時推行計劃的人員真的很用心在推動電影。有了這些器材,我便又可以在澳門拍片了。」
那時候好玩啲
十多年前搞這些活動,與現時相比,會有什麼⋯⋯「那時候好玩啲。」還未問完,朱Sir便已衝口而出。當時的人自然會明白,可能也會有相同答案。但這是什麼原因,在當時那麼貧乏的文化環境裡?
「那時很多方面都好玩啲。心理上,初生之犢,什麼都放膽去做,不會考慮太多,好記得那年代還沒有email乜乜乜,我要問波蘭等城市借片來放,我們先發傳真過去,然後深夜再打長途電話,竟然咁就得左!太神奇了!那年頭竟然用這麼簡單的方法就做到件事。那時很多事情都沒人做過,成立初期便遞了不少計劃書給市政廳,合作策劃了些古靈精怪的電影活動,如:搭個大棚在戶外放電影,還在裡面推雪糕車;找香港藝術中心的電影部門來開班教拍片等,網絡逐步建立,認識了許多人。99年時做了《平民百姓錄像回歸夜》,讓沒有拍攝經驗的人也拍些片來表達自己的回歸感受;那時推動電影的活動較多,2001年藝術節中又做了《看得見的城市》,在街上擺放錄像裝置,還首次使用棄置的婆仔屋來做活動,當時真的很多可能。」
「那時很天真,想做就去做。拍片方面,不會考慮太多,在推廣方面,我更賣力。那時比現在好玩的原因,可能還因為那時認識了一班葡國朋友,他們很熱衷於藝術,好玩得很,回想起來,回歸前的文化氣氛是活躍和熱烈的。」
回歸前後,在文化資源上有何不同?
回歸前要向政府申請活動資助是十分困難的事,即使有,金額也相當少。在拍《亞明》時,朱佑人更是一點資助都拿不到,這種狀況與今天很不一樣。
「應該說,資助這回事,某程度也是靠關係的,那時經常聽人說,只要有關係,就可以拿到很多的了。我回來初期因為沒有任何關係,沒有人知道我,拿不到是自然的。當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知道你了,一點點的資助總是會有的。但我們那時的想法是:拿一萬多元已經很開心了;拍電影相對是需要多點資金的,但也不會想可以拿到一百萬這類的大數目,那時我們對怎樣才是『多』並沒有概念,總之有少少錢已很開心了。直到2003年,賭權開放後,政策上出現了「文創」,情況便開始不同了。對電影來說,文創廳成立後是有很大轉變。」即其實也只是近這四、五年,電影的資源才開始有所增加。
「2005年我拍《澳門我是誰》(《堂口故事》前身)時,這是一系列的紀錄片,探討回歸後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變化,結果民政總署有資助而文化局則完全沒有回覆。拍完後我覺得紀錄片可能未必是最適合的,於是就開始構思《堂口故事》,找不同導演以劇情片方式呈現他所住地區的生活故事。就這樣開拍了《堂口故事1》,資金主要來自民署,後來有一點來自澳門基金會。」
拍片資金一直匱乏
98-99年,小鳥拍了一個不太短的短片(50’)叫《一把火》,一聽就知是年少氣盛之作,但小鳥說即使到現在他還是可以拍這樣的片。影片主要對回歸時社會上一致唱好之聲不滿。
「那時完全無錢拍,全靠大家仗義幫忙,有時來了幾個、有時幾十個,多是做戲劇的,台前幕後都有。那時我沒什麼經驗,許沛鋒是男角,很能跟我一起瘋,那時大家都不計較錢,一鼓作氣地去做,只想用影像去表達對當時社會氣氛的不滿。這部片也有在回歸當晚的『平民百姓電影夜』中放映。之後,我又拍了《迷城》(3’),是參與香港進念辦的“video Circle”,在香港科技大學中擺放的錄像裝置。回歸前還拍了黑色諷刺的《狂人》。
回歸後又膽粗粗拍了第一部長片《鎗前窗後》,都是全靠大家不收錢,才可以拍出來,我記得埋單時大概用了3萬元,主要是用於飯錢和租巴士,現在是不可能的事。」那部片得到很多人幫助,朱佑人幫忙打燈,還兼演黑幫大佬,電影放映時,這一幕使所有人笑到顛。「所以那時候真的很好玩。」現在想起,仍很回味。
到2006年,小鳥拍《夜了又破曉》,那次他籌到多一點資金,可以付一點錢給其中一些工作人員,錢雖少但他們並不計較,是義氣幫忙。這部片由Creative Macau 資助了大約6萬多,其餘小鳥出資,最後埋單用了14萬多,拍了廿多天。
小鳥:「現在很難再可以用這麼少錢做到了,就算仍然有不計較的人,但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可以付出,大家都很忙。我又想提高作品質素,需要請熟手又做得好的,一定是找專業的,不能總是像過去那樣做製作。」小鳥開始逐樣數算。以前用菲林或DV拍攝、專門的後期處理等都很貴,現在拍攝和後製都變得簡單了,攝影機便宜質素又好;然而,其它拍攝成本卻高了,如租一間餐廳來拍攝,現在收3000元一天都算合理,以前可能1000都不用。朱佑人補充說,主要是看你對作品的質素要求怎樣。現在很多年青人是團隊式的拍攝方式,尤其在大學及中學裡,如果不太要求質素,很多人也可以用很低成本拍片。
從草根走向專業
朱佑人認為這些情況正好說明了澳門的影像正在發展。自文化中心出現後,每年均辦影像的推動活動,增加了拍片的人。當拍片的機會多了,拍片的水準自會提高,各方面都希望做得好些。城市的影像發展了,個人的考慮多了,在劇本上、拍攝上會花更多時間去鑽研,因此拍得慢;當整個製作都走向專業化時,很多事情不能再是免費的形式,製作方式也會很不一樣,加上百物騰貴,因此在資金上,需要籌募得更充足才能拍攝;各種因素的影響都較前多了,使拍片變得沒有以前那麼容易。
可以這樣說,祐漢街市時期的草根式手作生產時代,是開心和充滿熱情的。隨著影像逐漸發展,從街頭放映走入文化中心,代表了電影製作邁向專業,也反映今天的影像其實是更多元的。兩人都認同對電影人來說,那種草根式生產是很好的體驗,但一個地方的影像不能總是停留在那種模式裡,作為城市及個人,均需不斷面對挑戰。
影像與城市變遷對話
澳門的影像發展與城市變遷是相互連結的,使人能看到影像對城市的作用。朱佑人提到,讓他感受很深的,是自2003年賭權開放後,城市開始急速轉變,之後幾年交來文化中心「錄像新勢力」的作品,有不少都談及城市的急速轉變,透露出作者在以影像來尋找城市認同的想法。
「有一位只有二十出頭的年青人的紀錄片《澳門的水源》(劉善恆2008/29’13”),是從水源方面來找澳門的根;有作品拍《兩公里外的花園》(丘靜,趙偉業,2009/32’)說的是路環; 葡人義來(Eloy)拍了《350米》,紀錄關前街那一帶的生活。突然在那幾年裡,多了很多這種尋根式的紀錄片,通過展示從前的美好,來找回個人的城市認同。當初要籌拍《堂口故事1》和《2》 也都因此而引發。」
《堂口故事》 起初叫做《堂區故事》,由五位導演各拍一個堂區的故事,有趣的是,片拍出來後,各人的故事不約而同都透出對昔日澳門的懷緬。澳門有不少影像作品其實都與城市變遷有很大關聯,始終影像紀錄的功能之一就是與城市對話。
文創的出現扭轉局面
朱佑人說:「回歸後,除了城市變遷影響了電影,另一個大的影響就是『文創』 的出現,把整個局面都扭轉了。」對電影人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現在很多公司都想搞電影,電影是要有整個產業鏈的連結才能成事的,造就了很多商機,這樣的發展是回歸前我們想像不到的。在影像的質素仍未扎根時,卻要追求生產的量,還要打進某些市場中,我不知道這會否太急進?但這與城市急速發展的步伐是一致的,站在文化藝術的角度,這樣的影像發展的市場轉向好像太快了。但詭異的是,電影本身除藝術外,從一開始亦是商業行為,它的發展與市場、與經濟本身是連結的。」
離地小品多了
小鳥同樣比較關注電影的質素問題。「回歸前的文化氣氛比較自由和活躍的,批判性的作品也較多。回歸至今,電影拍攝技術上無疑是進步了不少,但影片在題材和內涵上,則沒有太大創新,多了小品式題材,主題比較離地的年青人作品,或者是受港台劇的影響較多吧,甚至有些故事我覺得不會在澳門發生,不知是否與現時創作人對社會的敏感度不足有關。
影像教育還未能普及
在影像教育上,澳門一直沒有電影學院、大學沒有電影系,小鳥在icenter教一些短期課程,課程本身也是偏向技術的,但他會跟學生強調理論,分析影像手法。「其實每種技術,都有一套理論在背後。」
朱佑人曾在一些中學教授影像拍攝工作坊,也有在理工學院內任教。「現在藝術活動的參與年齡層是普及了,如果澳門多了人去接觸藝術,也會多了能從事不同崗位的電影人,燈光、美指、攝影等,都需要人才,當這個城市的電影開始受到重視的時候,其他藝術範疇的人也可以在電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可以發展,不一定只重視培養導演或演員。所以影像教育應是包括整個視藝教育,從小學、中學就要開始進行,影像欣賞也很重要,好多創作都是從『欣賞』開始的,而現在澳門的影像欣賞方面還沒有較有系統的培養,就算拍板放電影也只是零星地進行,現在看片的機會是多了,網上已有太多選擇,但卻缺乏有系統地幫助學生認識影像的教育。」
籌集資金渠道仍然狹隘
除了文化中心的「澳門製造」,每年大約收到六、七十部作品,主要是短片和紀錄片居多,長片除文化局的長片資助計劃外,還有文化局曾組織過類似電影創投會的活動,但未必有很大幫助,畢竟外地對澳門題材的電影會有多大興趣呢?即使在社會資源豐盛的今天,如要拍一部電影長片,仍然是相當不容易的。申請資金的渠道好像多了,如長片資助計劃可以有百多萬資助去拍長片,今年有十多人申請,但只接納4位。競爭的人明年可能更多,多了渠道,但也多了申請者。而文創基金好像又跟拍電影不是太大關係,對電影人來說機會應該很微。
與其他發展中城市比較,澳門電影人對於尋找資金一直有著很大困難,包括澳門與外地,外地的資金也對澳門電影所知十分有限。兩人都認為電影發展不應靠政府資助,目前資金來源過於單一,但問題是澳門仍然沒有私人機構、沒有其他商業資源會支持電影。藝術創作應向世界發展,有人用Kickstarter 進行網上集資,或像影意志發起「民間影像集資計劃」等方式來拍片。
朱佑人笑說: 「以前拍《亞明的澳門》已經做過了,那時是借了錢不用還。現在澳門的私人企業看來好像有機會,但未敲到門。」
小鳥: 「我的電影《似是故人來》到現在都籌集不到資金,或者我要先放在一邊,再寫另一個簡單的劇本,先以草根的方式去把它拍出來。」目前拍板已拍好的《堂口故事3》也同樣出現資金困難的情況,雖然有文化局和澳門基金會的資助,但因整個製作是複雜的,所以後製部份現在已沒有錢進行,要靠自己貼錢去做。朱佑人說,「拍板」不是要做拍戲的機構,只是藉這部片來測試,這次更多澳門人參與,攝影、調色等後製都是澳門人做,唯一混音是在台灣做的,與之前的製作很不同。
朱佑人說:「如果大部份導演都可以自己找到資源去拍片時,『拍板』可以做其他形式的電影工作,如推動影像教育、欣賞等,拍板的角色可能就是彌補現時的需要和不足,在我們能力以內進行工作。」
訪問進行了3個多小時,還意猶未盡,面前這兩位,仍是一如最初,只要關於電影,便永遠都有說不完的話題,露出似乎永不疲憊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