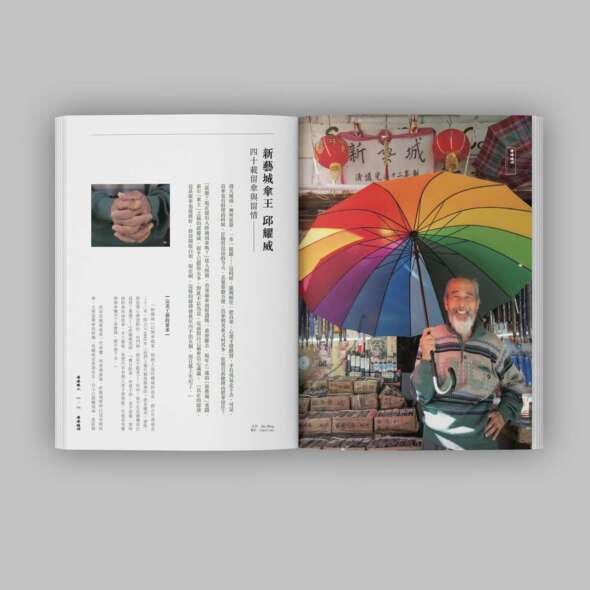握著剛付印完成的個人詩集,不過是樣刊,手就抖震得自以為是金馬獎最佳女優桂綸鎂,波亮波亮,花枝亂顫。拎到廣州書墟北京路225會場,這裡收集了各種最小單位的革命,眾多獨立出版品擠在自己的搖搖椅上,它們在此,對抗著甚麼,等待甚麼,懷抱的又是哪個初衷。
我是一個正在路上的人,不是成敗的個案,不求立功立名或變成瞬間永恆和誰的惟一,對於把作品結集成冊的事情,一點都不積極,不過卻非常在意生活在當下的每個狀態,或許,這也是促成後來走向獨立出版這條路的原因。從集資,到後來編輯、圖像、裝禎協力,這些瑣碎運動的時刻,創作的來路反而更加清晰,也不至於讓我離開現實太遠。
在這些過程之中,我才明白創作的價值對我來說,原來是作為各種行動的載體,而出版就是一個讓文字佚失的過程,我只能留下行動的可能,而非逼迫閱讀在消費行為中產生。易感、暴怒,傾斜與妥協、給予和收藏、流動與穩定、柔軟和剛硬的部分同時存在我的身體,身為不被邊界限定的現代女性,性別特徵被刻意消除,角色界定模糊且多元,獨立出版,正符合了渴望一個毫無雜質、單純放置自我而非其他聲音的絕對空間。
沿梯上三樓,福州《Homeland 家園》雜誌主編許靈怡正談著這個團隊,以製作書籍的態度,完成一本地域雜誌的探寫與編輯。我一邊聽著這些醇潤和緩的在地故事,並好奇本土性怎麼在主流媒體之外突顯出來的同時,另一場座談正在進行,樓上有些聲音。鍾適芳在樓上,泰雅族人正唱著自己的歌,帶來司馬庫斯孩子的風雨。座談結束,我看到一個女孩還在席上流眼淚,後來的每一場,我都能看到她認真地穿梭其中。在四樓,你可以遇見副本製作或其他獨立刊物,以最簡潔的方式,付印質量極好的作品。
回到澳門,台灣設計師小爽寄來報價單,我的出版計劃仍有數十萬新台幣的缺口,為了進入這個「無中生有」之境,我們焦頭爛額地構想接下來的行動,好擔心。我記起書墟裡誰的聲音:你懷抱的不是擔心,那是一顆名為用的心。有一群人正用心,完成一場場小小的革命。
孩子以食指戳點另一隻手心,用獨有的手語告訴媽媽他沒了餅乾,呀!原來在行動以前,我從不知自己一無所有。還怕甚麼?現在我歡喜樂觀,體會出時間倒數,生如夏花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