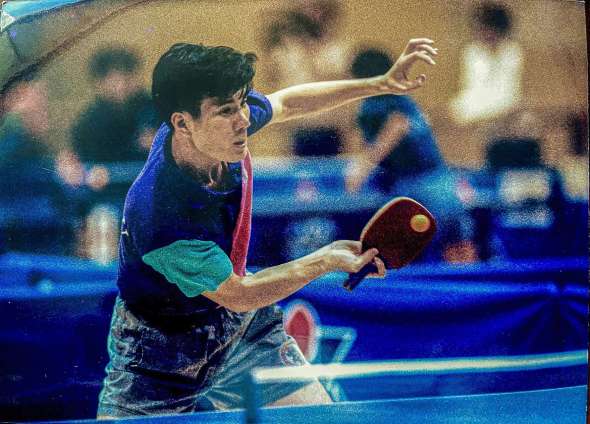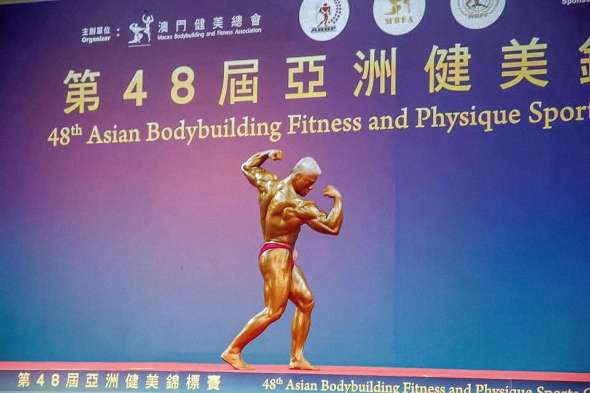防疫三年多,澳門特區政府終於在今年二月底宣佈放寬室內佩戴口罩的措施,乘坐交通工具和進入醫療機構、院舍則須戴口罩。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視口罩為生活必需品,似忘了澳門並沒有一直實施「口罩令」,甚至視為理所當然。但有沒有想過這些防疫措施對於聾人來說,卻如行刑一樣?疫情過後他們的生活真的回復「正常」?抑或仍要逆境前行,與疫前無異?
鍾婉汶(Candy)曾試過在街上拉下口罩用唇語和朋友溝通,卻遭受路人白眼。「我係聾人,我先天聽唔到嘢,聽力程度105至107分貝,戴助聽器43至50分貝。」惟走在街上,沒人會留意到她聽不到。
訪問期間,Candy亦表示,相對被稱為聽障人士,自己更接受聾人二字。
多數聾人都會使用WhatsApp或WeChat,與一般人無異。與記者見面前,Candy透過通訊軟件打字溝通。訪問時,她更多的時候是以唇語發聲、表情及手語來表達所想,遇上某些特別字眼就再以紙筆或電話寫下來。

沒戴助聽器,Candy會完全聽不到聲音,戴助聽器後「好多嘢都聽到,但未必會聽到人哋講乜就係咁」。
接不到的電話等於接不住的機會
Candy自小與健聽的家人用唇語溝通,曾到啟聰中心學發音,習得的詞彙都是廣東話,儘管說話時發音和咬字不太清晰,大致上仍可按語境意會內容。Candy在巴坡沙中葡小學由幼稚園K1讀到K3,當時只有她一個聽不到,不能理解上課內容,老師便建議她轉到協同特殊教育學校讀小一。「我讀小一得三位同學,加上我咋!」
Candy表示,自己在那時才開始接觸其他聾人,當時的同學已經用手語溝通,得自己才剛起步學手語。想起過往返學經歷,她不禁皺眉反一反白眼,搖搖頭兩手攤開以示無奈。
Candy自詡醒目,可惜的是,對接受正規教育的聾人一般所要求文化知識相對較低。
「外國有聾人明星、模特兒、警察、醫生,最近大陸還有中國首位聾人律師譚婷。」不過,澳門特殊教育水平的不足,讓聾人在求職時困難重重;即使找到工作,在職場上亦難以向上流動。
Candy表示,接不到電話是最大的問題,「對方知道你聽唔到電話,就唔會請你。」部分聾人求職面試可能需要傳譯,而找傳譯員的責任大多數卻落在聾人身上。如有需要,是可以向服務機構申請,見工、學車都是免費,而某些特殊情況下申請傳譯員則需要付費。如非必要,不少聾人寧可省卻麻煩。
中五畢業後,Candy第一份在化妝城做文職,然後又轉到酒店工作,每日只有不停地「執file」,沉悶無比。後來她在公營機構上班四年多,同事都願意跟她溝通,甚至學打手語。
輾轉間,Candy到主流學校裡任職教學助理,此乃緣於銀娛基金會在2018年推出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先導計劃」。在現時澳門的融合教育制度下,聽障兒童須入讀主流學校的「融合教室」,Candy會與健聽老師一同為學生提供手語及口語的雙語教學。

Candy以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表達句子,即使不懂手語也能作基本溝通。
到公共部門辦手續 人員手足無措
Candy:需簡單紙筆即可溝通
聾人學習如何適應社會,尋找方式與外界交流,然而,社會還沒學習如何與聾人溝通。Candy曾到公共部門辦手續,她向前台職員表示自己聽不到,對方卻露出驚訝表情,竟不知如何是好,還找同事求救。
雖然大多數情況下,聾人只需簡單紙筆即可溝通,但生活上總有例外,如快遞慣常以電話溝確認,她便需要找同事或朋友代為接聽才能收貨。有聾人朋友會在手機外賣應用程式中備註,但她並無這樣做,反而是習慣直接取外賣,「試過速遞員打畀我,我就傳訊畀佢」。

疫情期間,同時戴上助聽器和口罩讓Candy的耳朵叫苦連連,去年七月政府更有佩戴KN95口罩的指引,令需要讀唇的她極為不便。
不只隔著一部電話的距離
在主流社會的「調教」下,Candy早已培養獨立個性,搵屋、搵工、學車、識朋友等。她表示,聾人同樣經歷健聽人士相似的人生,只溝通上需要花多點時間而已。「學車第一堂有傳譯員陪同,之後就冇喇。」
有著教聾人經驗的學車師傅指手劃腳下,Candy成功考牌。如近視者需佩戴眼鏡一樣,聾人在佩戴助聽器下聽到50分貝以上的聲音,一樣可以考取駕駛執照。時刻掛著豐富的表情的她擺出一副自信的樣子,指自己的觀察力和專注力比一般人都強。
現時愈多愈多公共部門設立無障礙服務,如「視像警報裝置」、「視像通話系統」和「手語視像翻譯」等,文化場所如某些大型藝術展覽可掃描二維看文字導賞,部分劇場演出也有提供視形傳譯。
Candy打字寫字速度飛快,今天年輕的聾人只要有智能電話,彈指間便解決到許多溝通障礙,但聾人與主流社會仍然有著隔閡,也並非「全民手語」便能一刀切化解問題。聽力受損程度不同的聾人對手語的理解能力不一,手語的詞彙量亦不足以應付更艱澀和複雜的概念,Candy舉例,如看新聞節目的手語傳譯,對她來說看字幕反而容易明白,疫情期間也是透過網上的文字資訊去了解各項措施。

聾人有時需要戴透明口罩讓人讀唇,比起一般政府口罩才八蚊十個,這款口罩較為昂貴,Candy曾在疫情期間佩戴,現在已不需要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手語係我母語。」Candy雖如此說,但這套語言在主流社會中卻是一種弱勢,對話間的誤譯令聾人推向更為不平等的景況,尤其是在口罩底下更為明顯。
本澳現時愈來愈多公共部門設立無障礙服務,如「視像警報裝置」、「視像通話系統」和「手語視像翻譯」等,文化場所如某些大型藝術展覽可掃描二維看文字導賞,部分劇場演出也有提供視形傳譯,這些舉措的實施似乎能為聾人生活上提供便利、促她/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現實上真如此?
去年香港有出版社出版《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一書,以手語譯者的角度書寫香港手語歷史及聾人社群的點滴;亦有媒體專題《看不見的說話》追蹤多個個聾人/弱聽個案,揭露了聾人在傳譯制度下遭受的不公。反之在澳門,手語等文化仍不普及,亦甚少人關心聾人們的處境。
後記:沒被記錄下來的聲音
過往訪問前都會提醒受訪者,記者需錄音記下內容,這次因沒有完整對話而沒被錄下來,反倒更多的是用肢體語言和文字溝通。與Candy交談期間才發現我忽略了一些細節,例如,等對方看著你,你才開口說話、說話時口部動作誇張一點,句子中刪去「㗎」、「囉」與「喎」等語氣助詞等。
後來,我用文字問了Candy許多問題,希望她再作補充,才發現之前訪談中原來有許多我理解錯誤的地方。
訪問中Candy曾說,在餐廳點菜遇上侍應落錯單,有時她將錯就錯就算了。但對說過的話,她還是很著緊,亦很有耐心地作出指正。
捉緊話語權是重要的,可是說話有否被聽見甚至被錯誤傳譯卻是另一回事,尤其在聾人的世界裡。事實上,由於障礙聾人聽不見別人,然而社會上許多人卻選擇忽略別人的聲音,故隔閡一直存在,只是疫情把問題暴露出來。這正正提醒著我們:生活中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將錯就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