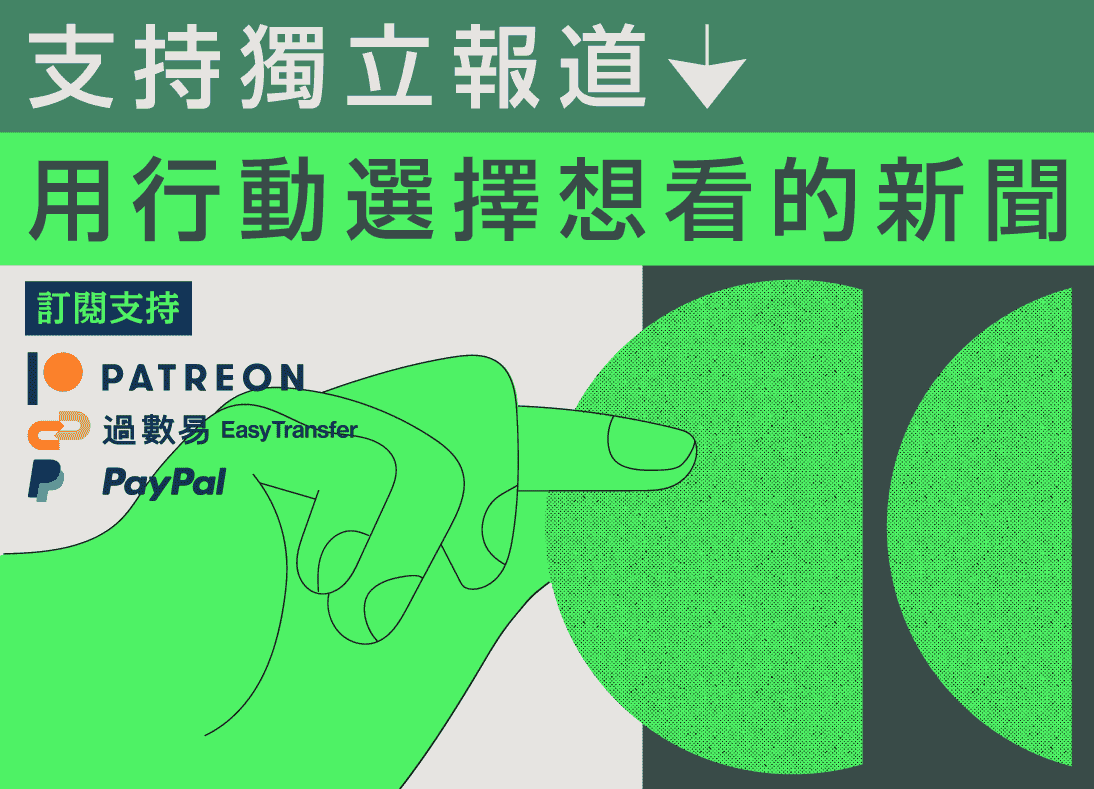自從藝穗節(Fringe)一詞在1947年出現,用以指稱英國「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外圍群聚的表演節目後,演出數量、題材、形式……統統不限制的「愛丁堡藝穗節」,逐漸從藝術節的周邊活動躍升為城市重要的觀光資產,不只是藝術節的綴錦,更是城市的綴錦,當然,也成了全球城市爭相舉辦藝穗節的參照目標。
這段關於藝穗節的歷史,是我在澳門「藝穗節」看了十一個展演後回臺查詢始知的。說來慚愧,在臺北看「藝穗節」時,我從沒認真想過臺北為什麼需要「藝穗節」?理由大概有二:每年「文建會」(與後來的「文化部」)都徵選團隊去國外參加「藝穗節」,當時臺灣並無「藝穗節」,出現一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其次,「臺北藝穗節」打一開始就屬性清晰,報名沒有任何條件限制,主辦方盡力媒合表演團隊與場地,讓「臺北藝穗節」成為一年一度的表演大拼盤,想看意想不到的生猛創意、不怕踩地雷的觀眾,都可以盡量嘗鮮。
我一直以為「藝穗節」不分地域,大抵就是這麼回事,直到看了「澳門藝穗節」。這是我的第一次,是「澳門藝穗節」的第十七次。我一共看了十一場演出,其中兩場名稱相同、表演場地和內容完全不同。駐留澳門期間,和當地、臺、港其他評論人經常在演出相遇,經過閒聊討論後,大致勾勒出這屆「藝穗節」的特色主要有二:
首先是跨國合作的作品共十二個,在全數二十個展演中(不含工作坊)比例過半。跨國者,包括臺灣、中國、葡萄牙、伊朗等,其中又以和臺灣共製或澳門團隊以製作角色邀臺灣作品演出的六個作品居數量之冠。
第二個鮮明特色──不,不是逾三分之二的演出在非劇場空間表演,近年流行的「現地創作」(Site-specific performance)早就是「澳門藝穗節」或許多在地團隊的演出慣例(雖然即使是相對制式的劇場空間,其實也就是閒置的「舊法院大樓」和入駐工業大廈的「曉角實驗室」劇場)。是觀眾互動、參與、浸潤──這個當紅劇場趨勢的說法眾多,一言蔽之在邀請觀眾跳出過往被動、靜態的觀賞行為,以(不僅是觀看的)行動投入演出中,構成演出的主要內容。這類表演就我歸納有十個:《我老豆揸巴士》、《流浪兔》、《裂隙—城市中的身體表演》、《身體感官系列—碰而不見、倒行激思》、《可以睡覺》、《愛情遺物拍賣會》、《日常編舞》、《白兔子、紅兔子》、《兩個轆.四圍碌》。

《流浪兔》,劇照由文化局提供
就我所知,跨國合作是主辦單位在徵選節目時提出的建議方向。由於給予經費較純粹本地製作高,加上澳門劇場工作者多曾在臺灣就學、有臺灣劇場人際網絡,最終導向此次臺灣共製演出多的結果。至於為何跨國?合作共製將為澳門劇場帶來怎樣的刺激和影響?由於我非長期觀察澳門劇場生態者,就把這個問句拋給澳門本地劇場人與評論人去擾動生態池。
我的提問面向聚焦於此:此次為數眾多的互動、參與式展演,劇場創作者如何想像、設計觀眾在表演中的非傳統行動?這些非傳統行動達到怎樣的目的和效果?這些提問最後也將匯於一流:倘若觀眾的動態投入參與是此次「藝穗節」表演主流,劇場藝術家和「藝穗節」主辦方對「觀眾」的想像範圍及於何處?
2002年,草創階段的「藝穗節」曾提出「全城舞台,生活藝術」的概念,「將整個節慶的表演舞台概念放於全城,所有表演強調與地點(site or city)整合,以突出澳門小城的風貌,並激發居民的好奇心、慾望、創意」(註:轉引自《慢走澳門》,頁17),重提舊事是我不得不注意到,儘管「藝穗節」十七屆以來早已滲透澳門許多公共空間,為何城市居民的好奇心、慾望、創意似乎仍然淡薄?以觀賞人次來說,或因演出形式而限制少量觀眾參與,同時卻也發生了場地附近居民抗議演出擾鄰事件。當觀眾介入表演已成潮流,被視為城市綴錦的「藝穗節」,有沒有可能順流而行,開展出一種藝術與市民觀眾的深度對話關係?
我試著用自己參與的六個演出為例,簡要談談它們各自創造的觀眾動態,這樣的互動狀態對演出作品有何效應,又投射出劇場藝術與觀眾的何種關係。
《我老豆揸巴士》這個表演幾乎全程在巴士中進行,觀眾坐在巴士內,由四位表演者(包含專業與素人演員)以語言和照片、車票、文件等物件輔助,向觀眾呈現澳門巴士的大歷史與主要表演者的父親擔任司機的小歷史,最後則是身為女兒的表演者自訴工作經驗,疊合父親的司機工作,借工作者的位移經驗投射澳門城市空間的滄海桑田與人事變遷。
由於對話或獨白是主要的表演手段,形式和內容安排,包括觀眾偶爾的回應,常讓我有聆聽導遊介紹景點之感,雖然增添親切感和生活感,卻不免困惑:除了挪用導覽形式與扮演,引觀眾也投身乘客角色外,在移動巴士內進行的演出還有哪些可能?特別是窗外變換不斷的風景即可能觸動觀眾/乘客腦內上演自己的地景回憶,從而切斷與車內演出的連結時,這趟傾向懷舊的旅程,是否註定只能停留在抒情憶舊的層次,而無法藉由藝術性的轉化或異化,讓觀眾陪同表演者一起鑽探大歷史或小歷史的深處,強化移動或旅程的精神意義?
《流浪兔》標榜藝術療癒而非表演,在「氹仔圖書館」的童書區進行。每次演出觀眾╱被治療者只有一位,報名後隨穿著兔子裝共演的創作者一同在開放空間中靜默行動,最終完成創作者宣稱的療程。作為沒參與演出的觀眾,我和其他人一起或遠或近地圍觀兩名「表演者」在童書區移動,有時白兔拿紅線示意出演觀眾繫綁,有時觀眾在白兔暗示下移動椅子或坐在椅上。從頭到尾都有一位攝影師手持鏡頭近距離拍攝他們倆。
我對這場表演最大的困惑是:創作者如何想像其他觀眾的參與(主要是圍觀)對這場「療程」和置身其中那位觀眾的影響?儘管他宣稱這不是一場表演而是療癒,並在該場演出後提到「療癒不一定要在私密的空間,有些人在公共空間也能達到療癒」,但當其他在場觀眾蓄意「觀看」時,場上被治療的觀眾如何在無所不在的觀看中安置自己?他如何界定被觀看的自己是不是在扮演?而扮演和療癒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當療效僅能由接受者內部感知所確認,療程則暴露在公眾以「觀賞藝穗節表演」為名的凝視下,卻又宣稱不是表演,那它的目的是什麼?
《裂隙—城市中的身體表演Ⅰ、Ⅲ》同名演出在三地進行,內容個個不同。我觀賞的是「群隊街市」的第一場與「何東圖書館」的最末場,至於引發擾鄰抗議的大三巴場次則錯過。
四位國籍不同的合作藝術家在「群隊街市」以一大型塑料布片在路中央進行動態雕塑式的肢體表演。塑料布是澳門攤位拿來遮蔽擋雨天的常用物件,可以察覺藝術家借常民生活媒材來觸發連結或對話,可惜肢體表達的抽象性在人來人往的市場街上只能製造奇觀,引起短暫佇留,而無法與這個環境的人事景物有更多一層連結或對話。
作為這場演出的觀眾,我對周圍其他街市觀眾的好奇心強過表演本身,甚至和一名經過買菜、好奇為什麼這裡有表演的菲律賓婦人有段短暫交談。她問這是舞蹈嗎?我說可以這麼說。但是沒有音樂呢她說,接著自問自答為什麼沒有音樂還能視之為舞蹈,因為表演者動作自有其節奏韻律。但為什麼在這裡演出呢?我答這是「藝穗節」的一部分,在城市各地都有這類表演。她點點頭,說了聲是免費的呢,就掉頭離開了。
第三場「何東圖書館」的表演,四名藝術家各據角落,要觀眾分別尋訪。我分別在入口座位區進行一場宛如療癒的與內在對話儀式、和芬蘭創作者口頭討論「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的差異、戴上耳機與第三位創作者在花園散步定點觀賞圖書館四圍風景、最後聽創作者抗議原先要做的演出被圖書館以擾鄰為由拒絕,並要我自行決定要不要以「想像」參與那場本該存在的表演。
對我而言,兩個表演的問題是一樣的。創作者進入空間,聲稱他們做了田野調查,要求觀眾以觀看或投身體驗參與表演,但供我深入城市空間紋理皺摺的「裂隙」到底存在於何處?以「何東圖書館」為例,四組創作者若非試圖以身體立即轉化眼見的景觀,就是停留在「自然風景提供療癒」或「圖書館是知識場所」的表面層次而要求觀眾共同完成那淺嚐輒止的空間經驗,恕我說,還真小看觀眾對場所的認知,以為他們只停留在和創作者相同的、宛若路人觀光客的層次上。當藝術介入空間,卻只帶來觀光客一般的浮光掠影印象,我們究竟為何而介入?更別提即使忽視場所周遭居民被迫成為演出風景的一部分,他們也首先是觀眾,如何與觀眾協商甚至共謀一場深入城市裂隙的展演,我認為是嘗試做這類演出的創作者不能迴避的現實問題。
身體感官系列:《碰而不見、倒行激思》這個系列是同一組葡萄牙藝術家的作品,《碰而不見》在「舊法院」一樓白色展廳進行,《倒行激思》則在戶外馬路上展開。我認為兩個作品的交集,在於通過觀眾的參與和行動探索當群體構成一個系統(system),如何藉由感官體驗凝聚關係?這關係會為個體帶來什麼制約或慣性?
我參與的《倒行激思》場次是黃昏時刻於南灣湖景馬路上,一群人倒退行走半小時。行動和遊戲規則非常簡單,形同一個「路上觀察學」式的實驗,然而當身體的使用方式改變,連帶感官接收訊息的慣習也產生變化,這條路上的行人不算多,但是道路障礙物不少,被迫放慢的腳步對應眼前開展的城市風景,讓這半小時不顯漫長。當所有人依藝術家指示面對南灣湖靜思,一架多人划舟快速橫過眾人眼前,身體與時間相互作用的緩急快慢以非常戲劇性的方式對立,讓這個執行簡單但概念可繁複延伸的展演留下頗富興味的餘韻。

《碰而不見》,劇照由文化局提供
《碰而不見》讓眾人背對而坐,從頭到尾盯著投影幕打出的英文念誦,雖然同樣是簡單的概念,設計與執行卻是觸礁較多的。文本隱隱浮現背對兩組人的關係敘事,但基本上是平緩的,雖然簡單的詞彙在形、音、義的推衍變化下呈現詩的質地與意趣,對非英語母語的觀眾卻不見得能即時掌握用聲音「玩詩」的概念,如此一來,現場操作語言的趣味大為降低,而觀眾要不要繼續加入群體的遊戲,或是以身在其中的方式挑釁設計者的制約,這層關於群體系統的認同問題也因觀眾失去耐性而難以開展。
《可以睡覺》在原先作為樂團辦公室的「饒宗頤學藝館」內上演。在入口Check- In後,觀眾化身為旅客入住旅館,隨後依住房分組,在旅館人員的指示下玩起Room Service──由其他房間客人擲骰子決定服務內容的團康遊戲。說團康並不為過,諸如「擁抱三分鐘」、「按摩」、「說枕邊故事」、「擦指甲油」等服務內容,多是以參與者彼此親近接觸為目的,我以為針對三十歲以下習於數位社交的年輕族群,與陌生人近身體驗、共同扮演是難得的,從某個角度來說,這非常「劇場」。但強調當下與感官同在的劇場除了「體驗」還能提供什麼?
當(遊)戲末了,眾人集中到一小房間玩起投擲抽獎的另一遊戲,也人人有獎地抱回耳塞、眼罩、枕頭、熱可可、泡麵等熬夜或助眠小物時,所有人顯然樂在其中,卻也不約而同地在結束後選擇離開「旅館」不願留宿。無人選擇「可以睡覺」的展演,雖緣於返家方便、留宿卻要忍耐各項簡陋不便(這裡終究是閒置空間而非旅館),卻也反映了兩道難題:當為觀眾設計的體驗無法進行到最後,以體驗為號召的展演是成功抑或失敗?其二,從創作團隊編纂的(虛擬)澳門旅館指南能讀出「可以睡覺」隱含以身體的私密行為侵佔公共空間、對原有場域氛圍提出翻轉或顛覆的概念,但現場展演或因製作層面等限制,只能以扮演、團康遊戲讓觀眾蜻蜓點水地體驗「佇留公共空間」,更具批判性的身體參與在關鍵時刻則退場缺席,不能不說是巨大的遺憾。
「今天,我們正處於觀看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個人從被動而純粹反覆的狀態轉移到由市場力量指派給他的最低限度的行動……於此,我們被召喚成為展演的臨時演員。」
——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
綜觀我所參與的這幾場展演,創作者為觀眾與劇場之間設計了哪些動詞?聆聽。凝視。遊覽。接受療癒。散步。討論。朗誦。與另一人身接觸互動。睡眠。玩耍。扮演……動詞一如商場貨架上的物品可以無限延伸,但這些可化約為「體驗」二字的動詞,對觀眾而言除了是可在一場藝術節慶中消費換取的娛樂項目外,還能是什麼?對創作者來說,在藝術節慶提供展演,將不同族群、階層的觀眾從靜態變為動態的構成要素,將會如何牽制或開展劇場創作的美學、功能和社會角色,從而與藝術節慶的原初意義──社群儀式──重新對話?於是最終,我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城市如澳門需要「藝穗節」?這是屬於誰、召喚誰動態(文化局╱劇場藝術家╱觀光客╱市民──單選或複選?)的「藝穗節」?
這篇文章以一串提問起,作為一個外來的觀眾和局外的觀察人,我因不願冒進武斷而拋出更多問句。能說的是:當觀眾的動能越發彰顯越見強大,它必然具備社會動能,足以提昇劇場藝術的公共性。但我以為,能同時將這股動能導引出更具藝術性的表達,是未來真正考驗創作者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