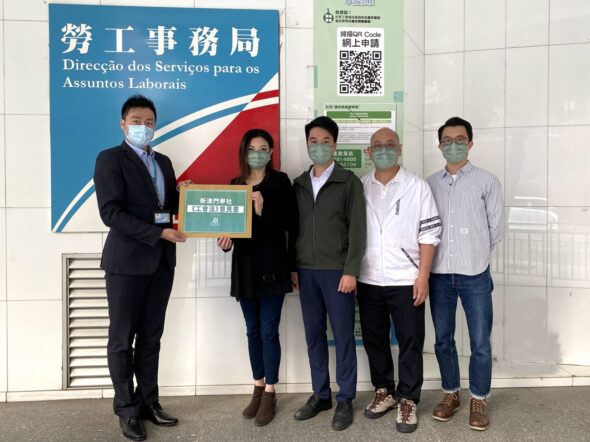「每花多一日爭拗,等於浪費多一日。好日子唔會好長,有地方、有固定資源,現在還不做工作,將來歷史對我們的評價只會是,這班人只係識鬥,不是做該做的事。」
新澳門學社經歷成立23年來最嚴竣的危機,新舊派分裂,陰謀論不斷,令親者痛仇者快。在風雨飄搖的一刻,副理事長鄭明軒從台大休學回澳重新掌舵,幾乎同一時間「澳門社區發展新動力」成立,新舊派各自歸邊,基本格局已定。外界觀望新舵主如何收拾殘局,力挽狂瀾,而他亦給出了清晰的答案:槍頭一致對外,停止內耗。
「學社存在的每一天都應該是服務市民。就算政見上、手法上分歧再大,跟貪腐者、傷害澳門人利益的官商比,夠那些差異大嗎?如果所謂新舊派有甚麼不協調,花在爭拗、爾虞我詐、抹黑的精神和時間已經是完全不相稱。」
從最激烈的社會行動,到最基礎的公民教育學社都要去推,要做的事太多人太少,鄭明軒直言已沒有時間再搞「宮廷鬥爭」。在他看來,學社23年來未有擴大社區基層組織,這是未能衝破的局限也是將來的「共業」,無分新舊,大家只是用各自方式朝共同目標進發。
上任一星期,訪談中,最常掛在新理事長口邊的是「危機感」和「迫切性」。
「眼前工作,第一是做好自己角色,證明自己勝任;第二,如果說年青人主政後爭取到學社獨立人格,那現在便是考驗這獨立人格的社會認受性。」
在學社年青梯隊中,鄭明軒向來以口才和頭腦見稱,但以往多是擔任副手和智囊角色,特別是近年赴台升學逐步淡出第一線。如今擔起大旗對內要重新整合力量、對外重塑路線和政團形象,面對角色轉變和挑戰,鄭明軒不忘先自嘲一番:
「我是這樣跟家人說的,如果不難搞、順風順水的話未必輪到我;如果有利可圖、豐衣足食,應該有好多叻仔去做。當是給自己推動力,如果太順、一切都有既定計劃,可能對鄭明軒來說可以做的不多。」
「有一套電影我很喜歡,女主角說合約得一年,當自己只有一年命。我也當這段時間是為社會服務的最後機會,有甚麼是想為社會去做,不做會後悔的,就在這時間盡力去做吧。至於之後的人事轉變,學社會否仍然是一個由議員和社團互相配合的組織,無人會知道。既然現在有架構、有戰友和一些資源,落在我手上不可浪費。」
決心撿起燙手山竽,不少人期待鄭明軒「認真落場拼一次」,更多的是冷眼旁觀。「那要考驗大家對我的睇法,可能長年都無人當鄭明軒是一回事,那有兩種涵義:一是不會驚鄭明軒,另一種可能是根本不會放此人在眼內。這也可以是好處,如果學社內無人視我為既得利益的威脅,那可能會推展到更多合作機會,或者可以舒緩一下矛盾。如果有人認為我係『流』既,那我要更努力證明能夠帶學社朝著既定方向前進,還有很多工作去做。現在我是完全開放,歡迎各種各樣的合作機會。」
學社與「良心」
近年新澳門學社理事長「頭戴幾頂帽」,有時以「澳門良心」或「開放澳門協會」名義發起行動,受到不少老一輩支持者質疑,新世代也覺得納悶:核心人物來來去去也是那幾個,只是換了招牌有咩意思?
本身也是「良心」成員,曾在去年八月「民間公投」被捕的鄭明軒承認「換帽」並不討好,但澳門的政治板塊單一,即使理念相近的群體也有意見相左和矛盾的時候,按議題嚴重性和受眾接受程度有所分工、將行動升級,有現實需要。
「 將澳門的政治光譜拉開來看,中間民生派到保守立場有好多人,中間到開放、以至極端的一邊非常空白,能持續有組織、有動員能力的來來去去就那幾個。很多時變成我們要戴很多頂帽,好似扮演不同角色,這樣反而唔討好。其實我們想做的是,按照湯醫生(湯家耀) 的說法是社區發展原則,每個不同群體都有自己發聲的能力或他們的代言人,這樣帶出社會議題的效率、反應都會較好,動員過程也會容易很多。現在每遇到一個議題、有重大危機,要從頭做動員的工作,可能大家都不知要怎樣做,也缺乏跟社區的聯繫,當然這是我們自身的局限,23年來都沒法擴大社區基層組織,這是整個學社不分新舊的『共業』,所以要花很多精力去做整合。」
去年6月學社換屆後,理事會已完成世代更替,由年青人掌政,基本不存在行動是否過激的分歧,鄭明軒坦白的說,「良心」不會消失,但他們會更小心處理好分工。「人們對學社和『良心』的期待不一樣,我們即使在這些組織都有主導權,但仍要做好Market Segment (市場劃分) 。不代表我們做甚麼都可以,反而要更仔細摸索不同受眾的感受。自由不代表可以隨心所欲,你有選擇的權力,但亦代表後果是好是壞完全由你去承擔,無得抵賴。」
「現在市民自己爭取權益的能力有提升,但相對其他地方仍然是很初階。有問題他們不知怎樣發聲,想發聲又驚,搵你又驚俾你抽水,澳門人總是有很多考慮。我們並非『包辦代言』,也希望跟對方一起成長,大家一起去推,要考慮可能有人需要不同的行動模式,從溫和到激烈。」
兩年後一場硬仗
開門見山再問兩年後的選戰部署,出隊?前鋒人選?鄭明軒直呼:太早了吧!
三十出頭,鄭明軒已經有三次代表學社參選的經驗,但每一次都是排在後面,俗語說是「幫人抬轎」。他說,個人對選舉不會有幻想,現在亦然。但作為一個參政團體,爭取將年青人求變的聲音帶入議會是肯定的,也有實際作用。即使現在議會是被間選官委把持大多數的「鳥籠民主」,在未能打破這格局前,暫時仍只能在這框架下推動民主參與。
儘管澳門公民社會發展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冷靜分析,鄭明軒坦言形勢一點也不樂觀,年青世代參選要數夠七千票,拿到立法會入場券比九○年代更難。 「 時空環境不一樣。吊詭的是,當年社會封閉得多,但知識分子的尺度反而比現在開放,對批評鴨涌河以北,對討論澳門的未來,相對而言不像現在有那麼多顧忌。當時民主派的路線與保守派反差鮮明,現在很多因素已改變。知識份子基本不敢得罪鴨涌河以北,很多人擺出一副很開明的樣子,但不敢觸及問題的本質。保守派亦拿了開明的外衣,那我們跟其他人特別是一些民生政策上兩者拉不開距離。我們的決心和奉獻不比當年少,但壓力也比當時更大。」
在和諧社會底下,社運若行得太前,「良心」模式被指劍走偏鋒「不理性」,大多數人未必接受;原來「學社」模式無突破,來來去去遞信、開記招又會被看成是因循守舊,暮氣沉沉。行出來被吐槽是抽水,企係後面無人知你係乜水,被問到如何突破現在的瓶頸,鄭明軒直言有兩難。
「大家說不需要有領袖、有光環,但到選舉時的期望就不一樣。最好是一個完人,家庭美滿,事業有成,最好是中產、會跑步,形象很健康。所謂開放陣型的年青人要在議會爭取到一個突破位,這個face要很靚,本身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參選的是完人,面面俱到、形象很好,又要求代表年青人的要出位、要發圍。以前做來做去也是這些,最好有年青人帶來突破、要有新思維,那怎可能做到這些又唔得罪人?這是兩組完全矛盾的要求,希望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但選舉是很殘酷也是公平的,選民是否投給你,不能再想太多,這已是後話。前面盡力去做,到最後這些人適合放在街頭還是議會,由市民來決定吧。」
後記:奉召歸隊
如果說,這是學社最壞的時代,那你這位理事長手上還有甚麼好牌?
「我是學社歷史上第一位不帶薪全職理事長!」一副不正不經的樣子少有的很快認真起來:「 這對家庭來說是任性的決定,要多謝我女朋友和家人支持。如果現在不這樣做,到幾年之後再返來,環境可能已經唔同晒。別人已經在為下一屆盤算,有一種要爭取時間的迫切感。」
中途休學不覺得可惜嗎?
「讀國際關係本身是興趣,學政治本身就是為搞政治服務,但我不喜歡八卦周刊封面一樣的宮廷鬥爭。現在外界睇政府『剝花生』既位係,那可能是前後兩任特首之間的角力,但我在乎的是,政府如何跟市民互動,讓公眾看到政府在做甚麼,官員如何說服市民,這才是有建設性的。派系鬥爭可能帶來一時的好處,又鬥倒一位庸官,但不會從根本上帶來一個開放的政府,不會令市民更關心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