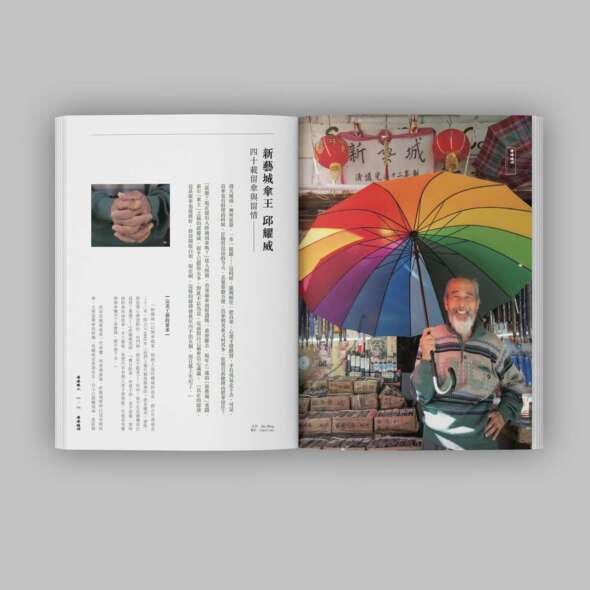二〇二〇年七月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香港的獨立書店如雨後春筍,由原先十多間,增至二〇二三年的三十多間,差不多每個月也有書店開張,深水埗大南街至少有三間獨立書店。香港仍然翻書的書迷不多,真的可以容納這麼多獨立書店?
現時獨立書店,已不只是一間「書店」。「書店」可以作為一個小眾的空間、社區連結的平台,甚至是一個參與型的傳媒實驗,而這個載體也可以在餐廳收鋪後變身成「書店」。
傳媒的伸延空間「留下書舍」
留下來做好公民教育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最大型網媒《立場新聞》的總編輯與董事先後被捕,資產被即時凍結,《立場新聞》無奈停運。不到半年,前《立場新聞》記者Kris Lau與兩位前記者在太子唐樓開辦「留下書舍」,開業初期行「會員制」,定期舉辦實體活動。開鋪一年半,「留下書舍」聯同其他獨立書店辦Podcast「獨毒讀不如眾讀讀」。其後,「留下書舍」開展「留白」計劃,以網媒方式做社區專題。
一間樓上的小書店,在網絡與實體空間開枝散葉。這棵新種的小樹能抵上《港區國安法》吹來急風勁雨?

逢周一休息以外, 周五留下書舍營業至凌晨四時,貫徹書店宗旨「睇多啲書、圍多啲爐」。關震海攝
出版、書店界也清楚,在過去兩年間書店舉辦的講座,警方多次聲稱「接到線報,懷疑在書店有可疑人物或事情」,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進入書店,並抄下所有讀者的身份證,在業界已造成一定的恐慌。這些事有些被報道,有些書店老闆選擇低調處理。
「留下書舍」亦是其中一間曾被警方調查的書店,Kris坦言有段時間感到恐懼,不知甚麼時候會「出事」,與其他股東經常猜「紅線」,惟每次也猜錯:當你以為危險,每次也安然無恙;你以為安全的議題,例如說緬甸議題,便有食環署職員上門警告,Kris對於「紅線」已沒有想太多。「今日要『收我皮』,真的好簡單,不需動用政治的法例,已經可以要一間店鋪收鋪,我們沒有任何反抗的空間。」Kris慨嘆道。
「記者聚腳點」 變成多元空間
在過去兩年,香港不但書店如雨後春筍,新開的獨立媒體一樣是一間接一間,法庭新聞有《法庭線》、《庭刊》;做即時、專題有《集誌社》,獨媒漸漸組織化,各有角色、崗位。「留下書舍」除了替傳媒、傳媒人提供一個平台,它也漸漸伸延成為一個「參與型」傳媒,在社交媒體的「傘」下創立「留白」,探討深水埗重建問題。另一方面亦邀請不同講者到書店辦講座,例如港台多元性向文化節目《自己人》被腰斬後,便請主持人梁兆輝到「留下書舍」開講。「留下書舍」已延伸至一個流動的媒體、小眾與社區討論平台,在這裏可以聽到非主流的聲音。

門外貼上「留下」書法,霸氣十足。關震海攝
拉門推入「留下書舍」,收銀櫃旁鑲起一張又一張《蘋果》歷年珍貴的頭版報道,一陣報紙味。Kris稱這裡除了入政經、社會的新書,新聞記者著寫的書籍一定是主打,漸漸已成為獨媒與獨立記者的一個平台。
他又舉例說,如不定期印刷的《庭刊》,九月創刊號選擇在「留下書舍」作首發書店。書店亦安排創辦人陳珏明分享有血有淚的新聞故事,以及目前經營媒體的困境。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下,一些難以在社交媒體分享的事,「留下書舍」也給予平台,讓讀者聽到多元的聲音。
Kris指,當初辦「留下書舍」,「只是純粹不想《立場》消失,想做個『記者聚腳點』,也是『姣婆守唔到寡』而已。」
一步一步走來,Kris沒有想過「留下書舍」漸漸變成一個參與型的線上傳媒。香港標誌性的公共討論空間之一《城市論壇》也被港台取消之後,其公眾便散落在不同的書店,令書店的活動不再局限於「新書發佈」,而是一個狹縫中看得見彼此的空間。
希望改變「不蝕不賺」的狀態
意念十足的「留下書舍」,可以走多遠?「留下書舍」跟很多獨立書店一樣,處於一個「不蝕不賺」的狀態。三位股東為生計出外打全職或兼職,書店則靠辦活動、賣書的營利維持基本開支。
Kris不諱言,這個生態並不健康,他曾經試過賣自家製的產品,營利又不夠維生,始終香港移民潮未止,支持者移民了便不會回來。
經營書店,多番掙扎,Kris與其他股東仍在努力扭轉「不蝕不賺」的狀態。

留下書舍主打新聞人出版的書籍,但Kris坦言香港人閱讀人口不多,需要靠辦活動賺錢。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流動書架 一個人也可以做的書房
──黑夜書房
疫情後香港未能「復常」,只要在尖沙咀逛一圈,仍然吉鋪處處,就算港府如何說「搞活搞旺」飲食、零售業,過去的八、九月依然未止結業潮,很多老闆紛紛稱香港開關後生意比疫情前更慘淡。港人阿傅疫情間移居日本兩年,在日本「小試牛刀」開格仔書店,吸收經驗回港後與餐廳合作,晚上租場辦流動的「黑夜書房」,既擺放自己心儀的書籍,也舉辦社區講座,在大埔拉近街坊的距離。
到神保町取經
阿傅於二〇二一年初到日本生活,日本正值新冠肆虐的時期,社區人流少,反而令社區的格仔書店活躍起來。日本有書店老闆為了減少讀者聚集,將書店轉為自助買書,亦有些書店轉型格仔書店。
疫情間,日本著名的書評網站ALL REVIEWS 在書店朝聖地神保町地鋪開格仔書店,吸引書評人租書架向讀者介紹新書,而阿傅便租了一格書格,專賣香港書。
日本賣書的經驗啟發阿傅:書店其實亦可以只開一個格仔。
二〇二三年阿傅回港,一直心癢癢想開書店。年初太子閱讀書店結業前,阿傅曾一度與店主接洽「頂鋪」,礙於租金,阿傅不敢貿然開鋪。於是她回到自己的社區大埔,跟一間店鋪商討,租用店鋪關門的時間,在租金高昂的香港尋找一點空間。
最後,她找到寶湖花園商場的V.W Vegan Cafe 素食店合作,在晚上八時營業時間之後辦講座、新書發佈會。

港人阿傅晚上租場辦流動的「黑夜書房」,既擺放自己心儀的書籍,也舉辦社區講座,在大埔拉近街坊的距離。
社區需要互動的空間
「我想要做的空間,是一個人也可以做到。只要我覺得好玩、有意義就可以。」不論在日本、在香港,這也是阿傅辦書店的宗旨。
阿傅說,經過這幾年開書店的經驗,自己更著重書店的流動性,書店可以不固定一個地方,反而變成一種理念,去哪裏辦也可以。「當初『黑夜書房』想做一個深宵食堂,因食肆不想晚上開火爐,但也不要緊,黑夜中大家以知識、書本點亮空間也可以。」

阿傅(右一)在「黑夜書房」舉辦的社區活動,吸引街坊出席,講座之後可以在場買書。圖片受訪者提供
阿傅在餐廳放了兩、三個書架,書架內均是有關「黑暗」的書本,食客可以即場買書,也可以幫襯食肆叫餐飲,書店與餐廳彼此是「雙贏」的。
阿傅曾在「黑夜書房」辦本地農夫分享離島梅窩人自給自足的實戰經驗。這種跨區的街坊經驗,阿傅認為是香港需要的,「大埔區是比較少有這種與讀者、街坊互動、連結的書店。」本地出版社辦新書簡介會,目前主要靠「流動」的空間辦講座。阿傅邀請著有新書《獨行的距離》的獨立記者李雨夢,到「黑夜書房」分享在亞洲採訪民主運動的經驗,這是社區比較少有的公民社會講座。

「黑夜書房」固定的駐場書架放在寶湖花園商場的V.W Vegan Cafe 素食店。
積極關注社區事務的阿傅在八月首次舉辦的活動,順理成章延續她一直想做的「山寨社區學堂」。講座更邀請到在油麻地、從事社區工作十年的「樂地文化」創辦人孔維樂到「書房」。
孔維樂一直積極記錄區內故事,出版地區報《油。樂園》,漸漸由紙本的記錄蛻變成公民教育,阿傅希望孔維樂在社區累積的經驗可以在其他地區播種。
阿傅指,香港經濟低迷,大埔有食肆早上賣漢堡包、晚上做串燒,經營者也已開始計劃「轉型」空間,因此「黑夜書房」仍在聯絡有機會合作的食店,將講座擴散到不同地方。
阿傅認為,香港未來將會走日本二線城市的軌跡,不同的社區也會轉型,將空間變成多功能的地方,而書店、閱讀只是話匣子,最終的功能還是社區互動與連結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