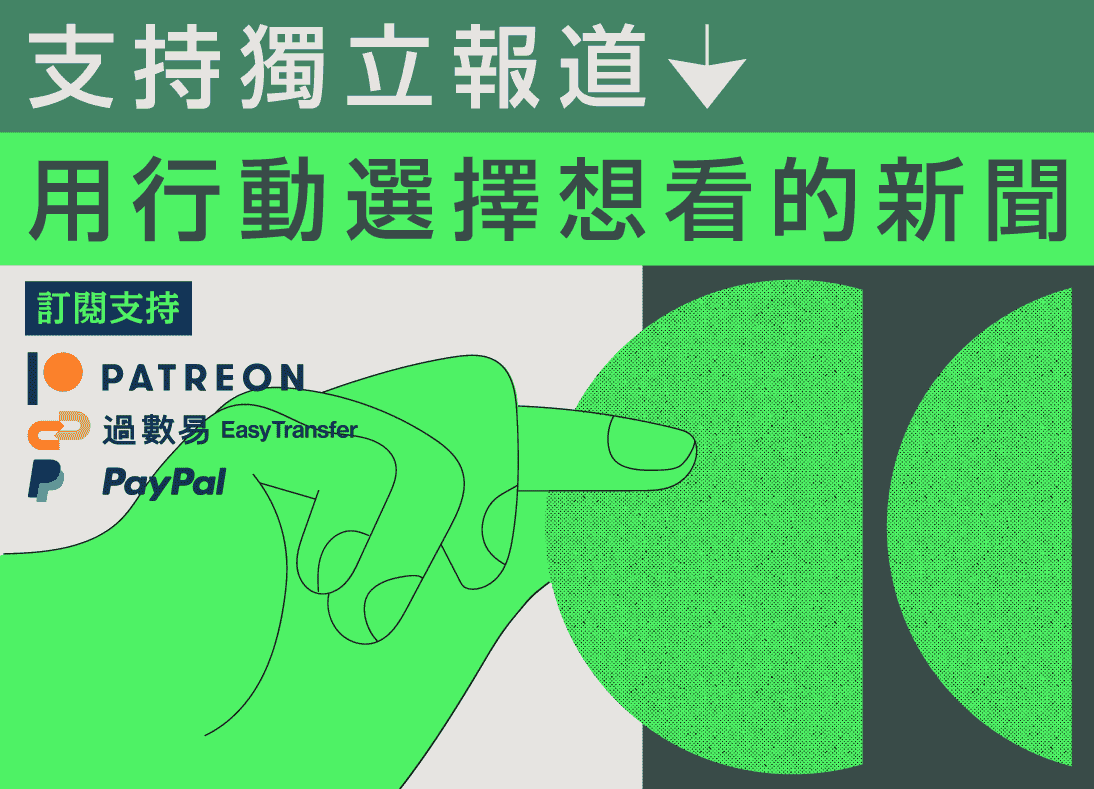何志峰 X Elisabela Larrea
追尋甚麼?「我是誰」。
我們認識,有幾面之緣,說過要詳談,借此機會,正好。
我問Elisabela,土生葡人之間的互相溝通,粵語和葡語已經十分足夠,沒有需要再講Patuá。Elisabela說,這已經不是用來作為溝通的需要,是身份,是一份認同感。現在,在澳門,很多大型娛樂設施內的指示牌,都沒有葡文,甚至連正體的中文也沒有。很多土生葡人會越來越懷疑「我到底在哪裡了?」「這裡還是澳門嗎?」「熟悉的中文和葡文都見不到?」下一個問題就是「在現在的澳門,我們算是什麼人?」所以,有一個機會聚在一起講Patuá,共同維持祖輩留傳下來的語言環境,就好像重新建構一個屬於自己族群的歸宿。
Patuá對有些年紀的土生葡人來說,是一個尋求身份認同的過程。現在比較有趣的,可以見到一些四五十歲的土生葡人,在facebook聊天的時候,會打Patuá。然後,每一年土生土語話劇表演,就是團結和感染更多的土生葡人,向大家展示土生葡人這個族群,每一次都會見到土生葡人爸爸媽媽帶著下一代來看,給孩子們說,這是父祖輩小時候聽到的語言,這是我們的語言。
事情不只發生在薩依德身上,人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就會想起自己到底來自那裏,才會問自己究竟是甚麼人。我十九歲時到南台灣讀書,一次老師介紹我們聽南管,因為唱的是閩南語,老實說,雖然老師說是很典雅的讀書音,但身為廣東人的我一句都不懂是自然的事。可我和來自香港的同學都能感覺到其質樸古雅的韻味,然後我們討論起,這種彈唱,廣東有沒有?卒之,我們在網絡上發現「地水南音」。然後搜集資料,細聽每一個唱家的唱腔,進行比較,尋找屬於本該是我們的東西,思考是不是在這一代就會被我們在不留神間湮沒了?
我是在外面才醒覺要去溯源自己族群的原本質地。Elisabela所屬的土生葡人族群的醒覺地,是在自己出生成長的城市、是孕育這個語言的地方,在急劇的變化中、在有意或無意之間,使之洗刷得消磨殆盡,澳門土生葡人現在只能緊緊捉住自己快被磨蝕的根。
Elisabela說,現在很多五十歲左右的土生葡人,一點一點地把Patuá學回來,他們小時候都不會講,那是他們祖父母輩的日常語言,普遍存在於五六十年代每一戶土生葡人家裡的嫲嫲婆婆口中,她們帶孫子時會給他們講Patuá,父母輩通常不講,甚至有些為了要小孩學好葡語,還禁止他們講Patuá,現在努力學回來,認為那是祖輩流傳下來的東西。
既然那些是已過去的語言/技藝,還學來幹甚麼?
「為的是甚麼?」Elisabela說。
對呀,為的是甚麼?每逢星期四去上區均祥師傅的南音課,我唱得永遠不會比師傅好。而且我的生命裡,南音只佔一小部份,甚至只算是人生階段的一個小點綴,以前區均祥師傅那一輩,甚至他的師傅劉就,和他的師伯杜煥,那些盲眼瞽師學這些技藝是用來謀生的。對現在的我來說,就算現在不學也沒有甚麼損失。我每星期不去上課、不去學,就會有更多時間陪家人,還可以看喜歡的小說、電影。到底我為甚麼去學?難道現在還可以去賣藝?
Elisabela說,Patuá也同樣遇到這種問題,年青的土生葡人,很少人去學,一日就只有二十四小時,不知道為了甚麼去學,可是她的一個長輩說︰
「Patuá我們(土生族群)一定要去學,這就好像,一個癌症末期的人,看來是沒有救了,死定了,剩下的問題,就是要不要醫?要不要盡力去醫?或許,有奇跡也說不定。」
為奇蹟而去做?哈哈,對呀,這是我和Elisabela得到的一個共識,人人都去做一些人人都會做的,那就不用我們去做了。而且,Elisabela更說,如果懂得Patuá的人又不傳揚開去,去敎想學的人講,文化的根就很容易會消失不見。
到底怎樣傳下去?
這就難以一概而論了,Patuá是一門語言,語言就要開班講授,一字一句的加以練習,要傳的當然是傳給不會的人,即使有人開班敎一些在生活和職涯上沒有必要的語言,可那些不會說Patuá的土生葡人是不是都願意來?
想來,我只是一個會去買地水南音CD回家聽的人。我當初去學只是玩票性質,決定去學時覺得當然最好找一個好師傅,其實哪知道誰唱得好誰唱得糟?不像Elisabela那樣知道有一個凝聚的族群。我這個年紀的人「去唱野」,和上一代的歌壇已經陌生,只能遍尋網上的資源,一開始能跟著CD玩著唱,去感受箇中韻味,而當中我發現有一位就是澳門的區均祥師傅。票友當然只是玩票性質,即使現在,我也只是一個跟老師學習的業餘學藝人,傳承技藝的責任仍在上一軰的師傅身上,對地水南音來說,還好,有老一軰的人。
我問Elisabela,會不會像我去學唱歌一樣,有沒有甚麼語言班講授,又或者係介紹Patuá呢?沒有開班怎樣介紹呢?Elisabela說:「我唔見有。」她接著說︰「飛文基律師有參與編寫的一本出版物《Maquistachapado: vocabulário e expressões do criouloportuguês de Macau》,是專門講Patuá的。」還好,有一本讀物在流傳,這是必要的,記得有一次我被葡國人問︰「你是澳門人,你會不會Patuá。」然後我就開youtube那一條《Macau Sâm Assi》給他看,葡國人看著看著就笑了,覺得很有趣,看來他們都看得懂,網路流傳發揮功用!
我和Elisabela說,我可不可以作如此類比︰葡萄牙語和Patuá之間的關係,像不像我們現在講的廣府話和開平、或者台山、或者順德話等次方言的關係。Elisabela說︰「有點像,也不太對」我明白,就是……不能類比!可卻讓我領會了一點。即使我和Elisabela說著一樣腔調的粵語,卻背負著極為不同的文化背景。
即使樣子長得如何像伊比利亞半島(A PenínsulaIbérica)的人,在我訪問桌面前這位美麗的小姐,在中學卻選了中文組,大學時最愛看的是武俠小說,更讓我佩服萬分。反過來,與我在整理這一篇報導時,正在享受著葡國來的葡萄酒、芝士配上中國製的魚皮花生一樣。拜託,這裡是澳門!這些各有背景的文化,流傳在澳門成長的人身上,在澳門這個載體,讓我和Elisabela各自討論著屬於自己的文化是多麼自然。
Elisabela在訪問中強調她不會Patuá,她說了很久她會聽,舞台上講的Patuá她大概都會,但是讓她講出來時,她說她沒有信心(我覺得是她謙虛)。她說這一代二三十歲左右的人講Patuá,都會被上一輩的人說︰不像我小時候聽過的!Elisabela說,這就難了,那裡去找我們上一輩(五六十歲)的上一輩?現在會跟著學著講的,即使講得不符合前人口味,都應該鼓勵。
這一方面地水南音比較好辦,就現在一個傳承人區均祥,他還真的有一個班,我去跟著學就是了。可是,他跟我們說廣州陳鑑的平腔南音如何如何,杜煥唱的也有其不同,這我就一頭霧水了︰即使是有著相同廣府文化背景也難以理解,因為這些是「文化的遺產」。像我全家歷代都是粵人,那些遺產畢竟有著時代隔閡,看來我和Elisabela所說的士生族群遇到同一樣的情況︰即使如何模仿前人,都難以回到上一輩人熟悉的從前的味道。
還好,地水南音很多蛛絲馬跡都可以在youtube找到,這是廣東人的事,畢竟廣東人還有超過一億。就看要不要去找?五六十年代的Patuá到底講成怎樣?土生族群只能靠口耳相傳。
「誰來學,怎麼學?」Patuá和地水南音在澳門遇到的傳承困境
Elisabale說,如果有開班,一定會去報讀,她相信也會有很多土生葡人去讀的。我覺得這是作為土生葡人對自己族群的自信。「但老實說,真的各有各忙。」她補充。
老實說,我每星期四上課上了那麼久,常常邀人來看我們上課,聽一下都好,都應該一起來認識我們本來的文化。可是,大都很難遷就時間,去上其他課程、照顧家庭、朋友約會,總之就各忙各的,也不能怪人家,現代社會就是如此,特別是成年人︰在國際賭城工作的人餘暇學藝的時間當然很昂貴,會去的那些已經是極少數有興趣的青年人。
我努力邀請過很多人來看區均祥師傅的敎學排練,因為這個傳承人公開的表演場次本來就不多,一年就一到兩次,想看想認識的人可到哪裏去認識?其實師傅也蠻急的,在區師傅的觀念,以及他在這一行的輩份資歷,如果不傳承下去真的過意不去。可是最讓我失望的是,最近師娘去文化局申請,打算十二月和去年一樣來次區均祥和他的學生共同登台,作為以老帶新的傳承表演,師娘得到局方的電話回覆說︰「不是區均祥自己表演?加入學生叫我們如何資助 ?! 」云云,就被拒絕了。師傅師娘蠻急的,生怕阻礙了傳承,但看來局方對保育傳承也不太在意。
土生土語話劇見於藝術節我所樂見。但作為習藝之人,屬於澳門的地水南音(還分別被收入國家級、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個名錄)都不見有表演者被邀請到藝術節或音樂節作專場表演,今年的國際音樂節也只是獲邀參與來自葡國的Fado樂隊大雜匯式的Crossover(Fado唱家倒是認真,來看師傅排演了數次),而沒有專場的講解和表演。我還真被香港朋友問及,有幾十人拉脫維亞國家樂團,而沒有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地水南音的澳門音樂節的事,太「離地」了吧?我也只能笑一笑,叫他自己去問文化局。
現在想來,真是極端的對比,土生葡人的族群小,大家同舟共濟,演戲的台前幕後同心合力,看戲的踴躍支持,Elisabela說今年的話劇表演更爆滿。見到很多土生葡人長輩帶著後輩,不同年齡層的人都來。看來土生葡人非常珍惜他們族群文化,土生土語話劇每次表演,都可以視為族群傳統再重構。地水南音對澳門廣東人的重要性顯然不如Patuá之於土生葡人那麼重大。與道敎科儀音樂宗敎性質和舞醉龍的漁民酬神功能不同,地水南音只是從前瞽師在珠海流域一種謀生技藝,算是城鄉之間具有商業性的娛樂。澳門現在是個娛樂博彩發達先進城市,甚麼娛樂都有,地水南音的商業性在現代社會變得可有可無。誰還會出錢請樂師回家唱兩出?
Patuá可以靠土生族群熱情,長輩傳後輩的維持。地水南音則是要師傅口耳相傳,演練時甚至會被逐句拆解。這兩項傳統都是流傳在澳門人的嘴巴裏,可是入門條件就非常不同了,Patuá至少要對葡語要有一定認識,地水南音則最好要識一種秦琴椰胡等樂器,彈唱真的有一定難度,即興的表演除了要板(拍子)準確、音要準是基本的,沒量化的「韻味」佔了絕大的關鍵。區均祥師傅常對我們說︰「你唱得不夠味」,我只能回︰「我多唱幾次,醃久一點。」這使我想到,到了我們這一輩或後一輩,還有沒有人有這樣的鑑賞力,直接說某人唱得「不夠味」?
我和Elisabela討論到地水南音和Patuá那一種會有失傳的危險,我們的結論是,Patuá和地水南音各有各危。
在澳門,Patuá和地水南音都只能靠參與者的熱情去維持。土生土語每年燃燒的是一個族群的熱情;地水南音卻是每個星期燃點著幾個人對自己說唱文化的懷古情意。每年一兩場表演雖只是貼個街招,出個幾百字的新聞稿,到場觀眾(平均超過五十歲以上)倒是坐無虚席,能不能會有我的後輩來聽?除了肯定我兒子會聽到外,看倌問問自己身邊有沒有十幾二十歲的人會去觀賞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不知道。我猜澳門的中學生大學生連Patuá和地水南音到底是甚麼都未必清楚。
語言,技藝與城市記憶
我想,現在地水南音和Patuá對我最大的意義,是維持著幾十年前澳門那個時空的點滴,大家想想︰五六十年代澳門的某個週日,在龍記酒家飲茶的茶客聽到劉就瞽師唱南音嘆茶,然後出來沒走幾步,正碰上在大堂彌撒結束,一位講Patuá的祖母帶著孫子去營地街市買餸,還有穿過營地街市往前走的爐石塘有人正在用木頭雕刻神像,晚上去清平戲院看粵劇前有一檔涼茶……在那個時候稀鬆平常,是社會的一部份,時移世易,現在都變了我們澳門的文化遺產。我們這一代三十幾歲的人,應該思考,即使我們已經很少去廟拜神或上敎堂望彌撒,我們還要不要這個城市留給我們的傳統。我們這一代是否有責任要將這些技藝和語言學到身上,再過十幾年展示給我們的下一代?還是讓文化局派人來做一個紀錄,例如錄一段Patuá或地水南音光碟,拿一個神像到博物館,讓大部份的大陸遊客和小部份的外國遊客給神像和那些錄音光碟拍個照就完事?
【非遺正在消磨 …… 除了保護,有否傳承?】近年澳門的「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 」、「魚行醉龍節 」、「南音說唱」、「木雕—澳門神像雕刻」被國務院評為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加上澳門的「土生菜」、「媽祖信俗」、「哪吒信俗」、「土生土語話劇」等等,看來是十分精彩的。而剛獲立法會通過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內,對於非遺的著重點則只在「紀錄」。 這些東西在被編錄成為「非遺」之前,都有它們的文化價值,現在真成為「遺產」了,價值還有多少?現今澳門社會,還有沒有它們的位置? 「保育」、「傳承」看來不甚了了。 「社會上有的人群有富人、窮人之分,還有一種人被稱為『弱勢群體』,他們的生存狀態差別很大。同樣都是 『非遺』 項目,它們之間的差別也很大……」、「瀕危項目,往往帶有『活化石』 性質,可能蘊藏著一些古老戲劇形態的信息,一旦消失,就不會再有了……」【康保成。中山大學敎授。理工學院主編《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未來》——-《第一屆澳門文化遺產論壇》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