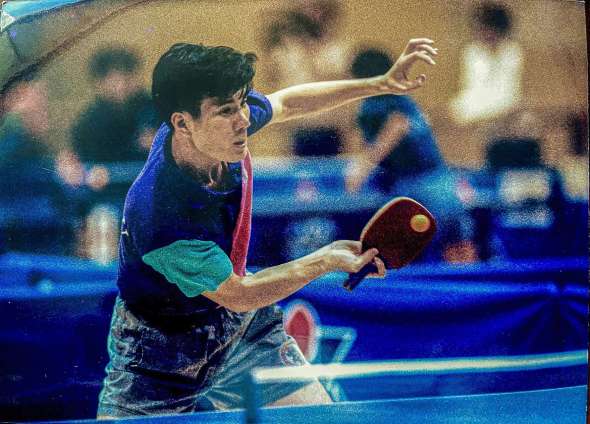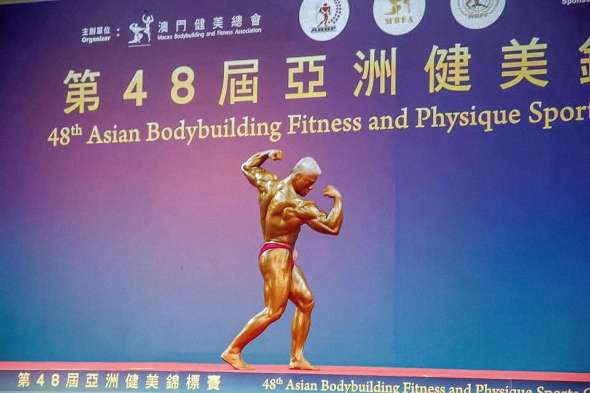在動態清零的時代裏,只有一關之隔的中國內地與澳門的關係顯得既密切又疏離。兩邊的人文交往,往往隨著一聲政令,明天又變得不再一樣了。除了國內新聞、微信與抖音以外,我們還可以透過甚麼渠道了解當代中國?
中國紀錄片導演周浩所拍攝的題材涉獵廣泛,包括中國工廠、城市拆遷、藥頭生活,這些每天都在中國某個地點上演,同時亦備受國際關注的議題裏,周浩的鏡頭從每一個個人、家庭及其生存環境當中切入,帶領觀眾閱覽這些芸芸眾生,究竟是如何處身其中的。而這些由人的性格與特質拉動的,與導演之間的關係與張力,又如何晃動公眾對紀錄片所謂「紀錄真實」的界線?一切在當代中國可能發生的事,都可以在他的影像當中找到這些痕跡。
私密、混沌、好奇、原始。在這些影像特質下,周浩廣泛地紀錄了當代中國各類社會題材,當中紀錄的人物,各自面對三餐溫飽、寄錢養家、童年創傷、權力運用等等的問題。對照今日,不少人在談論中國現代發展時所展現的已經有點固化的觀點當中,周浩的影片或者可以讓我們用另一種視覺去體驗目前神州大地的人文精神面貌。
第六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即將舉行,將為澳門觀眾帶來周浩二十多年來所拍攝的其中五齣紀錄片:《厚街》、《龍哥》、《棉花》、《大同》、《孤注》。今期專欄很榮幸能邀請到周浩進行線上訪問,與我們談談他對紀錄片與真實之間的看法。

紀錄片《大同》片段。
亦覴:我們知道你以前是一名攝影師和記者,後來才開始拍紀錄片,可以請你分享一下想拍紀錄片的原因,當中的紀錄歷程是怎樣的?你認為紀錄片能夠更靠近真實嗎?
周浩:我做了十年的記者,記者都是隸屬於一個機構。當你服務於那個機構便會成為那個機構的零部件。如果你不認同機構本身的價值觀的話,便很難在一個機構裏面工作。在我看來,其實全世界的媒體機構,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有著自己的立場。在裏面工作久了便會覺得:我爲甚麼一定要爲別人發聲?爲什麼不由自己來說點自己想說的事?即使我的受眾很小,每個人還是可以發出他自己的聲音吧。
我當時想,也許紀錄片可以更加貼近自己和真實一點。但實際拍了紀錄片之後,便會發現紀錄片的真實也是相對的,從來便沒有絕對的真實,因爲真實一定是跟你作為觀察者的角度、人生經驗、職業經驗有著非常大的關係。
我的第一部片《厚街》,我當時沒有在上面署名自己是導演。既然這是我拍別人的生活,我沒有導演它,為甚麼我會是「導演」?第一次我是這樣認為的,所以我在上面署名是「製作」。接著後來做了更多的紀錄片,便發現這應該是每個人的宿命吧,所以我們沒必要在這個問題上這麼較真,因爲本身就沒有真實。如同羅生門一樣,在100個人的心目中就有100個真實,像羅生門一樣。我慢慢接受了這個現實,用我的方法來觀察這個世界。

《孤注》電影海報。
亦覴:例如說《龍哥》,作品的界線一直存在使它本身變得更模糊的問題,就像是有人會認為裏面是在演戲、不夠真實一樣,《孤注》中佟老師也會擔心被消費。你在這方面有甚麼想法?
周浩:這不僅是關於紀錄片。任何行業,不同觀察者也許會得出不同的觀察結果。拍一部紀錄片,你是跟裏面的人打交道,就像今天我倆交流一樣⋯⋯一些人可能會對裏面的人說:你就當我不在一樣正常生活吧,我就拍拍你的正常生活。其實這是一種掩耳盜鈴,只要你介入了別人的生活,別人的生活怎會不會改變?
有人說龍哥就像在演戲,有人說你拍的龍哥不夠真實,因為龍哥永遠在說假話。那我就反問你了:一個不說假話的龍哥就是真的龍哥嗎?所以說,有人在紀錄片裏演戲的話,我是樂見其成,因爲那也是這個人性格的一個組成部分。有人天生就喜歡演戲,你偏偏要拍他不演戲,我認為這是一個悖論:你不是想看到真實的別人嗎?所以有個年輕人一開始去拍片的時候跟我說,「這個人總是在演戲,我怎麼辦?」我說,只不過是他演的戲不是你所期待的一場戲吧?
所以,我不會太糾結這個問題,你進入了別人的生活便要正視本身所帶來的問題。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必須清楚知道觀察是一定會影響別人的生活。就像佟老師的生活平時也是按照她的節拍和頻率來運轉的。為甚麼會找他們,實際上也是溝通好,因為你受過創傷,所以我去採訪你,別人也是知道你為甚麼要來拍的,要人假裝若無其事像平常一樣生活,這不是一種自欺欺人嗎?只有當你充分認識紀錄片的工作屬性,再去觀察別人,或許會得到一些所謂更真實的東西。有時候,真誠的態度比真實本身更重要,其實我們並不是去探究所謂的真實,我們是在真誠地探究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亦覴:那你是怎樣跟受訪者、被拍攝者建立關係? 我們看作品時會覺得受訪者好像不介意鏡頭在,你拍的時候是這樣嗎?
周浩:鏡頭是一直在的,有時你看不到,是我們把受影響的部分剪掉了,這一直是一個悖論。不可能你出現在別人的生活裏面,別人不看你,你就可以假裝說這很真實。我覺得拍紀錄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既然出現了別人的生活裏就一定會改變別人,要不你就別出現。
亦覴:你剛提到甚麼是真實很難說。為甚麼會堅持拍紀錄片?
周浩:如果說這世界沒有真實的話,那不就變成一種不可知論了?那你乾脆不要去做這事了。我覺得紀錄片是一種人和人之間交流的一種方式。我們在用鏡頭跟別人進行交流,那這種交流以後也許你會⋯⋯比如說你看完《龍哥》以後,我會問你一個問題,說龍哥是好人還是壞人?也許你不能第一時間馬上回答,但其實你已開始跟這個人產生了連結,開始關注這樣的人,開始知道有人是用這樣一種方式生存,那不是變成人和人之間交流的一種方式,這世界也因此變得能夠互相知曉。
這我並沒有說我拍完片子就是探究真實,但我們一直在……這並不能阻止人去探究真實這種欲望,我們都想知道所謂的真相,但是真相本身就是在虛與實之間。同一件事,不同人得出的結論不一樣,結論本身並不重要,所以我不覺得探究是沒有意義的。我不能探究真實,我的片子就沒有意義嗎?不會是這樣的。

紀錄片《棉花》片段。
亦覴:龍哥出獄了嗎?你們還有聯繫嗎?
周浩:龍哥沒有出獄,他還有三年。現在我還有給他寄錢,因爲沒人會給他錢,他父母也很不寬裕。我們在監獄裏還有約,他一直沒人去看他,但他可以打探視電話,每隔一兩個月可以打一次出來。我就會接到他的電話,他也不可能跟所有人都打電話,監獄會讓你登記幾個電話,他就會登記我的電話、他媽媽的電話。我們也約好,出監的時候我可能會去接他。
亦覴:你關注的議題很廣泛,會怎樣去選議題?
周浩:如果要總結起來的話,還是一些關於社會的議題。畢竟我們活在當下,我生活在這個年代,我肯定就是觀察周圍的人的生活狀態、我周圍的社區、我所在的國家,它們肯定會變成我的一個觀察對象。就像《龍哥》裏面所說,其實我在看很多人,有些是有錢的有些是沒錢的人,我只是對人的生活狀態有興趣。
亦覴:那你是怎麼讓受訪者答應拍攝的呢?
周浩:其實被拒絕還是很多的。你看過我拍過官員、毒販、普通人⋯⋯有時我覺得人其實並不拒絕跟別人交流,但前提得建立在他覺得這個人不會傷害他。這是基本的,因爲人總覺得人心難測,有時會怕被別人害。當確定這個人不會害你,其實很多人是願意跟別人交流的,因爲我們不是獨居動物,我們是社會型的動物,我們需要社會、也必須要跟社會發生關聯。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喜歡傾訴,如果有人願意去聽我們說話,只要把握好這個點,有的人是願意傾訴,有的人可能會內向一點,覺得自己老是被傷害便會怕。從概率上來說,也許十個人只有兩三個人願意跟你說,我就去找那兩三個人吧。所以我被拒絕的情況還是非常多的,甚至有的人已經拍了幾年,卻說「你別拍我了」。這情況也有,這是常態。我常開玩笑說,如果有人願意讓你拍就是中彩票了。所以有時候你就去把握這種機會吧,我覺得。

紀錄片《厚街》片段。
亦覴:那你一般拍攝的時候,會出現一些禁忌,或者是你覺得會被指責,覺得不想拍不該拍的地方嗎?
周浩:當然會有,就是別人答應了拍攝,也不可能去把別人剝得清光,你要給別人保留一點尊嚴。我也做過記者,並不是說你越深入越好,有時深入了反而會很尷尬,你知道吧?因爲你拿出來的東西,並不是說拍完了別人以後就可以⋯⋯即使我們拍之前跟別人簽了合同,他同意了讓你拍攝,但是這種合同你沒發現嗎?他隨時是可以撕毀的。這個合同和條例,對他來說是沒有約束力,只對我們有約束力⋯⋯所以我們跟他們的這種關係,永遠都是要小心謹慎的面對。
亦覴:那《孤注》最後也是停止拍攝了嗎?處理結尾是有怎樣的考慮?
周浩:我們畢竟還是很實驗的,所以當他拒絕拍攝時就意味片子要結束。但他(姚尚德)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吧,我們後來問他我們拍的素材能不能用,他說:「沒問題,你用吧,但我不會再接受你們的拍攝了」。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尊重的結果。
亦覴:其實在中國在拍紀錄片,通常會遇到什麼的困難或機會?
周浩:其實全世界拍紀錄片都是這樣的,首先是你有一個好的選題,然後要去找資金支持。中國的支持方可能跟國外的支持方不一樣,打個比方,像臺灣的紀錄片也許是有很好的產業鏈,有很多的支持,那其實在中國也有很多的支持,政府也有很多支持。也許政府的支持有它自己一些選擇方式。
我覺得拍紀錄片其實最難就是錢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社會制度原因,它會在你們看來有很多管制,像是《電影法》之類。現在我們拍紀錄片,實際上需要電影局批准。我覺得這是每個社會都會有的問題,但我覺得拍不出一部好片,你把它歸咎於社會制度的問題,我覺得有點牽強。就像伊朗,它的管制肯定是比我們還要嚴格的,但並不阻礙他出現一些世界級電影大師。既然你生活在這個地方,就要想辦法適應它。如果說你想變成一個鬥士,那你就去跟他鬥,或者乾脆離開。如果你要在這裏做就要想辦法找到你自己生存的方式。
亦覴:導演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喜歡的紀錄片嗎?
周浩:比如說我在今年北京電影節看了《火山之戀》(Fire of love),是講一對專門研究火山的法國夫妻,他們最後在探究火山的時候死了。導演是用這對過身了30年夫婦拍的素材編出一部影片,這部片被《國家地理雜誌》買下來,他們可能會成為今年衝擊奧斯卡一部非常重要的影片吧。
我經常被問甚麼是好的紀錄片,就是一個傳奇的故事、一個你沒有聽到過的人生。其實每個人看電影就是爲了拓展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我們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條件限制,不管是經濟條件還是社會條件,其實我們這一生活動的範圍相對還是很狹小的。我們想了解這世界的話,也許電影是一種非常好的方式。就像你們離中國大陸這麼近,但實際上你對中國大陸又有多少了解?也許你看看紀錄片,你會有新的了解。

周浩( 《孤注》片段)。
亦覴:想請問有哪一個風格的導演是很欣賞的嗎?
周浩:⋯⋯我會對一些關注社會問題的、當下的一些東西相對有興趣。但是也不一定,比如說像前幾年奧斯卡的最佳紀錄片《Free Solo》,這種片你說我覺得大多數人看都會喜歡,對吧?因爲他在探究人類能力的邊緣,你看過那部片嗎?大陸翻譯叫《徒手攀巖》,那是一部非常非常棒的片子,就講一個人徒手攀大巖壁的故事。
亦覴:導演可以透露一下在進行的計劃和未來的計劃嗎?
周浩:我一直在做,《孤注》完了後我做了一個,英文名也許叫WuHan Factory《武漢工廠》。這是講…..你們知道Motorola手機嗎?還有中國的那個Lenovo電腦⋯⋯是在中國大陸最大的工廠,在武漢。我從疫情、武漢封城開始就拍了很多工廠,拍一個工廠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怎麼去面對危機。開始是新冠肺炎的影響,後來是中美貿易導致了他們產品賣不了,他們不斷處理這樣的問題,即是一個中國企業如何生存的故事。
亦覴:那導演未來也是會一直拍紀錄片嗎?有想過停下來?
周浩:沒想過停下來。
亦覴:一直拍,拍到退休?
周浩:沒想過退休,拍到死吧。因為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我沒有這種退休的感覺,就會一直做下去。
周浩簡介
一九六八年出生,貴州人,先後在《貴州日報》、《新華社》、《南方周末》擔任攝影記者。二〇〇一年參與紀錄片製作,作品曾入選各個國際電影節並多次獲獎,以《棉花》與《大同》兩部紀錄片奪得二〇一四年及二〇一五年臺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