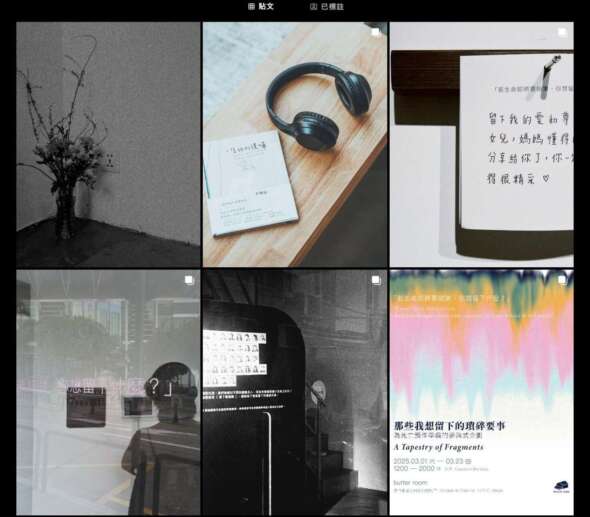阿忠與我 (選自國家兩廳院官網)
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怎麼樣的一種身體?
為什麼你的會比較不一樣?
當表演者之一周書毅悄悄進場時,實驗劇場仍然開著世界光,觀眾還在進場,忙於找尋位置。我早早坐好了,眼前的演區空無一物,沒有任何道具與設計的乾淨舞台。
穿著日常服裝的舞者徐徐走進,然後同樣帶著隨意、好像不想引起任何關注似的,開始慢慢做起動作來。
那是一些看似不複雜、不刻意的動作編排,好像自然而然地,身體只是,一種流動而已。
因為似乎「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燈光也還是世界光,大家都沒有那種「現在正在演出」的鄭重其事,只是隨意瀏覽著。畢竟現場同時在動著的,除了舞者,還有正在進場的觀眾。
當我正享受著這種不刻意的氛圍時,《阿忠與我》悄悄開始了。
「你認識我嗎?」(演出獨白)
周書毅在場刊中說,這一次創作,是以鄭志忠這位台灣重要的資深劇場工作者為主要研究對象,以身體角度切入。當人物成為一個課題,承載了一切經歷、情感與精神面貌的身體,有許多敍述的層面,身體就像一本書,有待翻閱。
坐在輪椅上的阿忠進場了。他的流動與周的有很大不同,那是什麼不同?我們的身體本來就各自不同,如何使用、利用?就像你用了身體,我用了輪椅,他們都是身體的一部份。
一個純然地隨心所動的身體,手腳能自然協調,平衡、使力、抬高、蹲下、每一部份的肌肉都在協同工作中,還有內在能量與呼吸順暢的支撐,身體是最微妙的科學,天知道要做到以上這些,個人要花費多少氣力與時間去掌控去揣摩,又要有著怎樣天賜的好運,才可以擁有一副運作精良的身體。而不擁有這些條件與能力的身體,也自有流動的方法,地板的使用更多,只要不再約束於所謂「舞」或「動作」約定俗成的呈現,觀看的方式就可以不一樣了。使用的空間不一樣,能量不一樣,使用身體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著力點不一樣,由於雙腿不能使用所以大部份身體的重量會壓在上半身與手臂,這形成重心完全不一樣的移動方式,相對於只能用腿來移動的人,其實兩者同樣有局限,同時有不適合的方面。
「平等是什麼?自由在哪裡?」(場刊)
如果說開始的兩人Solo,是在展示各自的身體特徵,好像是一個自我介紹的開場白。接下來的多段兩人舞,就是在開展對話。

阿忠與我(選自國家兩廳院官網)
身體的不同雖然可能會造成某些動作的阻礙,但動作的邊界不在身體,因為動作本來就可以有不同的設定,如果不看成是約束,只是身體彼此取向的不同,在使用的層面,動作是否就可能會有不同的維度?就有可能展開平等的對話?
探索展開,身體對話展開。周也坐著輪椅與阿忠一起動,或者兩人一起在地上,或一站一坐,一坐一爬等,身體條件的各種互換。像是兩人一起在地板上的那段動作,接觸互動的點都不同了,兩人的腹、髖部更多的著力與挪動,燈光在大部份的場景中都是表演者,與聲音/音樂一樣存在著自己的語言,與身體一起貼近地面的燈光,霧茫茫的光朦朧了兩人的身體輪廓,只看到動人的身體與能量,不需要再去區分,何謂殘缺?何謂健全?或者根本區分就是徒勞無益的,如果此身非我有,又要以什麼准則來指出他的不同?那並不是有如黑暗與光明的對比,何況在劇場裡,黑暗也是好看的,而且意義非凡。
「你可以看到黑暗嗎?請想想別人」(演出獨白)
這次的音樂創作與音響設計像是與表演者同呼吸,那些來自地板的震動,那些敲動心弦的獨白,那些巨大聲響像築起一道一道無法穿越的牆壁,包圍著我們。
身體何其龐大,又極其渺小——這是阿忠告訴我們的,把他每天出門需要準備的那一套程序如實呈現出來,我們就明白了。另一套法則的存在,是要告訴我們原來的觀看方式是何等狹隘。
一如這次的內容,兩個外觀明顯不同的身體彷彿不斷置換著主體與想像,有時非此即彼,有時既此亦彼,抛開殘缺或完整的內容載體,不斷被拓展著的是意義、表演與身體的領域,演出像是一層一層剝開,那為年月粹煉的身體存在,所指向的是最純粹、本質的呈現,可能就是演出終結時往上攀爬、探尋的所在,即使真實世界中所謂的「共融」,到底還是離我們很遠。

《阿忠與我》演出宣傳(選自國家兩廳院官網)
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阿忠與我》The Center
周書毅 X 鄭志忠
2021年4月25日14:30
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