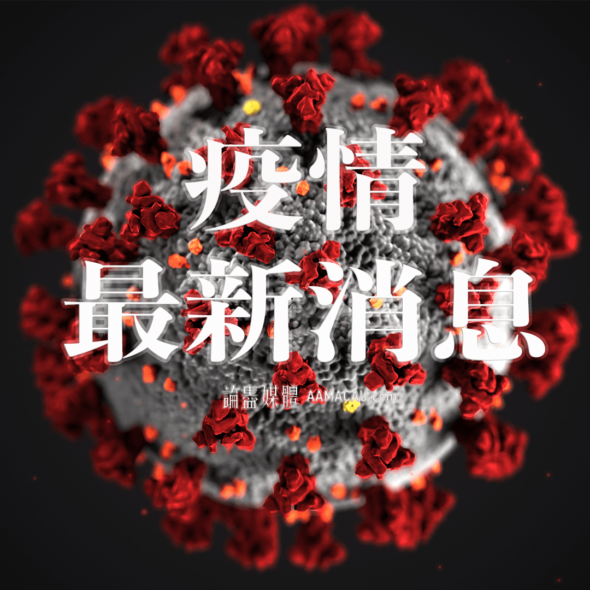社交網站上,通訊軟件中,近年不乏外傭僱主的群組,部份更擠擁得不能再加收「群友」。僱主們會在群組中做甚麼?互通「情報」——有查詢手續,也有說着自己家傭的種種表現,甚至數臭家傭;有收集管教家傭的建議,又或是徵集平常和家傭相處之道。而最經常出現的帖文之一,是家傭的相片或護照相片。圖中雖然略有「打格」,但外傭的樣貌乃至個人資料仍清晰可辨。僱主會在上面貼文發問:大家用過她嗎?她表現如何?
對於上述情況會否涉及侵犯個人私隱,《論盡》於2015年也曾向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查詢,當時收到的回覆表示,一般來說,如有關資料被部分遮蔽後仍可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某人的身份,已屬個人資料。若要公開他人的個人資料,需得到當時人的同意,或基於正當利益,否則或會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縱然如此,此等帖文從未消失。有僱主團體曾促請有關當局及職介所尋求建立家傭資料庫的可行性,以進一步保證家傭質素,但有家傭關注團體認為家傭資料庫實際上就是「黑名單」,容易對家傭造成不公,亦涉及私隱和名譽的問題。又指出:「如果個家傭被炒咗幾次,係咪一定代表家傭做錯?」表示曾有不少家傭被炒多次,卻最後在一個家庭融洽相處工作多年。「咁呢個係邊個問題?會否亦需要設個僱主黑名單?」

著有《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的學者史唯覺得,頗大的一個原因是社會缺乏安全感。
事實上,近年每當說到「家傭乜乜乜」,僱主在網上都會有很大反應。著有《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的學者史唯覺得,頗大的一個原因是社會缺乏安全感。「整個社會都缺少。不管是僱主還是移工,都缺少安全感。」
僱主家傭均缺安全感
史唯表示,當一個陌生人進入自己家裏,進入自己的「私領域」,這種不安全感就更強烈。「這種不安全感不只是在(家傭)這件事上,而是很多事情,只是因為家傭來到家裏時會更擴大。我覺得這安全感是種社會性的安全感。」
史唯指,很多時家傭和僱員存在文化差異。「家傭來自於不同的國家、地方。在我採訪的過程中,有一個僱主就抱怨說她坐月,家傭總是做沙律,冷冷的,(僱主)想吃點熱的,煲煲湯,(家傭)教也教不會,就覺得她很笨。但設身處地地想,做另一種不熟悉的飲食,可能我們也弄不好。」「有些(家傭)就不吃豬肉,僱主可能就想:『我為何要專門給你去買牛肉』,可能會說:『我都吃,你也可以吃呀』。可能作為僱主的角度而言,我是主人,你來這裏,你應該將就我才對,如僱主也能考慮到文化上一些差異,可能會消解一些這種差異。」
同時,現在本地媒體上有關外籍家傭的正面報道甚少出現。「在媒體上會有這樣的說法,比如『哪個家傭給小孩餵了很多藥』、『會打他』怎麼怎麼樣,(僱主)就會更恐懼。」「媒體首先最少要盡量避免類型化、刻版印象化。媒體的高度首先要不是對某群體特別大的偏見,這種東西會影響到僱主。想請小孩的人一看,請了哪個保姆都這樣,誰還敢?」
史唯表示,很多僱主家中都裝有錄像頭,就為看着小孩。「我想,如比如說,中介機構或政府能有一個很可靠的一種對家傭的培訓,很專業的培訓,或(家傭)取得怎樣的資格,有一種能緩解僱主的不安全感。有怎樣的一些措施可以緩解這種不安全感的話,可能會有一些幫助。」

學者史唯 。
澳門的定位是甚麼?
根據統計局的就業調查,2018年澳門就業居民有28萬人,在澳工作而居於境外的澳門居民則有9000多,合共約29萬幾。另外,在澳門及境外居住的外地僱員人數超過18萬(其中家傭人數約2萬9000)。史唯認為,依賴外來勞動力與澳門的定位有關。
「澳門的定位是甚麼?要發展博彩業,每天這裏多少賭枱,那邊多少賭枱,現有的人口就是這麼大。這個矛盾澳門首先要想清楚。你的定位和角色、你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還有你要把澳門變成甚麼。澳門是怎樣組成的?誰算是澳門人?這都取決於你怎樣去定位:你的文化怎樣定位?你的經濟地位怎樣定位?你的政治地位怎樣定位?」
「博彩業長得這麼大,你要不斷維持它;它就像是雪球,像餵不滿的怪獸。你每個月賺兩百多億,哪來的?就是博彩。博彩怎樣提供的?它要維持,必須要吸收這些新錢,它就必須要提供服務,提供服務就必須要有人。你的定位就是博彩,世界甚麼甚麼樣的一個城市,澳門只有六十萬人。」「就像一個人本身的胃很小,要吃很多東西,成為一個野心勃勃的國際都會,就是要靠外面的人來充,只能是這樣。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定位問題。」
「政府(對定位)這樣的一種期待,或對目前澳門這個角色,社會的認受程度是怎樣的?」史唯認為,現時社會出現的矛盾或也顯示一種對社會定位認受的落差。「博彩業是要不斷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的邏輯是和我們的期待是不一樣的。」
史唯指,澳門家庭越來越需要家傭,當中的數量非常大,政府應要重視這問題。對於現時,往往僱主有僱主自己互相討論的群組,外傭亦有外傭自己互相討論的圈子,她認為兩個群體需要有互相溝通的平台,讓雙方的焦慮都可釋來。「這是我在(當年)採訪時是沒有遇到的。」
「我覺得目前澳門政府根本顧不上這些。除非出了人命,出了很大的惡性的事情,才會想到這問題很大了。」「因為現在都是個案,政府不會重視的。現在都是個案,某個家傭如何如何惡劣,某個僱主如何惡劣,報道了兩天,社會譴責一下,沒有了。具體的東西,如何細化出來,怎樣去避免更嚴重惡性的事件發生,是需要很細緻的。」
「其實這是很大的一個社會隱患問題。僱主不安心,家傭也不安心,這需要一些消解和溝通的渠道。是不是一定要出了事才會去重視?是不是一定要堆疊到很激烈的程度才去重視?我覺得這些早就該做。早就應該公開討論,不是只指責一方。」
她也認為,社會對於家傭作為一種勞動力,亦需要有起碼的尊重。「她跟我們一樣,需要薪水,需要養家,去維持她的再生產、她自己的生活、消遣、需要。我覺得這些方面要對家傭要有足夠的尊重。她是一個勞動力,她是要按照市場的價格去計算她的價值,所以她的最低薪水到了一個甚麼程度,而且她的最低薪水和我們社會整體的薪水的差距已經是非常誇張的一種程度時,我覺得這也是需要考慮的。」
「其實她們跟我們的工作是一樣的,只是環境放在家裏。你不能看她說她沒有事,反正她沒地方可去,做點事也沒關係。同樣我們也是這樣。如老闆讓你無休止地加班,(說)『反正你也沒有事』,你會怎麼想?」
她又表示,歐美地區會把家傭看成勞動力。「歐美非常在乎勞動者的權利、工人的權利。這東西成本就很大,一般中產階級的家庭是請不起的。因為你要幫她付保險、社會保險、醫療保險。他們非常在乎所有群體休閒時間多少、工作時間多少、福利多少、基本的社會保障,非常在乎這些東西,所以成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