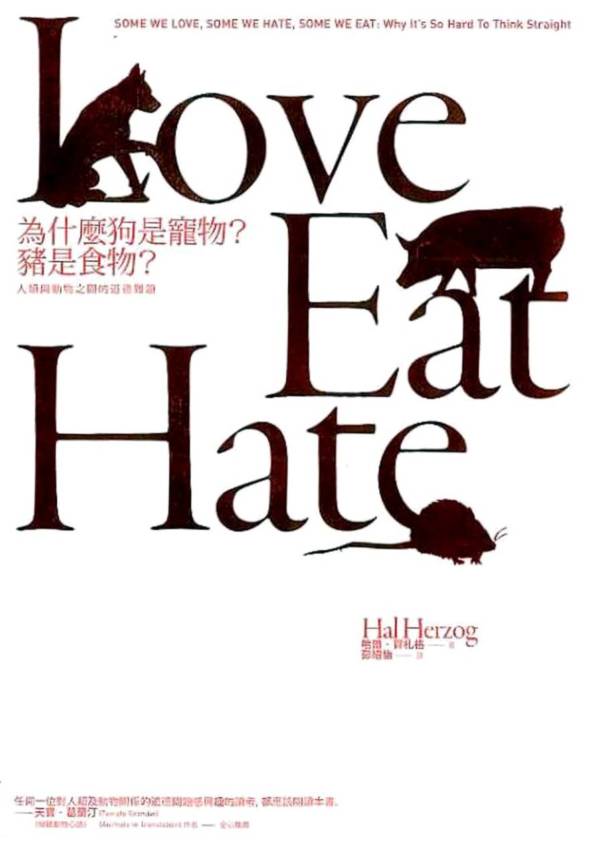在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的移地展出,我看到大量已滅絕動物的標本。有的動物因為在滅絕前來不及被製作成標本,所以展覽以塑像代替。展覽標本的來源,大多來自貴族階層的狩獵與買賣,唯生物學家有意識去梳理與論述,我們才得以見到地球多樣物種的來龍去脈。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動物所面對的環境、人類與動物產生的關係與本身物種的醒覺都不同:狩獵買賣、貴族 藉由標本呈現人類靈性與生命層級的高尚、自然史的梳理、環境思考、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的思索,走到今天這一步,生物命運進入公民議題的討論與思辨,遠比標本本身重要。
澳門被圈養三十年的動物,一隻名為Bobo的亞洲黑熊死亡。官方(民政總署)發言,報告之後將會根據流程,把這隻黑熊製作成標本,卻產生市民激烈反彈。

在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曾展出臺灣黑熊標本,但其實最深刻的是環境教育設計細節。有不同海拔與棲地的哺乳動物介紹與骨骼排列,以及不同哺乳亞綱的獸足拓印。
類似「處理流程」在澳門不是第一次見,先前於黑沙海岸發現的擱淺中華白海豚屍體,民署發言也是將會為之製作標本。之後在花城公園的一場關於中華白海豚的展覽,我的確看到了真實的標本,可惜整個展出乏善可陳,比較類似生態文件陳設展,而鮮有讓觀展者深思與互動之處。(有觀展者笑稱,「展覽對市民的意義,就係有免費冷氣」。)
冰冷的、毫無感情的標本展,會是澳門生態教育的形式嗎?
回應民眾對Bobo遺體的處理反彈,民署堅持自己的立場,並表示未來將會成立澳門自己的標本室。這個回應讓市民反應更大,幾乎是要發生政府信任危機層級的事件。一邊是「事後」處理,另外一邊訴求「身後」,「科學研究」與「大眾情感」一時對立,在輿論中形成激烈衝突。太可惜了,官方又錯失了一次讓公眾參與的生態教育機會。
1.圈養動物,城市主體?
當我們觀看動物,觀看到其實是人。
被觀看動物的命運,與人緊緊相依。這也是為什麼一隻圈養動物,集合三十年澳門人的情感於一身。這在野生動物身上鮮少出現,一來野生動物沒有「義務」出現在人類面前,市民也不太有機會出海去看到。二來它背後可能有一個更大的、「不讓野生動物被看到」的原因,或許是一個更優先於生態環境的、運作中的社會利益架構,也或是產業與權力流動的結果,例如失落的海上神祇祭儀、取代海洋思維的大陸中心史觀、以及由這些政策主導的/丟給澳門的發展價值,如港珠澳大橋或填海工程的興建等等。
圈養動物很容易變成指標,成為集體記憶所繫之處,剛好也是因為在這些儀式上的進行更加容易(校外教學、動物命名、節日參與),中華白海豚也是具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展現城市主體的一部分,牠沒有提供「被觀看的義務」,也沒有「形成人類行為儀式一部分的義務」,所以容易被「看不見」與「忽略」。
亞洲黑熊Bobo牠不像大熊貓在被迎接之前就有被禮遇的展館與飼養準備、牠不必購票就能與公眾面對面,因為市民在接觸Bobo時,排除了有膜拜感的政治儀式,收容命運、飼養空間與展館的設計,都容易令人產生「Bobo就即係澳門」「牠即係我(我家人)」的聯想。
動物自身不會知道人類多重視或忽視牠們,但保育和滅絕就在這些「看得見」「看不見」「怎麼看」與情感建構中出現。
澳門這次的黑熊處理事件,幾乎是一場政府信任危機了,官方在講流程,用科學塘塞程序運作,但市民感受的是情感、記憶、城市的過去與未來,「澳門是什麼」「澳門人是什麼」等城市主體性的討論,幾乎就要在死亡黑熊身上出現。被圈養、被禁錮的人生,無法自主的醫療、死亡程序,生前、生後被展示的人生。大家對官方提出與憤怒的,真的只是亞洲黑熊的處理嗎?
2.標本之必需?在保育的語境下,有沒有可能形成更立體的對話、關於生命為何、科學教育是什麼的思辨?

大英自然博物館移地展出內容,觀展的孩子說「牠好可愛,可是,我的心裡覺得好痛⋯⋯」,人類需要用幾個世代,來彌補用錯誤方式觀看動物時的失落無依感——內心的巨大破洞
在Bobo生前,我們可有做過與牠物種命運相關的、更深刻的自然教育思考?一樣被公眾視為記憶所繫之處的圈養動物,臺北市立動物園的林旺與馬蘭,牠們在死亡之後被作為標本,「讓大象站起來」開始了牠們作為標本的展示。但其死亡其實是動物教育的延續,動物的來源、動物勞動奴役、戰爭與生命、野生動物的貿易里程等,在大象林旺與馬蘭「生前」的社會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爾後當大象生病,野生動物罹患疾病的情況也一直在被公開討論的狀態:「我們很難藉由外觀去看到野生動物是否罹患疾病,因為牠會避免獵食者發覺而有隱藏病態的情況」(如果牠有一日突然重病,會是一種野生動物的自我保護所致)、「大象不可坐下,當有一日牠不再站立,身體將無法負荷自身重量,遂逐漸步入死亡」。在動物園對學校、公眾發布的生態教育中,我們會知道野生動物圈養知識,並且同時在飼養的「臨終與死亡」教育上與公眾一同為動物的死亡做好準備。
(有澳門市民說「我在收到民署發布Bobo無法進食時,已經排定週六去探牠,我實在接受唔到Bobo第二日(次日)就被公布已經死亡」,另外一位澳門市民回應,因為媒體收訊習慣不同,他在網上才看到無法進食的訊息,然後兩個鐘頭之後就立刻收到動物死亡的消息,這讓人不免懷疑政府是否有所隱瞞。並想到如果在這件事上都能隱瞞,那重大危機發生時,市民還可以相信什麼。)
本來可以由官方主導的思考,再次因為表態堅持「『展示』之必需」的觀看方式,反而斷絕了與公眾對話「科學為何」的道路。
3.未來,大家在觀看長隆的動物時,還會想到我們曾經有過Bobo嗎?
在Bobo生前,我們沒有機會認識或參與動物救援與收容的動物園工作,也不被允許知道「專業」的動物園教育是什麼。甚至是在教育資源分贓的情況下,前往錯誤的商業圈養環境去進行「生態教育」。沒有途徑學到真實、無法藉由圈養動物思索棲地現狀、牠們生存的環境壓力、人類行為介入的生存危機,當科學研究話語的霸道與民眾的集體生命探索(或說城市身份與主體的探索)出現對立,Bobo也無法在澳門自然史上有所意義,堅持以標本館來實踐科學研究或生態教育的姿態更不可行。
在生態資訊量巨大的時代,沒有標本,還能怎麼辦?
我們的Bobo死了,不再於澳門這個城市於你我同在,但牠會是個起點,我們該延續的去追尋的是在牠生前我們沒學會的事物,取代現在依然在進行中、觀看動物的錯誤方式,在反對好大喜功的標本展現時,有同時拒絕前往以生態教育為名的動物娛樂場所。如果沒有前往野地的可能,或許用閱讀來與不同世代的人群進行對話:活在巨大的自然史裡(《最高的塔,最小的星球》。小魯),看到生命的極限(《最高的山,最深的海》。小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進到大海中,看到不可思議的巨大哺乳動物(《藍鯨》。維京),見海見山又見樹,得知我們都在同一個星球卻不一樣的棲地裡居住(《樹》《海》《山》。積木),因為想看得更清楚,把謠言都追尋清楚(《動物謠言追追追》。親子天下),認識到更多的,是人類自己的現狀:我們從哪裡來?媽媽的肚子怎麼製造一座最初的大海,人從一條小小的魚,變成一個完整的「人」,生物結構學,讓我們感謝身體,知道自己的來(《骨之旅》。小熊)。然後,小心去想,活在第六次物種大滅絕的時代裡,每一個與動物有關的事情,都攸關自己的命運(《地球之書》小熊;《海洋/陸地滅絕動物》青林)。
與孩子繼續共讀,問達爾文怎麼在小獵犬號環遊世界回鄉之後,在整理標本的百無聊賴中讀到馬爾薩斯神父的《人口論》,看《演化論》如何牴觸神學環境創造出釐清事實、理論、信念的科學研究方法(《達爾文與演化論+21個自然實驗》。字畝)。
問清楚我們今天去追求建造一座屬於澳門的「標本館」在自然史裡的意義為何,整件事情是否與華盛頓郵報記者蒙特.瑞爾(Monte Reel)在《測量野性的人》(Between Man and Beast)詳實記載維多利亞時代在非洲追獵大猩猩的動物獵人保羅.梮謝呂(Paul Du Chaillu)及其同時代的建設者有所異同。當我們在測量自己與亞洲黑熊Bobo(或其他以製成標本的中華白海豚、大熊貓等)的距離,它同時也如同《測量野性的人》在預示澳門未來人類的命運。(《測量野性的人》。臉譜出版)
澳門的亞洲黑熊Bobo,或許真正的任務不是在於變成教學或科研的標本與否,而是在與市民那麼深刻的交往之中、在牠無法重回野地的命運裡,帶我們「回家」,去問「自然」到底是什麼。
延伸:
1.「我們用人對待人的方式對待動物,或者說看着動物如何被對待,想到人如何對待自己。」(莫兆忠《動物解放人類》。《澳門日報・新園地2015.2.15,16,22,23》)
https://goo.gl/DCCbae
2.「解放鯨豚,其實也是解放人類。」(盧盈年《海灣不該是血色》。《黑潮電子報第82期——告別禁錮,讓愛自由》)
https://goo.gl/i5QVhk
(來論照登,不代表本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