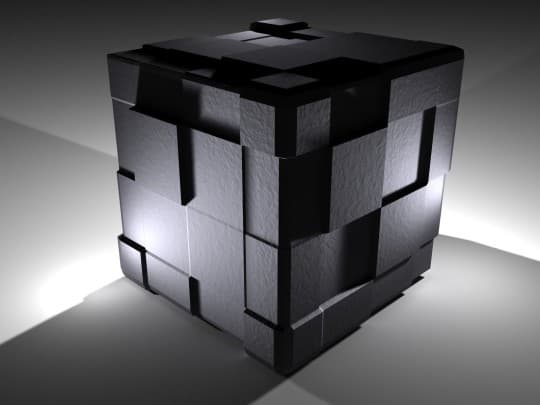一月廿日,某位剛到訪澳門的外星人打開報紙,立即嚇了一跳:報紙引用了某位資深評論員說,澳門沒有新聞界。
「可是,」外星人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如果沒有新聞界,這報紙是打從哪來的?」肯定是中文學得不好,有甚麼地方解讀錯了。外星人左思右想,覺得問題該是出在新聞界的「界」字之上。到底「界」指的是甚麼?他原來從沒認真想過。
直到他認真鑽研起來,才發現「界」字在澳門竟然這麼重要。翻開同一天的報紙,發現上面滿滿都是「界」:傳媒界、教育界、文化界、勞工界、學術界、體育界…因為到傳媒界的路程最遠,所以外星人決定先到教育界和文化界,展開他的田野調查之旅。
媒體資料顯示,澳門教育界是一張很大很大的網,覆蓋住本地和整個大江南北。負責編織這張大網的是一群精神旺盛的生物,據聞有六顆眼珠,能夠在同一時間轉到不同的角落去;又有八條充滿勁力的長腿,總是沿著網絡穿州過省拜會這裡,探訪那裡。他們有著同一個夢想,就是有天能把世間云云學子都黏在同一張網上,讓他們唸同一樣的課綱、考同一份的試卷。
可是,鑑於澳門也許並沒有新聞界,只看報紙顯然是不準的。外星人決定喬裝打扮,混入教育者中明察暗訪。說起教育者這族群呀,以前是住平地的,卻在教育改革的攻防戰中變得越來越沉鬱內向,到最後更撤退到在祟山峻巔之上去居住。他們用削尖了的竹棚圍出了一個個與世隔絕的山寨,在外面掛上了「閒人止步」的牌子。每當有陌生人靠近時,他們就會拼命用拳頭槌胸,並且咧開大大的嘴巴,對入侵者露出一口陰森的利齒。
外星人成功潛進山寨後,發現山崖上滿滿都是用鐵鍊吊著的鐵籠子,裝著很多餓得皮包骨的孩子。所謂教育工作就是教育宇宙真理的工作,所謂真理指的就是香蕉的分配公式:聽話的孩子有蕉吃,不聽話的孩子要捱餓。以往,聽話就是指別隨意發出「呱呱」的叫聲,擾人清夢。現在的小孩卻必須要學懂唱歌、跳舞、表演雜技(例如打鞦韆和踩波車),才能討來香蕉一根。此外,在山寨間的搶蕉大賽獲勝,「為寨增光」的小孩能一次吃上幾根香蕉,及得到在籠裡呱呱叫和咬別的小孩卻不受懲罰的特權。為了示範給孩子看如何耍雜和搶蕉,教育者自己也得在籠外手舞足蹈,呱呱亂叫。到底教育者是在籠外,抑或是籠內?外星人思緒混亂地想著。
迷失在目不睱給的奇妙景象之間,外星人幾乎忘了調查「教育界」的任務。外星人發現,除了搶蕉大賽外,山寨裡的人根本不關心別寨的情況──當然趣味醜聞和災難性悲劇除外。外星人在山寨呆了很短的時間,就聽到不少關於在遠處的某個山寨如何被教育改革攻陷的流言:眼睛如火炬的大蜘蛛在黑夜中推倒山寨的圍牆,如黑色潮水般湧進山寨之內…緊隨流言之後的是大批大批前來尋求庇護的難民。他們拚命敲打著山寨的大門,希望進來避難。淒厲的叫聲如流感般感染寨內的每一個人,大家開始四處打聽消息,想要尋找一個更堅固、又或是更偏僻的城寨。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當外星人離開山寨時,他仍舊搞不清楚到底甚麼是「教育界」。到底是織網的人,抑或是堅守在深山中的人?不過,外星人必須動身離去,以免被人識穿身份。外星人於是決定去尋訪傳說中的文化界。
外星人雖然缺乏語言天份,但還是勉強知道「文化」(Culture)一詞出自西塞羅「靈魂之耕耘」(Cultivation of Soul)的比喻。據說,早在半世紀前,文化人就在這個大部份地區仍被沙漠覆蓋著的島嶼上默默耕種,盼望能種出一片綠地來。雖然五十年過去了,這裡仍是一片沙漠,然而令人鼓舞的是,心靈耕耘者們還未渴死。
文化人所以活了下來,據說和天然水的供應有關。本市的河水是鹹的而雨水是酸的,所以必須仰賴由機器提煉出來的天然水。決定如何分配天然水的是一群「委員」,他們住在用黃金打造的新市鎮裡。城市中央有座建築物,是個黑色的大盒子,從外面是看不透裡面的。據說,這座建築物前衛地參考了京城「藍色立方體育館」的概念,而後者則參考了倫敦的「白色立方體藝廊」。
外星人走進黑盒子建築內,只見大堂中央豎立了一個金色人像。金像的底座刻有文字,解釋說這原是在舊城區撿來的一座碎石像,全靠近年流行的文物修復和口述歷史,專家們才發現它大有來頭:它是古代某位國王的雕像,這位國王有點石成金的奇妙力量,大大提升了澳門的生產總值。一旦他發現自己的女兒是個只懂抱怨政府批評富人的懶蟲後,決定大義滅親,把女兒變成黃金,傳為千古美談。委員會已通過把這位偉人列入澳門人的集體回憶當中。現正全力收購與其生平事蹟相關的建築,例如他常去的煙館、賭檔等等。把這些建築鍍金後會作為博物館開放給市民參觀。
外星人越過大堂,後面是大門深鎖的會議廳,門口掛著「正進行公眾諮詢 閒人勿進」的牌子。外星人把尖耳朵貼在門上,聽到裡面有物件碰撞的聲音,和幾個人在粗聲粗氣地怪叫著「碰」、「上」等字眼。外星人在門外站了好久,還是沒有聽到有關文化的對話。唯一例外是他們批評文化人喜歡亂花錢,專做蝕本事。聽到這裡,外星人已感到霧煞煞,坐在裡面的不是文化委員嗎?他回到大堂裡,碰到一個正在清潔國王像的大嬸。「大嬸,你知道澳門的文化人都到哪裡去了嗎?」「他們不在這裡啦,」大嬸回答,興味十足地打量著外星人,「他們都到舊城區去了。」
到舊城區的路並不難找。黑盒子和舊城區之間,接駁著一根很粗很粗的水管。。外星人順著水管到達城中心,發現那裡的舊屋全被拆掉,清出了一大片沼澤地出來。沼澤地寸草不生,唯獨中央有顆其大無比的椰菜,幾乎有三層樓高。耕耘者們如忙碌的蜜蜂般圍著這顆椰菜在打轉,替它施肥、灌水和上顏色。外星人想靠近觀看,卻發現椰菜的四週圍著鐵絲網,還架著幾門澳葡時代的大炮。他只好隔著鐵絲網,大聲問好。
一位耕耘者迎了過來,「你來這裡幹甚麼的?」他狐疑地問道,「我…我是來看椰菜的。」耕耘者臉上閃過一絲驚喜的表情,「這是我最新的作品,《十一號》,你覺得怎樣?」「我…我覺得好像還滿不錯的。」外星人緊張兮兮地回答,對方卻不滿意,「不錯?那你說說看,它跟我的《十號》比較起來怎樣?」「我…抱歉…我沒看過。」外星人嚅囁著說,他感覺到豆大的汗珠滑下臉頰。
對方的臉垮了下來,「怎麼可能沒看過?你知道《十號》是前年京城藝術展的入圍作品嗎?你居然說沒看過!」外星人心想身份要被揭穿了,誰知對方自顧自說下去,「唉呀,你看,現在澳門人質素就這樣低,除了賺錢以外甚麼都不管。想當初這裡還是一片沙漠時…」農夫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演說中,繞著圈忘我獨白著,「我們不甘心留在舒服的沙龍裡,我們走進死氣沉沉的舊城區,想用綠色的藝術力量感染這座城市,讓它重新活過來…」
「可是,為什麼只種一顆椰菜?種一片草地不是更好嗎?」外星人忍不住說出心中的疑惑。
「草地!你說草地?那只是騙遊客的商品!藝術是不惜成本的,藝術是不搞Mass Production的。我們把水和人力匯聚在這裡,一心一意地把《十一號》做好。想當年,當澳門還是一片沙漠的時候呀…」
「那麼,為什麼要圍起鐵絲網,還把大炮架起來?」
「嗯,這個呀,還不是為了對付那些該死的老鼠!這舊城區住滿了野蠻沒文化的老鼠,牠們總愛把《十一號》咬爛。」
農夫這樣一說,倒是勾起了外星人的興趣。和農夫告別後,他離開農地,徑自走進舊城區的橫街窄巷當中。在一條特別陰暗的小巷弄裡,他發現了一隻睡在路上,用紙皮蓋住臉在打呼的灰褐色老鼠。「嗯…你好呀。」「誰呀?是記者吧?」老鼠撥開臉上的報紙,睡眼惺忪地啐道,「我不是街友,你滾開。」「那你是誰?」「我是藝術家。」「你,你是藝術家?」外星人驚訝地問道,隨即注意到自己的失態。「喔…抱歉,我是說,你在搞那方面的藝術?」「我甚麼藝術都搞。」「那麼,你搞過甚麼藝術?」「目前還沒有。」「文化人跟我說,是你們咬壞了他們的藝術品。你怎麼說?」「那顆椰菜叫藝術品?別笑死人了!沒錯,是我咬壞的,誰叫那些農夫和黑盒子委員會勾結,狼狽為奸,壟斷了全部的人工水,害我甚麼都種不出來。」外星人很疑惑,他說,那些農夫和委員明顯是不同類型的人。老鼠卻幾乎笑出了眼淚,「傻瓜,如果他們不是一伙的話,你要怎樣解釋那根水管?」
最後,外星人向老鼠請教記者的住處,「你看見遠處的夕陽嗎?向著日落之處走去,你就能到達新聞界的所在。可是你得趕緊去了。日落之後,大地被黑暗籠罩,你就找不著路了。」
**********************************************************************
他睜開眼睛,迷迷糊糊地感覺到很多人在看著他。可是真怪,那一張張看著他的臉是純白色…
他眨眨眼睛,那些臉沒有鼻子,只有兩個很深很大的眼窩,像外星人的臉。那是…
他又眨了眨眼,那是死人的臉!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間堆滿著骷髏的房間。
「你在山路上跌倒了,我們把你救起,送了過來。」一把柔和的聲音說道。外星人從床上爬了起來,發覺一位鵝蛋臉的年輕人坐在床邊。那位年輕人上半身沒穿任何衣服,下半身圍了一條草裙。
「這是我們部落的頭顱屋,這些頭顱屬於我們的祖先,他們為我們而死。」年輕人故作平淡地說道,但裡面卻有種刻意壓抑住的憂鬱。「我們都給客人看這個,」他的聲調上揚,彷彿想強調內心的驕傲,「我們想讓大家知道,真相傳播者的不朽尊嚴。」
房間的門被推開,幾個村民走了進來,興致勃勃地打量著外星人。外星人這才注意到,自己是在一間茅屋之內。而眼前的幾個村民,都赤裸著上身,只穿著簡陋的草裙。
外星人向村民說明來意,想知道新聞界是否存在。「新聞界不存在?簡直是胡說八道,」村民七嘴八舌地抨擊道,「那他要怎樣解釋這房間裡的祖先頭顱?」村民答應外星人,第二天早上,就帶他到處去參觀。
在接下來的一天,外星人幾乎肯定新聞界是存在的。這條村落位處於山脈中央的盆地,山路如迷宮般險要,一不小心就會摔個滿天星斗。村落的週圍沒有城牆,卻劃出了一條很深的壕溝。「敵人很多年沒來過了,但為了表明我們不同於外面那些胡說八道的人,我們給自己劃下了這道壕溝。」鵝蛋臉年輕人說道,他正帶領外星人參觀村落。外星人現在知道他的名字叫摩西,一個絕不流露感情和違反律法的人。
村落由數十間茅屋組成,入口處建有頭顱屋,中央則是部落長老所居住的禁地。輩份在這座村落非常重要,長老們個個渾身刀疤,並且掌管著上古流傳下來的集體回憶,「我們是經驗主義者的信徒,」摩西說道,他正帶著外星人走向村落的中央,臉上因染上落日的紅霞而顯得未老先衰,「你看過了天色的幻變,你的血曾灑在村落的泥土上,這樣你就擁有了帶領族人的威望。」「以前這裡不是這樣子的嗎?」「當然不是,老人家說,以前這裡到處是肥沃的田地。可是後來我們得罪了黑盒子委員會的人,他們切斷了通往這裡的水管,」摩西俯身捏起地上的泥土,「現在大地龜裂,五谷不生,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活活餓死的。」
「你們有把這件事告訴大家嗎?」「當然有,我們每天測量土地的乾旱程度,再作時序的分析,把結果張貼在頭顱屋的門口,以證明黑盒子委員會在打壓我們。」摩西憂傷地說,「可是,沒有用,沒人要管在世界邊緣發生的事。」
外星人不知要怎樣安慰對方,一種強烈的絕望氛圍扼殺了他說話的能力。
「其實,」摩西突然沒頭沒腦地說,「天色自那時起也不一樣了。這裡經常維持著黃昏的狀態。光線剛好夠人們注意到村落的存在,卻不夠讓他們走到這裡來。」
「所以黑盒子連太陽都控制了?你們有把這個告訴大家嗎?」外星人興奮地說,自以為替這個困局到一條出路,「你可以告訴大家,黑盒子將會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他們,目的是要操控整個世界!」外星人心想,像灰老鼠這類人,必然喜歡聽這樣的故事。
可是,摩西聽到後只是搖頭苦笑,「我們只能說我們眼見為實的事情。那怕是為了傳揚真理,我們都不能夠作假見證。」
說著說著,兩人來到了村落的中央廣場,中間豎立著一個瘦削的騎兵雕像。那個雕像有張蒼老卻倔強的臉。恰好地,雕像底下也坐著一個在吃煙斗的老人。他看見外星人,便迎了上來。
「我聽過你的事蹟了,真想不到,現在還有年輕人願意攀山涉水地過來這邊。」「很少人會過來這邊嗎?」「現在很少了,」老人吐出一口煙圈,飽經風霜的臉上看不出情緒,「可是在從前,大家都會不怕艱辛地來到這裡,以一睹真理的奧秘。」。「你們為何不考慮搬到外面去?」「我們不會為了讓客人方便找著我們,就搬離這個地方,不然客人就變成我們的主人了。你看見圍住村子的那道壕溝嗎?那是我們對自己的誓言。我們不會搬離這裡的。在這裡,我們是自己的主人。只有當我們是自己的主人時,我們才能傳播真理。」
「那麼,新聞界存在嗎?」「對我而言,它當然是存在的。」「對你而言存在,這樣就滿足了嗎?」「這樣就滿足了。有甚麼比面對自己更難的事呢?」「我以為你是傳媒人,但現在你聽起來像哲學家。」「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年紀,誰不是哲學家呢?」
外星人覺得這話題說不下去了,就指著老人背後的雕像問,「這人是誰?」「他是澳葡時代的客觀與法律之父。」「我以為他是唐吉柯德。」外星人吃驚地說道。
「他是我們效法的對象。」摩西突然插嘴道。
「你怎麼可能效法唐吉柯德呢?」外星人狐疑地說道,「唐吉柯德之所以是唐吉柯德,是因為他把風車看成是巨人去攻擊。如果你已經知道了風車只是風車,你就不可能是唐吉柯德。」
「所以你也不是唐吉柯德了?」老人笑著問道,「那麼你四處遊歷,所為何事?」「我想去看更廣闊的世界,待我看得夠多了…」外星人看著被夕陽染成血紅的天空,覺得自己正在做一個了不起的誓言,「說不定我就能把風車看成巨人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