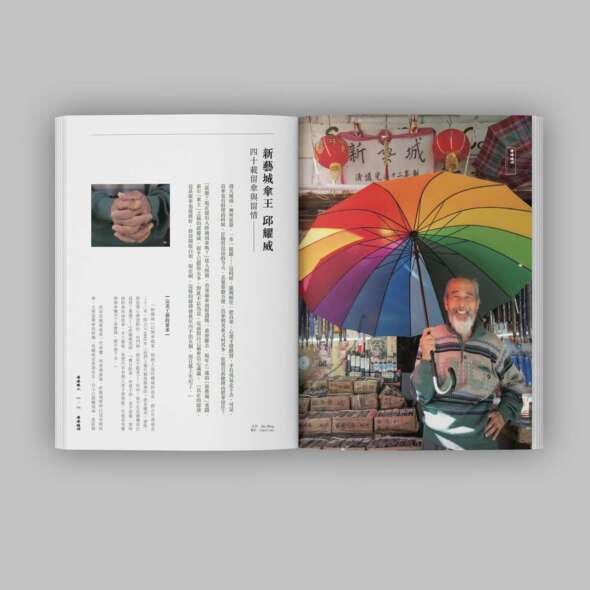2002年,初至澳門,友人帶我走進西洋墳場,我滿心疑慮:「為什麼澳門人與墳場比鄰?」後來這個疑問,陸續從不同遊澳友人的嘴裡吐出,大夥兒又各自解答:「澳門人是莊子的學徒,個個都看透,能一死生居住?」「うですが(原來如此),墳場是一個城市的歷史沉積,百年老城的各種包容性,從居住者能與鬼神和睦居住,就能看得出來呀。」
再後來,變成澳門人,更聽聞許多軼事:
「別到鏡湖對面,從前那一區,都是亂葬崗。」
「我也曾在夜半走進墳場,聽到了一影子操洋文,卻見不到人,原來這聲音,是從某某將軍雕像傳出來。」
又「聽說望德堂後有幢樓便宜,我便走上去看房,還是買不下手,不得了,墳場的相片,個個對著我,若哪天有人落棺或撿骨,我還能看得清清楚楚耶,不能買呀。」
在今天的城市空間裡,生與死原來還是各有場域,之前遊客們佯裝成人類學家,怎麼解讀,都是瞎猜。
澳門土生作家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在《愛情與小腳趾》裡流放了男主角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因為自己的浪蕩行徑,散盡家財,淪落入華人貧民區,他的流放處就在今天鏡湖前方。我才恍然大悟,西洋墳場從來就不是權力的中心,它是葡漢族群的交界處,基督城的邊緣地。
這次澳門文學節一座談「邊界內外」又誤植作「邊緣內外」,卻恰好體現了這個城市邊界邊緣同存一境的特質。
無論是澳葡時代或是回歸之後,這裡一直是權力的邊緣。既是化外,來歷各異、飽含故事的創作者在此聚集,但彼此之間,卻又界線清晰。
何其幸運,可以在澳門文學節裡能讀到葡萄牙、巴西、台灣、大陸以及澳門本土不同語系的作家作品,這些聲音幾乎就要讓我有一種參與國際性節日之感,但作為一個節日參與觀眾,心裡一直有種「如果還有這個那就更好了呀」的希望。
不抨擊節目安排和消息公布的情況,因為已經比前幾屆好得多了,主辦單位發印了節目單(儘管到場似乎變更挺大,但我仍每天握在手上,計劃下一場座談該怎麼前往),也發行了電視廣告(就算家中老母每每吃飯時間睇到都要問句「這到底在賣甚麼」)。單從內容來發願,我好渴望能聽到澳門漢語、葡語或其他語種的寫作人對於澳門本地文學的不同論述:可能別於/融於海洋性或中原史觀,也可能還有另一種本土視角出現的可能性。
我總以為關於一地的文學論述應該不只有一種視角,主流也不應專屬於一種權力,只有經過討論或是矛盾的修正(或者根本不必修正?),才有可能展現出一地的文學樣貌,它可以是多元的,也允許各種不明確存在。
澳門是旅遊城市、移民社會,移民者帶著旅行的想像而來,然後安居在此,或今身、或世代,一篇書寫自澳門的文字,都可能帶有書寫者曾經的異地色彩,也可能是其原鄉文化的濫觴,這些東西怎麼能清楚界定?無法定位的美麗,這也是澳門文學吸引我的地方,在此城辦文學節,便有可能碰撞出各種不同的火花。
喜歡席慕蓉那晚朗讀《蒙文課》,提醒各個族群回歸自然和土地,以「人」(不以各種界線)的身份相互去愛、去理解。不那麼在意自己是不是在邊緣寫作,或放心地書寫各種邊緣,唯有把自己放在邊緣處,才能找到界定之外的幸福(回應前段,飛歷奇不也寫作《愛情與小腳趾》讓弗朗西斯科愛上了維克托利娜,還有《大辮子的誘惑》中愛上了阿玲的阿多森杜),澳門文學節或許正可以作為一個消弭各種族群界線的平台,從對話開始,展現出在這個城市中,各種隱微施展的文學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