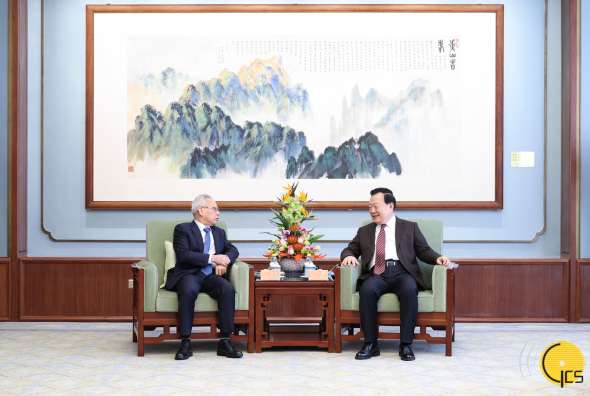還記得初中畢業前夕,思想品德老師拷了一部記錄片給我,名字叫《天安門》。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通過影像了解「六四」。我為民眾在鎮壓前向軍人送蔬果的畫面而感動痛哭,也為柴玲在錄像機前大喊「我知道這次一定要流血」而震驚扼腕。
那年,我十四歲,而那位思想品德老師教的正是所謂「政治洗腦課」。
其實早在小學,我便知道「六四」的存在。緣由無它,用Google在內地搜索「天安門」,會出現「部分搜索結果不符合中國法律,未予顯示」的提示。這行字,驅使了我的好奇心,鍥而不捨地追查背後的秘密。終於在大陸2002年才建立的網絡萬里長城管制下,我逮到漏網之魚。
那隻身阻擋坦克的身影,以及央視主持人羅京鏗鏘有力的「螳臂當車」旁白,讓我認定這是場家仇國恨,雖然八九那年,我父母尚未結婚,母親仍是位大學生。
說到母親,她在八九中的經歷無甚特別,僅在學生聲明上簽了名字。我的小姨則沾沾自喜於要遊行聲援北京的那天,自己躲在一樓樓梯角落,沒被「鼓動上街」。母親常常強調,在政府秋後算帳中,因她非學運領袖、扮「三不知」,順利逃過一劫,而那些積極串聯的卻身陷監牢。「不要觸碰政治」,遂成為我母親對我的諄諄教導。
不觸碰政治,並不意味在家不談論政治。由於「六四」激起了反叛心,我與國家意識形態越走越遠,與父母的政治鴻溝愈發擴大,因此我與父母任何涉及政治的討論,無不以爭吵收場。等到長大了,翅膀硬了,我不光仍舊堅持自見,還有實際行動,比如參與2010年保衛粵語遊行。父母沒有加以阻止,也似乎對此無能為力。
知道八九那年中國社會湧動的細節越多,我便越對六四有揮之不去的心結,好像一切陽光與滋潤、一切激情與理想、一切進步與正義,在那天凌晨,遭坦克碾碎;好像中國轉向開放民主的樂章,在那天的新聞片中,戛然而止。因此每年點亮十幾萬燭光的維園,成為我心中的聖地。
2012年大學考試前的第三天,我跳上開往香港紅磡的直通車,完成了朝聖。父親似乎早察覺我的心思,在火車啟動不足十分鐘後,發來一條短信,勸我好好準備考試,不要被利用,要有判斷能力。父親從始至終沒有名言我會去幹什麼,因為這本身在大陸就是一項禁忌。
到達維園已經是下午六點,分隔集會區域的圍欄已經架起來。民主英雄紀念碑正對集會舞台中央,紀念碑下面有許多市民的獻花。我在靠近舞台的地方找到空位坐下,隨即拿出口罩帶上。雖然在黑壓壓的人群當中,講白話的我難以被認出大陸人的身份,但我仍擔心之後會秋後算帳。高中二年級,即2011年茉莉花革命風聲鶴唳之時,我一位同學被老師召去和國保談話,僅僅因為他在twitter上轉發反政府的信息。有鑑於此,對政治後果的顧慮,我無論多勇敢,總會有。
第二年再來,我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圍觀者,而是一名記者,要給實習的媒體供稿。
6月4日當天,當我在茶餐廳望著有線新聞播出李旺陽的好友悼念李時,我眼濕濕了。我很感動,港人實在做了太多,甚至可以為一個絕大多數內地人都不知曉的民運人士,而呼喊。
而本來我三日已經和維園旁一棟民宅的看更打了招呼,希望能在晚會當晚俯瞰維園的燭光。可惜的是,我四日晚七點半離開維園,前往尖沙咀採訪本土派的活動後,天降暴雨,晚會腰斬。翌日凌晨我回宿舍點播電視新聞,見到市民在雨中守護燭光,我相信那一幕,便是這二十四年來,最具象徵性、最美的畫面。
同一天的澳門,也不改二十四年來的慣例,在風雨中悼念亡靈。
六四,始終是無法迴避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