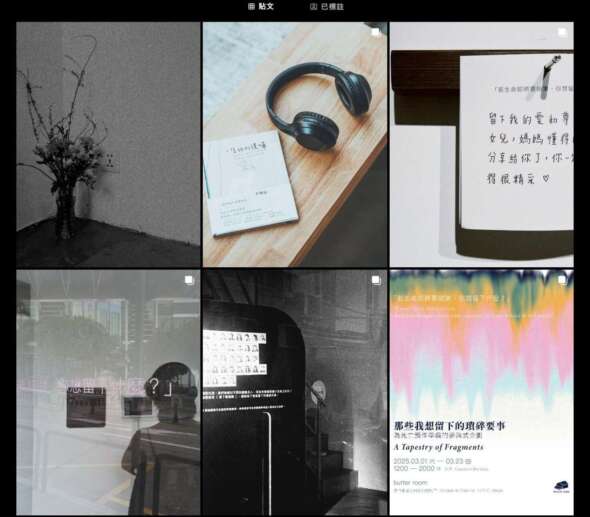到了2010年後,澳門多了很多拿起攝影機敘事的青年。
科技普及,或許是拍攝技術變得低廉易得,這個五、六十萬人口的地方,越來越多青年用鏡頭書寫自己的城市。不管結果如何,手法如何、成敗如何,在各種因緣際會的情況下,他們奮勇地拿起攝影機作出嘗試。這十年間到現在,即使是曾有「東方荷里活」之稱的香港,每年生產的電影已遠不及前,台灣的電影也在境內市場努力。在以前相對落後香港的韓國電影,在這十幾二十年間已經發展成一門賺大錢的產業,在亞洲範圍普及開來,甚至在世界的電影市場中已經有一席之地。香港和台灣的電影產業已難以向韓國看齊。澳門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政府出了扶助政策,本地青年作出嘗試,當中他們努力地向所謂 「商業模式」進行模索和嘗試。商業模式,緊張刺激,美國片如是,以前的港產片如是,韓國片如是。然而,在配套、產業、市場、觀眾、政策等未有足備的情況下,可想而知,當然是舉步維艱。本文無意去探討澳門的電影創作怎樣才可以在商業或藝術上獲得成功,只是想紀錄一下,一直在「襁褓之中」發展的澳門電影,如何不丟掉澳門的身影。
《痕跡》(編導何飛,90分鐘,2014年)
故事是講述,一名外地男子,在澳門從事高利貸事業,故事一直在欠錢和還錢之間發展。男主角置身於由澳門賭業衍生出的高利貸行業,他的生活風景揭示了他認識的澳門,賭場、黑道、高利貸。直至到他認識了在澳門地標——議事亭前地書店工作的少女,繼而產生感情,因為「書店、少女」的出現,他認識的澳門與自己所處的社會不同了,藉此重新思考澳門/少女的澳門與自己的關係。再考慮這個關係如何維持/能不能和如何留在澳門。賭博的社會,出現書店和文青少女,這樣的世界觀大概很難出現在任何類似的黑幫類型片,但在澳門觀眾眼前熟悉卻又不覺得突兀,而且真實。
影片最後,男主角返回中國大陸生活,即使能在黑道上生活,也難以與澳門的生活共融。與其說黑道男子本來不屬於澳門而出走,倒不如說他所代表和描述的世界與少女所代表的世界難以相融。影片裏,同屬澳門的兩個世界之間所發生的戀情多在晚上發生,而不是在正常作息的白天。最後,代表著兩個澳門世界的戀情分裂,在澳謀生的黑道少年離開澳門,有點即使無奈也希望這個黑暗的世界消失的意味。
《沙漏愛情》(編導陳雅莉,90分鐘,2014年)
少男(攝影師)和少女(舞者)的感情美好發展,與另一對相對成熟的地下(婚外)情侶(女舞者與中年男編舞家)的感情失敗,兩條故事線互相參照交替發展。
要說的是,是在故事發展之間,對澳門與澳門以外「外國」的二元看法:少男的攝影展在澳門辦成,並有機會去外國(留學?展覽?),少女的舞蹈甄選的結果是在外國巡演。而故事線的另一對情侶,則是女舞者決定從外國回澳,而與舊愛——因同樣回澳甄選舞者的男編舞家重遇。所有角色的際遇都有「本地」和「外國」非常二元的地域屬性而開展,彷彿可以從在未來「外國」生活的無窮想像,變得美好,反襯的是在澳門生活的侷促、狹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太緊密而變得互相擠壓。
本片值得深思的設計是,感情失敗的女舞者回歸澳門住在父親家裡,與同居而住的少男對出去外國發展的憧憬的反差。以「家」作為保護和離巢展翅高飛的意象非常強烈。
《骨妹》(編導︰徐欣羨,97分鐘,2016年)
到了《骨妹》,是講述澳門有一段過去。已經移居台灣的女子,回到澳門後,重新找回故友,回憶與故友於八、九十年代在澳門推拿中心作按摩技師的故事。
相較於上面兩套,《骨妹》用已經在外地成家(男女成家)的澳門人的立場,去講述過去的點滴,減少了當下以澳門的立場去思考是否移居外地的元素。即使故事開場的一句對白說出了主題︰「這,已經不再是我認識的澳門。」然而,卻因為澳門友人逝世,義無反顧回來。在一輪與故友相聚回憶下,影片對過去的重新建構,更重遇少女時代,與另一少女好友共同所育的兒子。在重建她的生活脈絡之後,主人翁再度與過去連結,重新在澳門生活。對於澳門「留下」還是「出走」的問題上,給下了非常清楚的答案︰即使出走,「最後,我也會回來」。
《下一站》(編導黃小雅,19分鐘,2017年)
在這裡得提一提《下一站》(編導黃小雅,19分鐘,2017年),一開始便在父子回憶開始,並於加拿大母親通電話中,預示要離開澳門。然而在新舊巴士上的交疊敘述。在與父親買下的舊相機作為留住過去的象徵,以巴士的失智老街坊作時間定格的串連,並回應主角對未來的猶疑,其實已經不難解答。即使父親已是故人,也離不開父親對他的影響。在相機的籠統舊照、失智阿婆八十年代的巴士月票,主角連結過往父親,繼而是還有父親所在的澳門。但「這一切都是過去」的訊息鮮明,因為第一個父親墓前的鏡頭已明確告訴觀眾「一切都已經是已經死亡的過去」。
《下一站》裏面那一部父親的照相機。在戲裏象徵著「留住過去、留住回憶」,照片對過去描述是遙遠,照片裏所顯示的內容是概念性的、模糊不清的。照片的出現在於懷念過去的材料,但未清楚說明過去為何值得,也就是對過去更詳細的觀點描述。這並非是孤例,例如《骨妹》在重構過去時,正正是嘗試為觀眾重新構建一個生活艱難(女性在按摩店謀生)也值得讓人懷念的過去,然在《骨妹》內,懷念這件事本身就是原因,主角最後是決定要回重新回澳門生活,畢竟不覺得在未來美好就不會回來。
以上的作品,當中的《痕跡》、《沙漏愛情》、《骨妹》三套是長片。創作者都是相同的年齡層,儘管受敎育的背景並不盡相同,然而他們都是在長居並在澳門成長的創作者。他們都在作品都直接或簡接地透露出,人與城市的關係,更不約而同地直接提出「留下還是出走」的命題。這個命題輪廓逐漸清晰,答案卻有所不同,如《骨妹》非常清楚,給出「最後還是會回來」的答案。有的卻越來越模糊,例如《痕跡》的男主角出走,究竟是應該歸類於他是外地人不能在澳門生活而出走?還是他厭倦了博彩業,面對戀愛不能「正常生活」而出走?如果是後者,是不是他的焦慮也可以歸入從事相關行業的人也有同樣的焦慮,而不是限於他是外地人難在澳門生活的類別?本地作品透露出創作者充滿難以梳理的感情,彷彿回答了朱佑人《亞明的澳門》裏的問題︰「唔知將來的澳門係點嘅呢?(不知道將來的澳門會是甚麼樣呢?)」,這個「怎麼樣」不只是純粹的生活方式,不只是硬邦邦的經濟、社會制度、工作就業等轉變。這答案更在於心理層面的探究。回應好像就是︰「我們還不知道該怎麼樣。」不只是︰「我是澳門人該做些甚麼?」或「我們是怎樣的澳門人?」的追尋,更多的是︰「我們在這裡幹甚麼?」、「我們要不要留在這裡?」之類的答案。
我嘗試用同樣是澳門作為題材的香港導演作品去比對。有明確商業目標的香港書寫來拍攝澳門的作品,如《游龍戲鳳》(劉偉強,2009年)純屬一個商業的夢幻歡愉故事是否發生在澳門其實不太重要;又或者《青洲山上》(張經緯,2015年)也就準確地描述一個博彩業城市的家庭關係和城市人的生存狀態,無助和絕望的情況。
當然,近十年,科技發展、澳門青年所選讀的科系、放映的技術、放映場所等等,都不能和2009年《奧戈》年代相比。澳門的影視作品已經與《論盡媒體》2014的統計無可比擬。當年我大多都看過,但現在很多拍攝後的放映,憑觀眾一己之力幾乎已經來不及觀賞得盡。
另外,在近廿年來,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長片或短片,諸如《鎗前鎗後》、《夜了又破曉》(編導許國明)、《過雲雨》(編導陳嘉強),《堂口故事3•見光》(編導周鉅宏)、《撞牆》(導演孔慶輝)、《上膛》(飛夢映畫)等等,當中更有的作品奪得各種殊榮,但礙於本文主旨,暫不討論,留待將來有機會再作討論。
亦正因為同期有很多各種不同題材的作品湧現,或許這個「留下還是出走」的命題,可以視作為「階段性的」、止於數個創作者的,對澳門的質問。如果只有上述幾套,其實討論也勉強地可適可而止。但如一而再、再而三,同一個命題不停出現,這已經不可能是我對這個命題的一廂情願的認識了。
在《2019澳門之年》的出現,我更相信「要留還是要走」是一個世代或一個城市的創作人對社會觀感和焦慮的延後呈現,應該可以是澳門電影創作者的集體情緒。
《澳門之年》——一場持續了20年,「是去還是留」的情緒延伸(五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