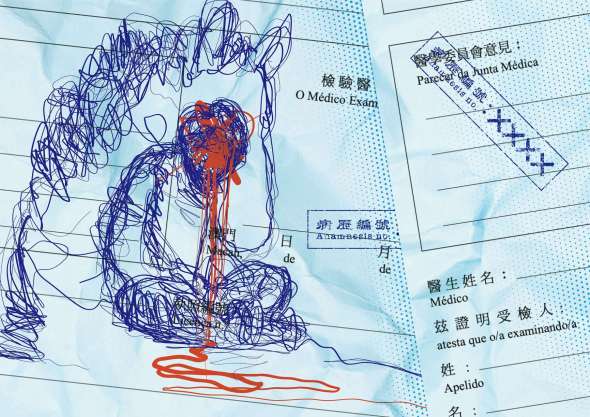《海鷗》劇照 (由文化局提供)
「時間是用來流浪的,肉體是用來享樂的,生命是用來遺忘的,靈魂是用來歌唱的。」
──吉卜賽歌謠
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鄉下莊園一群自怨自哀者的人間劇場,變身為二十一世紀初冰島度假屋一群不上不下文藝工作者及中產階級的浮世繪。穿越一百年的物質景觀和社會焦點,找到新的連結點並轉化出新的舞台象徵;成長與職涯遊走於歐洲、美國、俄羅斯的新銳導演雅娜.羅斯(Yana Ross),向我們展示了所謂「經典當代新詮釋」,可以是怎樣一場大膽的冒險。
在瑪莉亞說出知名開場白:「我在為我的生命服喪」之前,二十一世紀冰島版《海鷗》先讓康尼如當代憤青悒鬱暴躁地在舞台上遊走;他聽英文流行歌曲,讀村上春樹、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愛搖滾爵士鼓,不站肥皂箱而用錄影機「見證社會的不公不義」。憤青康尼對鏡頭咆哮他對冰島政府驅逐吉卜賽人的不滿:「他們被趕走了!他們流離失所!他們無處可去!」——吉卜賽人是當代歐洲的「海鷗」象徵?正當我狐疑猜想之際,度假屋內的中產份子已紛湧而出,「享受大自然」。
當然,劇院舞台上不會真的「自然」,只有仿毛椅墊、烤肉架、塑膠盆景和砂岩牆垣等「偽自然」物,一如「度假」這個工業時代產生的人造概念。瑪莉亞並沒有一身黑色喪服,卻圍裹帶吉卜賽風的格子大披風,在喋言濫飲喧鬧中吐出那句經典抱怨,像半醉的一句咕噥。暗戀瑪莉亞的教師西門仍滿口講錢,但手上一直把玩著足球,彷彿新世代瀕貧青年的休閒時髦配件。以前衛戰鬥姿態對待藝術的康尼嫌「劇場」老套只玩「表演」,並用搖滾爵士鼓伴奏。一夥人左等右等、胡鬧打發了好一段時間,康丁斯坦的演員媽媽伊蕾娜終於出場了。毫不遮掩的傲慢、自戀,對別人的表演漫不經心,最後以接聽手機中斷演出⋯⋯

《海鷗》劇照 (由文化局提供) 2
契訶夫《海鷗》是寫實主義(Realism)戲劇經典,但卻不是「典型」的寫實主義戲劇。他的劇中人群聚而無所事事的模式,大大違反傳統戲以事件衝突而推進行動;但又顯得生活氣息十足,迷人閒談著關於人生、藝術、青春的漫想。他們到底是在台上做戲還是在舞台上生活給人看?經常是後來者演繹契訶夫的難關。羅斯和她的團隊在舞台上創造了一些新的事件——搖滾烤肉派對、卡拉OK競唱、玩遮眼扮貓、拋靴遊戲等——當代人「無所事事」的方式,讓演員重新「生活」在舞台上,看似動線散漫實則節奏流暢。第一幕有場戲中戲,那段充滿名詞與概念而缺乏行動性的知名「前衛」台詞,導演羅斯乾脆讓女主角妮娜躺著說,表演空間就是她身體下的那條長凳,「觀眾」往往會不明就裡把屁股或腳擱上了「舞台」——幽默反諷「『前衛』就是叫一般人看不懂」的成見。「觀眾」們頭戴電子儀器,觀賞過程中腦波被傳回多媒體呈顯,恰與幾天前德國前衛團體「里米尼筆錄」(Rimini Protokoll)來澳門做的《聽你的.走我的》相映成趣——當代藝術與日常的界線不斷被提出質疑,往往戲劇行動者就是觀眾自己。
經常被塑造為天真、柔弱、無辜的角色妮娜,在這裏呈顯為嚮往藝術而大膽言行的高大女郎。背空的服裝讓她的性感外溢,第二幕她甚至搖著七彩呼拉圈小丑般進場,露骨地凸顯她把握機會表現的心態;這是本劇對《海鷗》原作「解讀」後的進一步「轉譯」。狂野亢躁的表演方式,容易流失的暗通款曲細節,便以康斯坦丁手搖攝影機去坦露劇中人的凝視對象,幾乎像是視覺化的潛台詞。第三幕瑪莉亞與西門的結婚、成名暢銷作家B.T.與妮娜的通姦,從對話中的事件變成現場行動,在卡拉OK派對(全是英文流行歌曲)的迷醉氣氛中,康尼與母親的愛恨糾葛以摔跤似的「行動」暴烈地宣洩出來,但同時也消解於誕樂;如同瑪莉亞對單戀的絕望、伊蕾娜對青春的戀棧;無濟於事,無法面對,只好繼續放逸,麻痹度日。
第四幕除了「行動」以外還增添新地「角色」:杜利醫生從遠東旅行中帶回一個泰國女人,宛如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典型:平靜、安嫻、無私;尚未知「東方」能為西方個人主義的末路帶來什麼救贖,康尼的生命已迫不及待走盡。滄桑中年的妮娜與年輕無畏的妮娜同時出現在康尼面前,此時舞台場景轉為心象化,幾乎撤空,水洩舞台,汪成一灘湖似的,康尼在水上滑行,最後溺斃自己——取代了原著的持槍自戕。原本的描繪是:幕後槍響,醫生進去檢查,善意謊言回報沒事,一面交代人把康尼的母親帶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轉到二十一世紀的版本,整個事件化為一部錄影機器,在某個角落觀看中「見證」了康尼對生命最後的微弱控訴與省思;但只見醫生手指輕輕一鍵,delete,刪了。死有輕於鴻毛,這不是悲劇,但令人思之愀然,久久難自已。
契訶夫以筆代手術刀,對劇變時代下自詡進步又徬徨失措的小知識菁英,一面以寫實筆法精筆細繪,一面以淡嘲取代激烈批判:他們如此感性耀眼,卻又輕如鴻毛;他們渴望自由、夢想、真愛與美,卻又談不上壯烈犧牲,只落得玩笑般的遺憾,化為時代的浮沫。與後資本主義消費時代的輕盈,似乎一線之隔而已。有報導稱導演雅娜.羅斯是「契訶夫的翻譯者」,但她的《海鷗》不僅僅理性「翻譯」時代,更具凝視當代的企圖。手法看似衝撞、暴烈、絢爛浮誇,卻巧妙地捕捉到那種晃蕩在輕憐與深歎之間的微妙情愫;而這,正是契訶夫作品最雋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