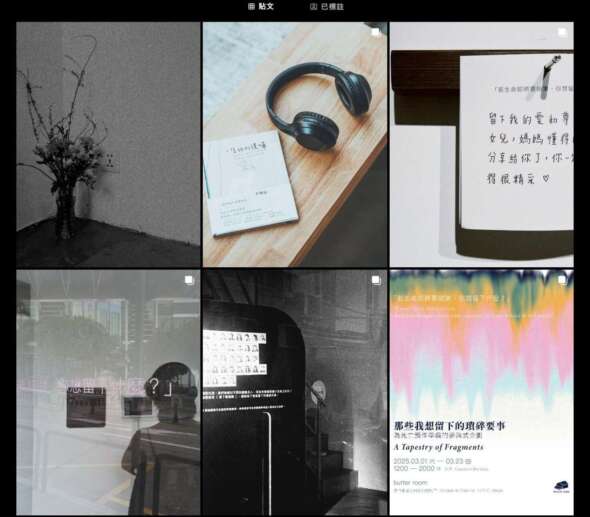自有記憶以來,我幾乎每天都經過愛都。然而,我似乎從來沒有問過,她到底是誰。
當然了,儘管每天清晨站在同一位置上打掃的都是同一位阿姨,同號碼巴士上的司機個個熟口熟面,可是年復一年,你就是不會想到要問她們是誰。可是然後你想起了,喂,你的問題不對勁,愛都不是人。
對,愛都不是人,然而在被人類創造、利用和詮釋的過程中,它會產生人性。若把城市比作野比大雄的房間,放在裡面的豆沙包會使你想起誰?你會想起叮噹。就好像看到漫畫書時會想起大雄、看到曬衣架時會想到大雄的媽媽一樣。從歷史資料的角度來看,這推論並不對,說不定豆沙包是大雄的午餐,而漫畫書是媽媽買給大雄的,至於現在正在後院曬衣服的,其實是叮噹,更何況衣服全家都有份,怎能說只代表媽媽?然而,若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在特定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下,所有事物都會被賦予了特定的人性。
城市亦復如此。如果城市是一本書,那建築物就是當中的角色,而身為作者或讀者的你與我則在不知不覺間賦予其生命力。
可是,這些年來都沒有人想知道愛都是誰。這也難怪,那是我看過最落魄、頹廢、空洞的建築,其生命力彷佛已完全流失,被附近那棵茂密的細葉榕吸收殆盡。從對面那塊像是太陽能發熱板的白色廣場走過來,沿著破舊不堪的紅色牆身走到那座陽光永遠無法照到的神壇時,你會覺得整座建築物的外牆透出陣陣寒意。愛都像個空的蝸牛殼,曾充斥在其中的歷史亡魂早已散失在空氣之中。
然而,這陣子,愛都又活過來了,彷如迴光返照般,就在它性命垂危之時。在唇槍舌劍之間,愛都的輪廓變得清晰銳利,重新有了臉孔、有了角色、有了生命。那麼,我們問,她到底是誰?
首先,愛都絕不是個「上流人」。因為,有意見領袖一本正經地說,那是供上流人士的下流場所,因此沒資格繼續存在下去。接著,當我們像品茶般慢慢細味這句話時,我們會發現愛都不只是下流場所,而且是唯一的下流場所,是導致澳門變得下流的唯一污染源。不然的話,當我們要抹去下流的集體回憶時,為甚麼只獨獨拆掉愛都,而不用一併拆掉那些好色貪婪的上流人的豪宅、為甚麼不用一併拆掉准許這種下流勾當的澳葡總督的官府?顯然地,澳門變得下流,完完全全是因為愛都這個下流的傢伙到處播毒。一旦拆掉愛都,上流人就會重拾體面生活,澳門就會重新變成聖城。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回答,愛都到處是誰呢? 大家不妨想像如果閣下是豪客一名,挺著大肚腩昂然闊步走進愛都,你會看見誰? 你會看見莊荷、舞小姐、公關、服務員,從你的角度來看,正是這些林林種種的人構成了愛都的下流。為了糊口,他們每天都得待在這座下流的建築物裡,提供下流的消遣,穿著下流的制服上班落更。至於你自己,在愛都下流了一番之後,洗過澡、穿上衣服離開後,在陽光之下又重新變成一個上流人了。所以,你本身並不是這下流玩意的一部分。
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說在這種厭女情結的語境中,愛都已經成為下流的女性身體,並被放置在肥皂劇般的電視劇情節之中:愛都是個為名為利會到處勾引無辜男人、危害社會風俗的壞女人。必須等這樣的女人自行了斷、又或者洗心革面(例如變成芭蕾舞蹈員),無辜男人才能重拾他們的體面生活。把愛都視為下流場所而毀之而後快的論述,背後的潛台詞是對那些被定義為「下流娛樂」的從業員的一種鄙視。
而這種鄙視其實有跡可尋。澳門賭收下滑,我那些從事「體面行業」的朋友,無不冷嘲熱諷,「班荷中學都未讀完就出嚟撈,一啲競爭力都冇。以前好景就話賺到笑姐,而家賭廳執哂佢地死梗啦。」聽著聽著,你會有種錯覺,好像全澳門只有博彩業從業員倚賴賭收為生似的。喂,大佬,教師津貼那裡來的?公務員薪水那裡來的?藝術贊助那來的?不都是從賭收來的嗎?如果博彩業是下流的,那直接或間接收取相關利益的全體澳門人都下流。如果拆除一座舊賭場就能夠擺脫下流回憶,那所有因賭收而興建的建築都必須一併拆除。獨獨認為賭場該為澳門的下流負責的想法涉及歧視,也自欺欺人。
可是,我們的社會似乎就是如此不懂感恩、不懂反省。我們無法接受自己的身處的社會竟是如此下流,便把下流的責任歸在一部份人身上,以此說服自己相信自己的手是乾淨的。那群代罪羔羊將來的命運,難道不會如愛都的下場一樣淒慘嗎?他們儘管人數眾多,在公共事務上卻早已失去了發言權。明明是在決定一座舊賭場的去留,我拼命翻閱報紙,找到的都是政府如何諮詢了藝術家、青年領袖、教育界的意見,但身份更相關、人口也更多的界別如博彩及其他賭場週邊娛樂從業員的意見呢?我們的社會,似乎只有在涉及莊荷權益時才會想到讓莊荷發言,似乎已不屑地假設了這群人不會關心個人利益而外的公共議題。
不幸地這還沒完。愛都除了是個下流的女人,她還是個下流的老女人。大家要知道,我們的城市對古建築可是照顧有加的。可是愛都並不「古」,她只是「舊」。「古」是古意盎然的古,能吸引文青們攀山涉水前仆後繼跑來打卡拍照。「舊」是殘舊不堪的舊,老而不死、每天篤眼篤鼻、毫無意義地佔據空間、阻礙社會進步、老眼昏花流膿咳痰純粹等死。為甚麼不趁早自行了斷?愛都是座舊建築,因為它只有六十幾年的歷史,沒有經歷過偉大的抗日時刻、沒有住過像孫中山和葉挺之類的英雄豪傑、也沒有為澳門帶來輝煌世紀—在澳門,如果下流不算罪,那下流卻賺不到錢就肯定罪大惡極了。愛都被指控以毫不起眼的角色經歷了澳門某個毫不起眼的「過渡期」,然後隨著年月的逝去而臉目全非。現在其命運只得任憑年輕人的處置。這難道不也是我們這些平民百姓的宿命?有天你垂垂老矣,發現你充滿回憶的地方已變成一座為青少年而設的文娛中心,而這個改變過程是在一個只設教育界專場而不設老人專場的行政程序中完成的。然後你定必發現自己不是這座城市的一員,儘管在非常抽象的意義上,你仍然是公民。實際上,你和你的回憶卻早如愛都一樣被埋葬在歷史的垃圾堆裡了,而你得到的交待,沒錯,是對老人家最殘忍的一句話,「有回憶並不代表有價值」。
最後,我想再回到野比大雄的家裡去。大雄的儲物室很小,但還是一直藏著嫲嫲送的不倒翁、已移民多年的幼稚園同學送的煮飯仔玩具、以及大雄爸爸的零分測驗卷。你只要一打開這樣的儲物室,就會知道這是一個你能夠安心終老的家。因為這裡的取捨並不只取決於資本主義的效益考量,而是有著對於「家」的價值的考量,而是有種對於生命的重量的承擔。若果有天家裡添了小孩,而必須選擇拋棄甚麼的話,那被拋棄的想必會是洗衣機是電視機而不會是那個已經失去工作能力奄奄一息的你。
然而,如果一座城市決定建築去留的考量是它有多輝煌、有多上流、而不是它有多反映那些佔人口大多數的低下層老百姓的生活時,那麼這座城市就向下一代傳遞了這樣一個訊息:這是一個賺快錢的地方,賺夠了就移民去別處過退休生活!不然有天你老了,不再卓越、不再成就甚麼的時候,你過去為這座城市所做的低三下四的一切貢獻都將變成這座城市把年老日衰的你棄如敝屣的藉口。「有感情但也應該要拆」,你這個六十多歲的老廢物又憑甚麼可以例外?
由此,愛都其實預示了我和你和我們社會的未來。她的生死,正如我們的生死那樣,取決於我們如何面對我們自己、如何面對我們的社會、面對我們的過去、未來、下流的現實和上流的夢想。「拆」的邏輯背後,充滿著因為把性別、階級和年齡歧視看得太理所當然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的主流論述。而如果我們最終決定留下愛都,那麼我們就留下了與這論述相抗衡的存在物,而在這個逐漸瓦解、人人喊著移民的社會中,我們說不定也會從愛都的保育中找到從新出發的起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