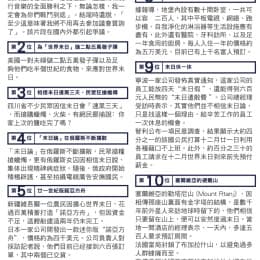與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哲學助理教授馬文寧對話
記:有「末日」這回事嗎?
馬:我不會說有或者沒有,但世上宣稱過的「末日」已多次落空,人們現在看「末日」的心態已不同以往。我個人並沒有認識,相信這回事的人,因為如果相信,一個人的行徑應該跟平常有所不同才對。
記:那為甚麼大家都異口同聲說2012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
馬:說它是流行的集體現象更恰當吧,就像過萬聖節一樣,大家都喜歡把「末日」掛在咀邊,卻已經欠缺了一份真正的「相信」,可能人們很憧憬去相信,但認為沒有可信的,人們不再信有完美的烏托邦,反而寄望有徹底的衰敗和終結;這可能基於持續的失望,人們更寧願想像,也不願意再相信。反而真正叫人感覺如「末日」的,往往是在最平靜、最意想不到時發生的事,例如911襲擊及日前的校園槍擊案。
記:那麼「末日」對我們還有甚麼意義嗎?
馬:任何一種宗教系統都提供社會免疫功能,末日信念也不例外,它可以令大家相信,這不是僅僅一個個人問題,從而迫使我們要做些甚麼改變,也預備我們去面對突如其來的改變。假設世界末日了,我們會把自己放在人工的緊急狀態中,正如看到自己的人生突然變得代表性和有意義起來時,我們會重新審視人生的優先次序、挑戰自己既定的價值觀,例如到底是金錢物質重要,還是活得快樂最重要?以往人們面對「末日」,會求神拜佛悔改,但道德觀念下降的現在,人們不再相信是道德敗壞的終結,反而覺得是環境破壞、世界大戰、飢荒等帶來的惡果。但與其說「末日」是神對人的懲罰,那為何會在二千多年前就決定了今日要懲罰人呢?這個說法又好像不合理。人們也嘗試解釋,瑪雅人為何沒有寫2012年12月21日以後的事,其實像電腦程式一樣,未計算到那裡也不代表就是「終結」。我常記起一個玩笑:「今時今日,相信有世界末日,比相信有資本主義的末日,來得更容易!」
記:那麼「末日意識」帶來甚麼正面影響嗎?
馬:是的,其實「末日意識」是好的,正如我每次坐飛機,也會跟自己說「若然飛機五分鐘之後發生意外,我有甚麼該做而未做的事嗎?」,也正如每年年尾除夕倒數,都是某程度上一個「小型末日」,所以「末日意識」,就是叫我們集體思考,「要去做啲嘢」,同時更可因此團結世界,因為我們可以做甚麼,遠比那天將會何時到、怎麼樣,來得更重要。記得有一套關於末日的電影提到,那些平日生活上一團糟的人,面對末日反而平靜自在,但平日生活很有條理的人,卻完全失控,這會令你想到甚麼?就是對人生的掌控權!華人社會可能更受鬼神慱統影響,對「末日」這些概念較惶恐,但事實上近年的統計反映,中國人是世上最樂觀的,日本人則最悲觀,或許跟近年經濟發展有關吧。至於澳門,同時集宗教和博彩中心於一身,早於1938年,英國詩人奧登寫了一首叫《澳門》的詩,提到澳門充滿著所謂的罪和祝福的矛盾,倘且沒有發生甚麼大災難,因此沒有擔心更多的必要。
記:對於「末日」前夕,人們出現很多反常行為,你如何理解?
馬:對於「末日」,反正沒有更多可失去的,故人們可藉此機會,令平常一些「不合理的行為」,更加合理化地進行,只因為活出不尋常的自己,需要更大的勇氣!只要不是傷害他人的事,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