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的出版當中,有關藝術類的書籍,撇除掉翻譯類的著作,《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這本書應該在華文的藝術書籍撰寫中屬非常特別的一本,為此亦贏得2022年數個出版獎項,包括「2022 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
此書牽涉到的面向頗多,既是與當代藝術史、公共藝術密切相關,尤其二十世紀二次大戰前後德國的公共藝術/雕塑作品與德國公共空間的藝術實踐,也是對於歷史如何被書寫、被形塑所進行的反思,對於作為紀念物的藝術作品,如何面對/摘取記憶,如何記錄/形塑德國近代歷史進行審視與研究。
在這些橫跨藝術、歷史與政治的不同面向中,作者聚焦於德國在二戰期間所建立起來的眾多紀念物/碑,以及它們作為「超克過去」或「處理歷史」(這是德國用語,台灣稱為「轉型正義」。德國這兩個詞義與台灣的詞義分屬不同思想體系,詳情請閱書內說明)的文化實踐案例,來展開其研究。記錄在此書中的,也並非只有「成功」的「模範」案例,而是作者以其高度的批判性,來審視德國通過設立紀念碑/物在「超克過去」方面所進行的文化實踐。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作者:鄭安齊。
紀念物/碑的誕生,是一種特殊的建構,與其所在地人們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態勢密切相關。它往往承載了大量的訊息內容,可以是一種政治威權、國族主義,或一種文化認同、一種(想像的)共同體的形塑;也可以出於民眾集體的情感宣示與精神寄託,或是主導者對歷史造成某種干擾的企圖,一種話語權的搶奪往往因此而展開。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 )在其著作《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ire)中便以「應該如何書寫法國史」為全書核心。他認為歷史書寫所要記錄的並不只是過去的事情如何發生,「而是瞭解它如何持續地被利用,它的應用與誤用,以及它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史學家要書寫的「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書中也提及諾哈將記憶分為兩種,一種是「活的記憶」,隱於行為、習慣或者身體的知識中,以人為載體,另一種則為「檔案化的記憶」,這種記憶若其內在體驗愈稀薄,就愈需要外部有形物的存在以維繫記憶的存續,「之所以有記憶之所,正是因為已經不存在記憶的環境」,而記憶所繫之處需要同時既是「物質的、象徵的,也是功能性的」,他認為這三種意義所佔比重可以不同但必須同時存在。
在公共藝術的建立過程中,儘管其所採取的藝術形式與技術等各自有所不同,但政治的介入甚至主導,影響著藝術家所要採用的美學策略(無論正反),一個公共雕塑往往就是在這些不同張力的拉扯下而形成。這些具有「公共性」(在非民主地區則與此無涉)的藝術作品也會隨著歷史的發展、政權的更迭,而出現不同的有關「文化記憶」的演化。作者同時也指出,「文化記憶」即使一旦形成,也不會自動傳續下去,而是需要有賴於「一再的重新商定、確立、傳介與習得」。

作者在序中表示,「超克過去」是一個德文語境中特殊的概念。這個複合字的直譯可理解做「面對」或「克服」過去。
德國的紀念碑正好體現了這個國家動蕩的歷史發展,從右翼的極端國族主義與威權主義,到戰後初期,冷戰期間,西德因「超克過去」的工作遭到擱置而反而對納粹時期避而不談,東德則與其他共產政權相若,以「反法西斯」為主調,只頌揚其受難的左翼政治人物,而對大眾的苦難視而不見,無論是「英雄化」還是「妖魔化」,都離真實的歷史很遠。幸而德國自七O年代末,民間組織開始了倡議行動,加上政策呼應,歷史的發掘與反思開始形成,不同藝文形式介入紀念行動便開始啟動起來,而話語權與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角力也更形複雜。此書即以此舖陳其研究。在考據不同時期紀念碑/物、展覽與藝術行動等的出現,如何被推動建造,以及其所使用的藝術形式,背後整個歷史脈絡以外,貫穿全書的是對於「超克過去」在文化實踐方式上的困難及其複雜性進行探討。
除了種種政治權勢上的角力,在今天還有更具影響力的是對於資本與消費行為的全面擁抱,使這些紀念場所/物件無法避免的被「觀光化」與「旅遊產業化」,使其原有的紀念與反思被剝離,記憶的力量被概念化,柏林圍牆的地景幾乎完全消失,剩餘段落成為觀光化的紀念物,周邊販售著實質上不具有任何歷史意義的圍牆「紀念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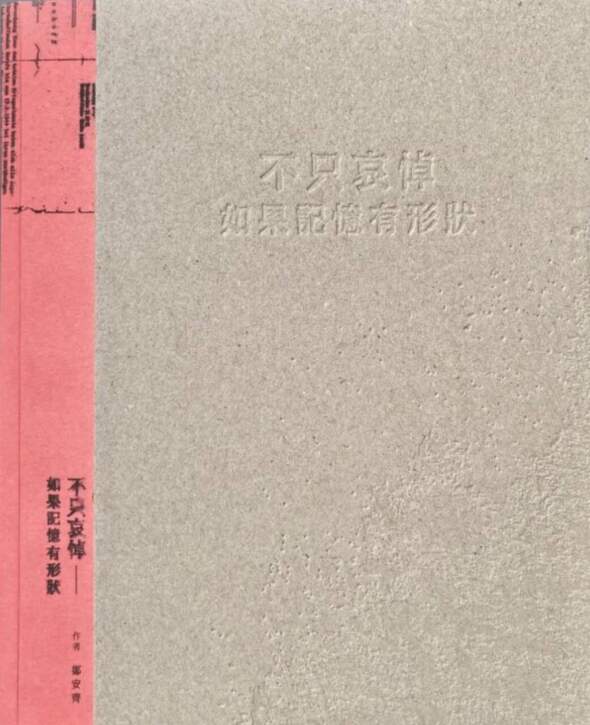
作者指,書中的案例絕非蓋棺論定之作,他們往往回應了過去累積的論爭,但隨即又開啟了另一端的論辯。
書中其中一例即為此中典範。有些藝術家趕在柏林圍牆地景消失之前,策劃了一次名為《自由的有限性》的展覽,其中一件由漢斯.哈克所作的〈現在起可以小額贊助自由〉,對於以柏林圍牆為象徵的社會轉變進行毫不留情的諷喻與警醒。他改裝了原設置於東德圍牆邊上,用以搜尋越境者的探照燈站崗,在其頂端原探射燈的位置架設了賓士標誌的旋轉燈「梅賽德斯之星」,並裝上東德建築經典樣式的玻璃,但在玻璃前方則裝上西德鎮暴車用的鐵柵。塔的兩邊則鑲嵌上兩句取自賓士的廣告詞:「準備好就一切泰然」,以及「藝術歸藝術」。作品警示了圍牆的倒塌雖然終結了一方的覇權,但資本覇權亦乘時而起,並且往往在地方政府與人民的助長之下,形成更龐大而複雜的組織結構,往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使人人皆成共犯,進行無孔不入的侵奪,甚至染指文化。這些資本財團可以通過資助文化的方式來使文化為其所用,不止為其染白,因其具有操控藝術展示的權力,更於無形中使異議者更形孤立,使用的正是「藝術歸藝術」這樣的一種看似「純藝術」口號來混淆人們的批判意識,只要不觸犯政治界線,賓士便可以進行「小額資助」,由此藝術家便可以得到「小額贊助的自由」。
就如法國社會學家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於紀念碑的設置,指出其「具有一特定或不確定的多重意義,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層次結構,而紀念碑的不同意指,會在特定的行動下不時輪番浮現」,點出這些藝術品/紀念物的設置並不限於對過去歷史的追思與懷緬,同時具有多重揭示與警醒的意義,畢竟在今天,歷史該如何及以何種方式被記錄、被書寫,更值得我們的關注與反思。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作者:鄭安齊
出版:沃時文化
出版年份:2022年0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