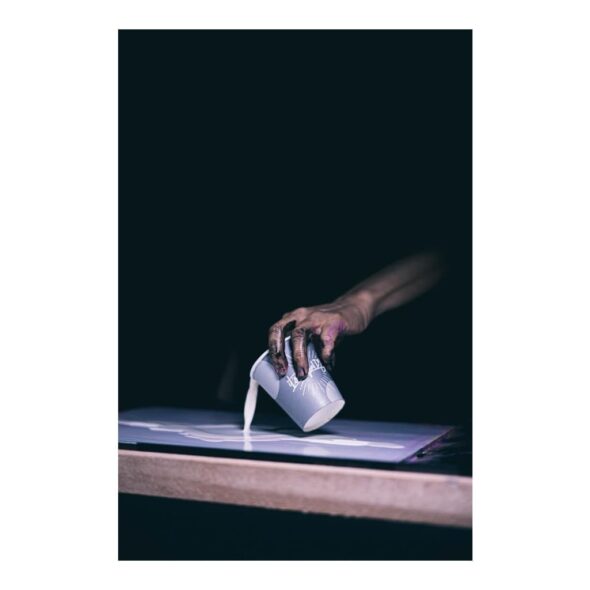在《澳門之年》這一套回歸20週年之作,每名創作者都只有十分鐘,但卻隱隱然延續了一個命題,可以上溯上文——在這個城市的人,和城市的關係,是浮動的,鬆散的,無根的,不確定的;而其情感連結卻又是非常強烈的,強烈到近似離家獨立卻又被倚在門前的母親的眼神牽著,不能瀟灑而去的羈絆。然而,「堅決」選擇留下的人,卻又止於顯示對城市鄰里的關係的持續延伸,例如《骨妹》的回來澳門再重建社區關係,和朱佑人的《最後一場放映會》為後輩放映和不停地紀錄澳門,這是顯示對社會職人責任和道德,唯暫時未見到更深層的、歷史性的紐帶關係。
關於像前途類型的詰問,例如香港《十年》類似的作品,這一方面澳門人的作品類叢中,曾有一靈光乍閃之作。2013年澳門其實有一部由霍嘉珩等人拍攝的學生作品《2049》(編劇歐志恒、霍家珩、區浩賢,2013年,長版48分鐘,短版25分鐘)。此片嘗試作出預言式的總結。故事講述2049年的澳門,即回歸後「五十年不變」的最後一年。其時,澳門人口嚴重超負荷。政府為了控制人口,頒佈了一項殘忍的「減少人口政策」。在香港還沒興起學生運動時,澳門的學生已經對自己的前途嘗試作出極度悲觀想像,片中有像疫情時押送市民離家的畫面,去留已經不是一個選項,是唯一一個被安排的結果。被強制滅絕的吶喊,更甚於被異文化或別的生活方式強行同化的焦慮,更加殘忍和粗暴。希望有機會能夠再在公眾面前出現。
的確,彰顯在澳門錄像/電影工作者的作品之中,這種「留下還是出走」的心理,說到這樣,已經不可能是巧合,可以說是一種普遍性的集體的情緒了。它一直圍繞著在澳門生長的人,特別是受到鄰近地區近日發展的社會運動的因素所影響,香港有不少有重新考慮留下還是移民的問題,不多不少影響了澳門人的情緒。而不能斬釘截鐵地決定去或留,我認為是創作者對澳門明顯有一種羈絆的同時,「外地」對於他們而言卻又是失語的——眾多澳門作品之中所描繪的「外國」,是面目模糊的,只是一個「出走澳門的目的地」,所指的外國是加拿大或是台灣其實分別不大,地點可被置換的程度非常高。因為作品的內容都只多於集中在與澳門關係的描述,鮮有提及任何「外國」的細節。回到澳門描寫彼此關係之上,又找不到屬於自己在澳門精神的支柱,這一點在上述所有作品之中時有散見。
創作人的視界對過去,牽扯著茫然回憶、沒有細節、乃至正邪屬性不定的羈絆的存在(如許國明《夜了又破曉》、《鎗前窗後》描述的澳門、及上文提及《骨妹》,涉及男女肌膚觸碰的生意在澳門來說是尋常工作,卻又拍出溫馨的感情),顯示出一種對過去認同的焦慮。依從這個脈絡,觀眾一再對自身城市的未來和自身的位置的模糊而又強烈的羈絆,並且一次又一次的互相確認。這種無根飄零感,暫時未能完成褪變。另外,就是城市面貌急速變化改頭換面,甚至街道的景觀沒法完整地保留使大眾覺得物是人非。例如在《澳門之年——最後一場放映會》中,少女的家族麵包店的關張,與「導演」的放映空間準備關張,這樣雙重消逝,更加重那一種「留不住在澳門的根」的感覺。兼且本土的文藝作品,還未形成普及地傳播和討論,當電影人沒法找到屬於城市的反饋,便更難再反覆補敘、深化下去。
可能在於澳門本地創作,只集中在這二十年間陸續出現,以及創作者年齡及個人經歷等原故,這些作品的歷史觀之中,大多涉及到澳門回歸,對於澳門回歸以外的澳門歷史事件鮮有提及,可以說是最深刻而且珍貴對「回歸」的延後反應,但卻又成了作品的框架的局限。此外,在文化圈高度並置又或重疊的澳門,探討「回歸」或者「留下還是出走」的視界卻又非常不同。例如,《澳門之年》中,杜健康、António Faria、周鉅宏都就差不多的問題提出了全然不同的方向和答案。然而,觀眾卻不可能三種方式全然認同。觀看者認同了其中一個,那是不是另外兩個方式來會否定自己?還是體諒接受?亦或三者都瞭解和體諒?這種涉及不同身份認同的文化選項,很難非黑即白地馬上給出清楚的答案。
關於作品對過往的聯繫,順著這個脈絡,我想用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的《記憶所繫之處》作結。對法國人來說,馬賽曲、聖女貞德、自由平等博愛、艾菲爾鐵塔,是法國人心裏共同的交匯之處,然而在每個時代,他們的意義都會被重新定義,每一次的觀看艾菲爾鐵塔,或者不管在戲劇甚至廣告上看到聖女貞德,都會產生記憶。最後這些重要的,不管是物質還是非物質,成了國民的記憶聯繫的連結。在這篇文章所指,就是在現在的戀愛電影館所收集和放映的澳門電影作品。
容我引用《記憶所繫之處》的一段︰
「……我們不探究往事如何發生,而瞭解它如何持續地被利用,它的應用與誤用,以及它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我們要追問的不是傳統,而是它如何被建立、被傳承。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所以,這確實是某種法國史,卻屬於不同的層次。」(《記憶所繫之處》,P.19)
這些澳門作品的存在,對創作人可能是拍攝的經驗,對創作團隊可能是圓滿的喜悅;對首演的觀眾可能是觀賞日常的熟悉面孔所參與演出的愉悅;對於二十年、三十年後的觀眾而言,他們可能會覺得「以前的老澳門就是這樣子」。同一事件,在時間的長河裏,會有不同的功能和記憶的生成,但都被這個事件——澳門的電影作品,去一直串連下去,才形成了我們——這個城市的主體與獨特性。
澳門人「留下還是出走」的集體情緒,在電影作品裏延續20年,日後如何,還待觀察。然而這些作品的陸續出現,正正就是充當著「再記憶」的功能,可以顯示出更多的細節。羈絆即使再怎麼被確認,無根的感覺或許可以減退。也就是說,對過去的細節更多、更明確、更清楚,論述的面向更多,虛無的羈絆可能會變成強而有力的對城市深處的精神紐帶。
建立了清楚明確的精神紐帶,肉身是留還是去,可能未必會是一個問題了。
《澳門之年》——一場持續了20年,「是去還是留」的情緒延伸(五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