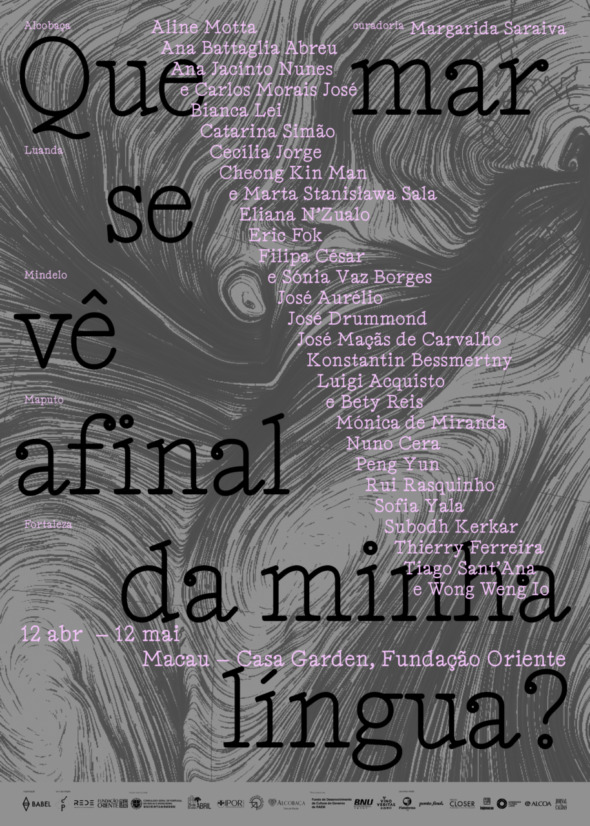(編按:2019年的10月、11月,綜合媒體報道,再有香港藝術工作者入境澳門時被拒。當局給予的理由是「存有強烈迹象顯示,利害關係人企圖入境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危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活動」。
社會有聲音質疑是因為近期的政治氛圍,也有人擔心會限制藝術交流自由。臨近主權移交20周年紀念日,編輯組憶起了1999年的回歸前夕。本文由編輯組於《碇石二十— ── 石頭公社藝術二十年》1一書中選段重組併合而成,簡述1999年12月19日晚上藝文界曾發生的一件事:當晚,澳門一個藝術團體石頭公社組織了一場在街頭行進的演出,原設定於幾個公共空間中進行即興的街頭表演,然而演出隊伍行進至議事亭前地一帶時即被圍捕,有十三名本地及香港藝術工作者被帶走,拘留一夜後才被釋放。《碇石》在多年後重訪多名參與者,重述當晚所發生的事。標題為編輯所擬。
回首來時路,只為盼記得過去,只為從多角度討論澳門。)

據《碇石》所述,1999年12月20日凌晨,其中一位被帶走的香港藝術家並無表演,只是觀眾。莫昭如等被釋放後,回到議事亭前地執拾。
莫2:(…)哦,99回歸當晚。當晚一行好多人,郭達年、尊子、傅老炳、Jennifer本來想做一個Traveling的performance,由一個點去另一個點,每個點都有些關於歷史的段落發生。很即興的,未曾事先寫好或談好,每個定點做一些表演。出發步行後第一站是在大三巴?我們帶了大木偶,去到那個叫甚麼? Leal Senado,就有警察行動,很快,從四方八面來捉我們,有多少人被捉走?
J 3:該是共十三人。
莫:當時是已經回歸了。
J:已經過了十二時。 (…)
Nikita 4:(…)可能我對社會真的比較遲鈍,我只想著做演出,沒想過會發生這些事。(…)但到出發的時候,我記得我當時要戴著一個道具,是尊子畫的江澤民頭像,我們都不知道道具是怎樣的,當晚才分發,我戴上的是江澤民,要向途人揮手囉。在我角度來看我不會覺得有些甚麼政治敏感。直至走到大三巴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有人會拿著相機在我的道具底下往上拍?當天比較冷,我剛好穿了一件好長的樽領外衣,衣領一直遮到鼻子,只露出眼睛。也許因此他們一直認不出扮江澤民的是誰。接著當我們走到噴水池,就有一個女的便衣走過來,不知問我些甚麼,我說是,她就即時要拉我,她一來拉我時就另外有兩個便衣男人來拉我旁邊的誰,我就聽見阿樂(Candy的男友)好大聲叫為甚麼捉我女朋友?場面很吵,那個Madam本來想把我也拖過去,被我一手甩開了我就馬上逃掉了。當我回看整個環境,才開始意識到正在發生甚麼事。(…)
Jenny 5:(…)當晚在大三巴,我第一個被一個西裝男人拉到一旁問我是誰,我就大叫,香港那班人走過來,那男的馬上鬆開我。其實那人的表現算是友善,還說:「叫你們的同伴散開」。我就大叫有警察,我還跟他說阿sir我們在做演出。但我很肯定他不是澳門警察。

據《碇石》所述,1999年12月20日凌晨,其中一位被帶走的香港藝術家並無表演,只是觀眾。莫昭如等被釋放後,回到議事亭前地執拾。
奮6:(…)我們在街道走一走,覺得那個氣氛很怪。因為我做過記者,我就見過那些警察躲在一邊講話。後來就拉人了,拉的都是香港的朋友,那時大家就覺得,嘩! 有沒有搞錯?一來是很擔心,二來是有種……震撼感。剛好和回歸的那種氣氛是完全兩回事(…)
Lenny 7:(…)澳門怎樣呢?我還記得回歸那一年發生了那件事(回歸當晚的拘捕事件)理解他們是澳門新華社的人,他們逐個幫你們拍照。我也有相機,我已表露身分,但他不敢表露身分。我學他一樣拍他,他便開始害怕了,他不知我是甚麼人,便害怕我會拍下他的模樣,找出他的身份。所以他逃跑,他一走便有很多記者以為發生了甚麼事,追著他來拍。我向記者說我們在面對回歸的監控。好吧,其實他們是需要做一個記錄,記錄低澳門回歸那一晚有誰過來搞事。然後大約十分鐘不到的時間,兩台小貨車出現,有一群澳門的……便衣嗎?還是警察?說這個人,那個,跟那個都要捉回來。(…)
Lenny:(…)但警察也看不到我有甚麼特別,所以在清晨便把我們全部釋放。其實我們只是在一邊走一邊打鼓而已,為甚麼值得我們每個人frame來拍照呢,我覺得對我們freedom of movement,freedom of expression的一種入侵。但這樣也能看出澳門的監控存在。(…)
莫:(…)在入邊無甚特別,也不慌張,就是後來要逐個拍照,打手指模。就是我們在澳門警方的檔案中有個記錄。後來我要去澳門的話,有時不能入境,有時又讓我入境,有一段日子是連續三次不讓我入境,我便決定以後不再來,是你的損失嘛!哈哈!(…)
J:(…)被拉走的大部份是做演出的人。尤其緊接的時間裡影響是很明顯的。99年的事件之前我們在香港藝術中心麥高利劇場做了《後太平天國之天國近了》,當然很想在澳門再做一次。事件發生之後就很明顯的覺得這個演出應該做不成了。 一來《後太平天國之天國近了》有點敏感,二來又剛剛發生這件事,演員都不想在澳門重演。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勉強,要再去做這個演出好像對大家都有點難受。

據《碇石》所述,1999年12月20日凌晨,其中一位被帶走的香港藝術家並無表演,只是觀眾。莫昭如等被釋放後,回到議事亭前地執拾。
J:(…)於是另外排了澳門版。除了服裝、音樂、影像,內容亦都改了很多,流程完全不同(…)
J:(…)我想最主要是大家不想做《天國近了》而已,因為《天國近了》中其實有很多對於社會的一個……疑問? 我們直接在劇中播國歌,現在可能已經不准,我們將國歌切碎來播,有很多做法是頗挑釁的。 所以當時他們覺得在99年之後,不適合再在澳門做了。(…)
倩8:(…)我想,在開始參與演出時沒想過我必定要去表達甚麼或想說些甚麼。我想大家都是在偶然的機會下聚在一起,就一起做些甚麼,既然有人拋出一個與社會有關的問題,當時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不能碰或要迴避。既然有人拋出問題,我們大家就因應題目去想想到底我們想講些甚麼。是一個直接的過程,直接的反應。 沒想過表演者「不應該怎樣」。你說是很純粹藝術上的嗎也不是,與我們生活很貼身的,你說很政治性嗎?也不是。只是我們從一個藝術角度,一個表演藝術的方式去向觀看我們的人表達。我覺得沒有需要迴避,我們就是從藝術的方式表達一個社會的題目,就那麼簡單而已。
1. 《碇石二十—-石頭公社藝術二十年》,出版:石頭公社,2016。 2. 莫昭如(莫),香港藝術家,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主席。 3. 李銳俊(J),石頭公社始創成員。 4. 石頭公社早期成員。 5. 石頭公社早期成員。 6. 石頭公社始創成員。 7. 郭達年(Lenny),黑鳥樂隊始創人。 8. 石頭公社早期合作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