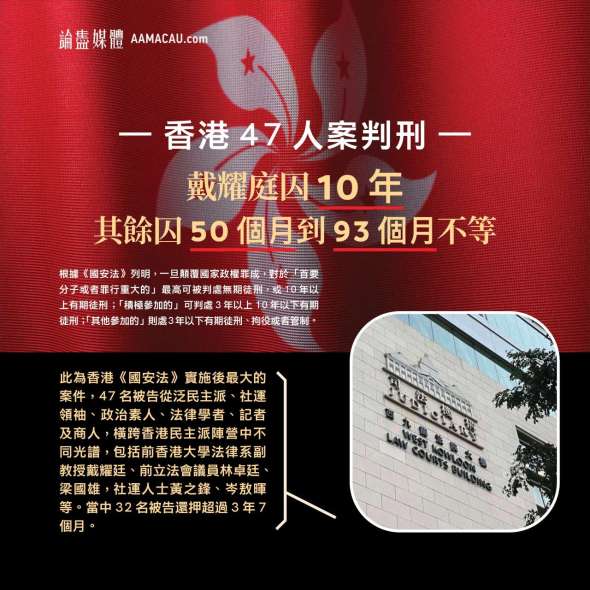示威遊行就是一次很好的民主討論,沒有世代之分。(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是一個多麼漫長的六月啊。
全世界都在觀看着香港瀰漫的淚水和血汗,跨越界限,我好幾次看着天空和雲影交織着光,從中等待黑暗再度來臨,月光和烏雲每翻一頁,凝視着細縫那擠出的暗光,映照出受傷的人淌着血泊仍高舉雙手,等待正義被伸張的來臨。我們深信沒有一個人是偉大的,偉大是因為我們都在一起。
示威遊行就是一次很好的民主討論,沒有世代之分,不管是菁英或是基層 ── 尤其中產一直被視為對社會最冷漠的一群 ── 卻再也不敢不紮根孩子的未來,大家都公開誠懇地提出堅實的討論。藉此機會,我們終於不再浪費時間在無聊的對罵中,複雜艱難的議題肯去虛心學習,沉溺創傷,高舉火炬,燃起沉寂了很久的聲音。
在極權國家,當然希望把異見份子噤聲,或從今流亡不再歸來,留下來每個靈魂都不敢再無忌憚地說話,溫馴在國家機器的震懾下,然後我們變成了政治冷感,每件發生在身邊的事都卻感覺千里之外遠。現在的一切決定,就是為了我們整個未來,我們即將活在我們手中建構出的制度基石,我想不出不發聲的理由。我們可否改變,在於你拿擴音器的手,不在那張遙遠又冰冷的那個首長的辦公桌上,每個人們的一念之間,能影響歷史,把不適合的領袖趕出房間。
在街上,我抬頭好像看到了張開臂彎的光,如果沒有法治和自由,就不香港了。
我們也都曾有過這樣的想法,要去愛這個崩壞的世界。真正絕望的不是那些年少的人,他們還能對世界懷有希望,所以抗爭,把沉睡的人逐一叫醒。年老才是最大的絕望,他們會站在台上但不再狂妄,不敢再要求世界為我有所改動,譏諷着懷有希望的人來保讓自己夢想的綠洲,享受了上世紀經濟社會為他們帶來的各種便利,他們經不起一無所有,害怕改變,改變會令他們更加滄桑,所以奮不顧身去維持現狀。
但你看那些所謂破壞社會秩序的人,我想請大家想想,你不能去譴責他們。因為他們比誰都更堅實地走在城市的路上。我一直強調,沒有人有資格去輕視他們,因為首先你要做的是先理解他們散落各處的動機,反省為什麼他們有這個抉擇。你會發現他們都脆弱且誠實,比心痛還要痛。看破了政策暴力的破壞力比打破立法會玻璃更大,他們比誰都看得更深,現在所有不公義都來自行政立法的散亂無解,全然失序。
同時,好幾個離開我們的靈魂也不會白走,我理解他們,同時他們理解我,因為我需要被同情,我知道他們渴望的慰藉,我思考他們的迷惘,我會把明天收集到的每道曙光,去替他們在睡前溫柔地關心自己,在所謂人類和他們同伴所創造的城中好好繼續活下去。
如果你厭惡他們,就如同我平時厭惡着討厭的你們一樣,因為我也厭惡我自己。
時代就像卡謬所說,角色矛盾就在歷史中不停改換身份,今天的壓迫者就是昨天被壓迫的人。歷史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但我們都無處可逃。有什麼原因能把一個人的靈魂撕裂,你要知道衝突並不可怕,可怕在於聲嘶力竭之後,原來大家根本不理解大家。
絕望生根在現實當中,我們都清楚自己是在跟運轉中的國家機器抗衡,極權且荒謬,所以抗爭在邏輯上是不太成立。我們孤獨地活在高牆之下,沒有控制權,有太多複雜的誘惑、時代焦慮,太多人妥協、廉價的背叛,每天學習面對悵惘若失。這不是一種此刻的對抗,是注定要捱過些季節更迭,先培養整個社會價值觀才能符合未來的想像。
集體的決定是隻面目模糊的惡魔,我們想要怎樣的社會,每天都用行動來投票,社會是致富了更開放了,個個活色生香,但陳舊的基本哲學還是只像鬼魅般遊走;誠然講再多,總有人覺得又夸夸其談,又把道德搬出來晾,我只區區蟻生,社會我不能負責,所以不想負責。要有改變,我想可能要等到有一天,整個國家都遵守道德不是為了畏懼公權力、被監控或受懲罰而做,是為了人格、道德、人類文明及普世價值。雖然劉曉波等人寫了《零八憲章》,陳雲飛用幽默面對「尋釁滋事」,丁子霖組成「天安門母親」,王全璋為弱勢群體利益做辯護,香港每年堅守「世界最大悼念六四的土地」。為了活下去,一切都沒有改變。
社會短路,所有人都感受到撕痛。沒有例外,而世界也只會愈來愈沉重。
但我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如民主國家般詩情畫意,在海德公園一樣的地方享受着懶洋洋的午後。
總有一天。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