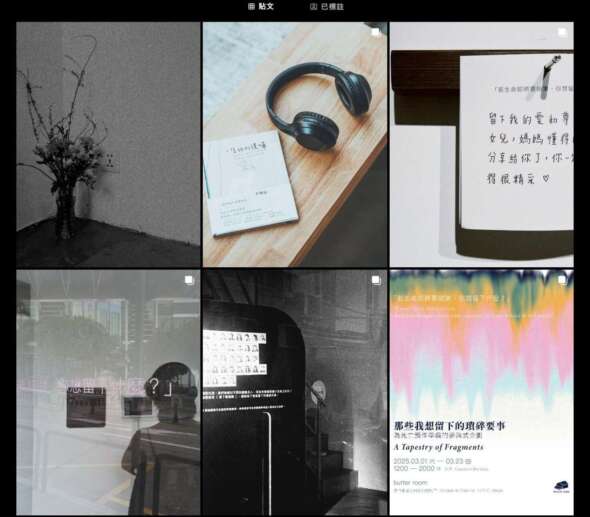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據說,在矮人國裡,每隔三個月就要更新一次地圖;這裏除了街道就是博物館,甚至連街道都成為了打卡聖地;這裡沒有遺物只有文物,沒有死亡只有活化。」這是藝術場刊對藝團「足跡」今年的演出《咖喱骨遊記2019.旅行裝》一段介紹。
「據說,在矮人國裡,每隔三個月就要更新一次地圖;這裏除了街道就是博物館,甚至連街道都成為了打卡聖地;這裡沒有遺物只有文物,沒有死亡只有活化。」這是藝術場刊對藝團「足跡」今年的演出《咖喱骨遊記2019.旅行裝》一段介紹。
「遺物」、「文物」只差一字,為《咖喱骨遊記2019.旅行裝》總導演莫兆忠,兩者有何分別?「對於我來說,遺物是死去的人留下來的,而文物反而是更加定義不名的狀態。」莫兆忠說。「有些未死的被判死了,有些死了的又不會進入變成文物,所以是更加無法定義。遺物很簡單,就是使用者已經死去了,但文物很多時是使用者未死,那件事本身也未死,但也被文物化了。」
「但現在以文化觀光旅遊發達的城市來說,將一些文物化,似乎變成了一種生存策略。」
城市在變 遊記也在變

莫兆忠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2004年,「觀光博士咖喱骨」這人物第一次出現在「足跡」的演出中,2009年《咖喱骨遊記》正式面世,對上一次以《咖喱骨遊記》作為演出名字的作品是2012年,今次是「足跡」第9個有「咖喱骨博士」的作品。這角色的原型是著名童話《格列佛遊記》,即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在「足跡」的作品中,「咖喱骨博士」時而是主角,時而是傳說,但故事總是圍繞着他在「矮人國」。
「最初寫的時候覺得,當時自己成長的地方變化得太快,很多事物都消失。雖然覺得『不捨』,但對事物的來歷其實一無所知,於是開始查資料、走舊區。」甚至有幾次,莫兆忠等人刻意角色扮演,穿上觀光客的裝扮,跟着觀光客的路線去遊澳門。「於是開始想,自己的感覺會否就像在自己生長的地方裏,突然變成了一個陌生的旅客,去重新認識這個地方呢?就這樣開始有『咖喱骨』出現。」
而多年來,「咖喱骨博士」也隨着莫兆忠對城市、歷史乃至人的生命的理解而不停在改變。「他(咖喱骨博士)好像我自己的成長或對一些事的視點,跟着我不停去改變,所以他的變化是一種必然,因為他不是一個真的很固定的人物。」
想像是抵抗 最後的抵抗
2012年,香港劇評人鄧正健在《咖喱骨們的想像與抵抗》一文中寫道:「想像是抵抗,而且是最後的抵抗。當我第一次聽到『咖喱骨』這個名字時,我就一心以為,這將會是一個抵抗者的角色。但澳門始終不是我生活的地,對於這個表面金光燦爛,內𥚃卻已呈枯竭之態的(後)殖民城巿,『扺抗』究竟意味著什麼,我仍然無法明白……」
事隔數年,《咖喱骨遊記》再度上演,莫兆忠亦在這些年對「自由」、「想像」、「抵抗」有新一層思考。
「如從澳門人角度,這麼多年社會發生過的問題,有人曾經激烈地抗爭過、保留過;有人做過這些保留,然後開始覺得沒所謂了,很無力;又或者自己再扮演一個催毀者的角色也不一定。尤其是2014年之後,大家那所謂的公民意識的高峰過了後,有一種分崩離析的社會狀態,好似經歷了很多抗爭或抵抗之下,變成了有人覺得『係咪冇用呀』、『係咪個社會都係咁行』,然後有人可能繼續堅持,但每人堅持的角度已開始不同,似乎去了一個『冇乜大台』的狀態。」
「這幾年過程無形中會被社會發生的一些事,產生所謂有種無力感。但怎樣幫自己抵抗這種無力感就是要靠自己有冇想像力。我繼續想像我的生活可以怎下去。」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今年的版本中,《咖喱骨遊記》的Facebook帖文有這樣一句:自從時間獲得自由以後,《咖喱骨遊記》就成了矮人國的禁書。
文學也是想像,書被禁了,莫兆忠指,可以是權力關係,也可以是所謂「無權者」自己對想像的世界或真實的世界自我審查。「我想講的是,人怎樣去建立某種自己對生活的想像,和對我來說一個重構的過程。因為這幾年真的覺得太多價值觀或曾經相信過的事有破碎化的感覺。而這種破碎化我覺得頗有這時代的某種記認。」
「之前接觸雄仔叔叔講故事時,我自己在他身上看到一個頗重要的想法是,當我們有很多價值沒法去觸摸時,或當我們沒法去馬上看到變更時,其實我們作為人,無論是哪裏的人也好,想像力就是保留你自己對這世界的抵抗的最後一道防線,而且你要相信想像力。因為你對生活有想像力,你才會有改變的動力,如你永遠都說『係咁㗎喇』、『現實係咁㗎喇』,其實就是缺乏了一種對現實甚至未來的創造,或要改變甚麼的動力。我覺得想像是拉近理想和真實之間很重要的力量。」
虛擬與想像 何謂真實?

工作人員在街上作程式測試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今次的版本指《咖喱骨遊記》被製成智能電話程式,觀眾繼續在想像出來的虛擬與眼見的真實之間穿梭遊走。而在莫兆忠看來,在虛構與真實之間,還有論述的拉扯與辯證。
「現在我們所謂認知的世界或城市空間是相對虛構的。它拉遠了我們在真實的距離。」怎麼說?「所謂虛構是例如某種城市的論述,或我們生活的主流價值某程度上是被塑造出來的,而它和真實的世界可能拉遠了距離。它會告訴你:例如香港的獅子山下的精神,澳門是蓮花寶地、和諧社會,這些其實是種塑造,而它並非將城市的真實用一種所謂寫實主義的方法描繪出來,而它也是一種虛構。」
「我們必然是生活在一個『虛構』的世界中,而問題是我們怎去找到一種辯證的關係,我們怎在這虛構世界中,幫自己去接近真實,或即使我們沒法接近真實,但起碼我們能夠辨認甚麼是虛構,甚麼不是真的接近我們的真實。所以今次有很多這種想法放了入去這作品中。所以這故事一開始就告訴你,《咖喱骨遊記》在這地方已成為了禁書。怎樣把過去某些被認為是價值的,否定之後再重構,是我自己的一個,在這次創作的一個起點。」
陌生的城市 為重新想像

演員在街頭進行創作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今年的演出雖然觀眾要跟着智能電話程式走,所謂「一APP在手,人人壯遊」,但其實沒有地圖。「因為今次不會直接講澳門這城市。我會虛構一個城市。」
「對觀眾來說是一種不斷產生陌生感的過程。」莫兆忠笑言,自己一直都在說今次絕對是一個很離地的演出。「突然間覺得自己對一些事無知這感覺很重要。不要自己覺得『我已經好知呢個地方』、『這地方我好習以為常這地方』地去生活。你發現自己突然間迷失,你才會去尋找方向。當你常以為自己的方向就是這樣,你就不會去尋找,你只會樣樣事都習以為常,擦肩而過咁去做。」「也回到『咖喱骨』這人物的設定。他就是要將所謂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陌生化,重新去看。」
顯然《咖喱骨遊記》並不是童話,正如《格列佛遊記》在十八世紀出版時,有說因其濃濃的諷刺意味而曾被刪改。世界的故事在迴轉。香港劇評人鄧正健對2012年版的《咖喱骨遊記》曾寫道:「……不論在內容和風格上,整部《咖喱骨遊記》皆展示出一份如脫韁的想像力,它試圖為我們示範在主流論述以外的另一種想像城市方式……」來到2019年了,不論是在「矮人國」還是在澳門,面對各樣的社會事件與氣氛,我們往後又該何去何從,重啟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