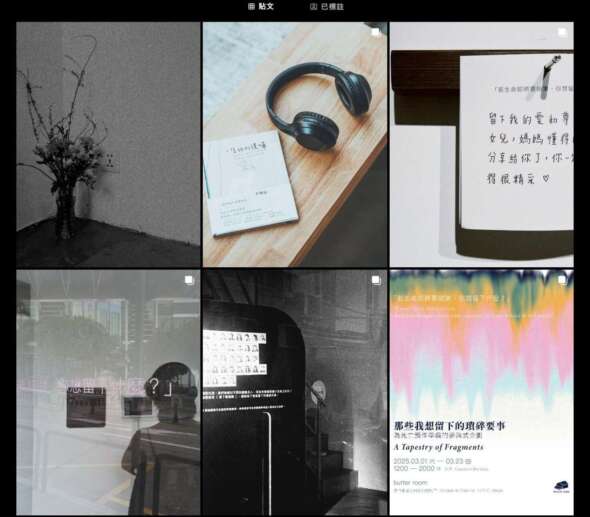圖片來源:紀錄劇場《離下班還早–車衣記》Facebook專頁
「如果沒有記錄下來,那些曾經以為隨意可見的日常風景,同樣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我們甚至可能連嘆口氣的機會也沒有……」
這是摘自今年藝術節風盒子藝術發展協會的作品《離下班還早——車衣記》在Facebook專頁的「導演的話」。曾經,澳門的製造業是澳門重要的經濟支柱。但到九十年代中後期,紡織品及成衣配額制度的取消,工廠開始北移,本地製衣業於是式微,加上之後賭權開放,今天的澳門,龍頭產業是博彩旅遊。「當年製衣業工人用雙手築起的榮景已經落幕,他們的故事亦被輕輕帶過……」
「即使不在,我仍記得」是《離下班還早——車衣記》一直在說的話。所「記得」的,除了女工的個人經歷,也是澳門這城的經歷,而用導演李銳俊的話語,也關係我城的 “DNA”。
「我們訪問了很多不同的人。有好幾個都是偷渡來,包括我媽和我姨都是。當時在內地生活不了,有幾個家庭的媽媽都是因為生活不了,所以要偷渡落來。」錄像創作李卓媚也分享道。
紀錄劇場 重現歷史

資料圖片
《車衣記》首次公演是2017年,當時是「舞蹈劇場」,今次藝術節的版本則是「紀錄劇場」。話說「紀錄劇場」的定義隨時代不斷被重新闡述,但總括而言是指建基於真實的訪談或自述內容的作品。學者Carol Martin 將之稱為「現實的重用」(recycling of reality),而這現實可以是社會、政治、歷史或個人。亦有研究認為,紀錄劇場可以補足不完整的歷史片段,提供不同版本的「真相」,亦有人指,紀錄劇場「不是屬於一個人,而是來自不同階層的聲音。」
《車衣記》的故事就集中於澳門製造業的女工身上。1963年,英國率先限制香港的紡織品及成衣進口,於是部份香港廠商轉移到澳門投資設廠,並將英美市場的訂單轉到澳門,澳門的紡織製衣業由此時開始進入歐美市場,澳門的製衣業亦由此迅速興起。1974年,全球41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多種織維協定 (Multi-Fibre Arrangement,簡稱MFA) ,實施紡織品配額制度。澳門因當時屬葡萄牙殖民地而成為MFA成員,其紡織品成衣出口於是同受配額制度保護,澳門製造業於是進一步起飛,工廠處處。
因為製衣不需高學歷,許多家庭都會安排女兒到工廠打工,幫補家計。同時,不少內地人為生活而偷渡來澳,靠着在工廠上班維持生計,從此在澳門落地生根,甚至成家立業。澳門也因着他們的勞動,製造業得以起飛。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澳門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當時除外資設立的大廠外,還有很多家庭式的中、小廠遍佈各區。
經濟轉型 「叻」的定義在改變

團隊訪問了好幾位昔日的車衣女工
「一路去到80年代或90年代,製衣一直是(澳門)經濟上的中流砥柱,撐起了經濟,而當中大部分勞動力又是女性,這件事也很不可思議。我們好像從來沒強調過這件事,但其實很神奇。你可想想,一個城市由女性——七成的勞動力是女性——去撐起,且持續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李銳俊說。
但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昔日的工廠不少已遷到內地發展,澳門經濟轉型,「叻」的定義由手藝超群變成有幾張「沙紙」(證書)。一班車衣女工為生活,只好轉行。錢或許是比以前賺得更多,只是好手藝也再無用武之地。
「這也是一個很無奈的地方。做莊荷的是其中一部分,還有很多是製衣業息微後,她們被迫要轉行,很多可能去了做保安、清潔等等。你會見到那工作性質是完全不一樣。她們很難得到一種所謂的工作上的成就感或滿足感,但以前製衣時相對是有的,她們仍然可說得上有一個專門的技能,她們也會見到自己勞動所得的製成品,又或者那種做得多就可賺得多,那種很直接的一種工作快感。」
「我姨以前看着電視(節目)《歡樂今宵》會話:『哇!嗰件衫是我車㗎。』她們真的很驕傲。但你在賭場沒理由說:『哇!你咁叻嘅,賺咁多錢。』沒可能的嘛。那成就感就會不一樣。」李卓媚也分享其中一些受訪者的說話:「『我成日都話畀阿妹聽,我淨係叻呢樣嘢,不過而家連呢樣嘢都冇埋喇……』」
「媽媽自己都有提到,覺得以前製衣就是手工業,可以專心去做,自由度也很大,做幾多就搵幾多,累就休息,想賺多啲就搏命做,但做莊荷雖然都像一個工廠形式般運轉,但它是服務業,是服務別人,她沒得say no,冇得好似控制自己怎樣去做。」
「而現在很可能有些工作是你坐下來也不可以,就算沒客都不可以坐。另一樣也是她(李卓媚)媽媽說的,那種工作上你自己的位置是甚麼。你自己的尊嚴是甚麼。」李銳俊說:「例如她做莊荷,我們戲裏面也會說,很大的不同是你做車衣時大家都是平起平坐,大家都相對平等,都相對是同一階層中,但去到那(莊荷)就是很不同的一回事。你會隨時被客人罵,即當你是出氣袋,粗口那些更是不在話下。」
「我也覺得很特別的一樣是,我們大家都會想像,工廠是一個很苦的地方,沒多少空間的地方,有受訪者很不喜歡,到現在還是覺得工廠是很可怕的地方,好髒、好嘈、好雜亂等等,印象非常差,但亦都有一直和我們說,『我覺得以前返工廠係最開心』,『我真係覺得以前很開心』,會不斷地有這些說話在當中。」
兼顧家庭的自由
- 2017年舞蹈劇場《離下班還早──車衣記》劇照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開心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由」,而所說的「自由」可能是因為可兼顧家庭。「以前的製衣,我是覺得我和我媽同在。」李卓媚說,「我和她一齊做緊這件事,我可以在她附近。但她自從轉了做莊荷時,整個家庭的構造就已經拉開了。我可能見她的時間十分少。」
「我們訪問的那些女性,十之八九都很以家庭為重,甚至她們覺得所謂的自由就是因為她們可以同時工作和照顧家庭。」李銳俊說,「如果萬一仔女發燒唔舒服,那一兩日不上班都沒問題,之後自己再勤力啲車返啲件數回來就可以了。類似這些她們都會覺得這份工我可以很自由,就是因為她們可以很照顧家庭,她們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時間,她們仍然有自己的重心,有自己的家庭。這個自由是來自於這方面。」
「雖然你也可以說,工廠也是一個非人的地方,很壓制,工作時間很長,但如跟現在的工作比,你就完全能看得出那差異在哪。雖然同樣工時長,但以前的行業,因為女性大部分都要照顧家人,他們是批准女性帶小朋友去工廠,甚至有些大的廠會闢出一個角或一層的一些空間做托兒服務。」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轉變。作為一個女性,(現在)她很可能第一件犧牲的就是家庭,因為她一定要輪班工作。首先很簡單,可能她已煮不了飯。她很可能已陪不了女兒,那已經少了很多親子時間。」而照顧小孩的工作現在就可能都要交予親人或外傭。「但她們又會覺得賺到比以前多的錢,這就是一個魔鬼的交易。」「但某程度上她們是被動的,即她們不是主動想做這交易,那是因為沒有選擇。」
向上流動 同樣困難

錄像創作李卓媚
李卓媚覺得,在當年的工廠,別人不會看女工讀了多少書,大家是同在一條起跑線,一起學車衣。「但因為她們就是讀書少,變成沒了製衣要轉行時,就會競爭力變低,但以前你有對手就可以拼搏。」
「她們一直會定義自己是社會某個階層。」李銳俊說:「我們當中也有些(受訪者)意識到這方面,然後她在工廠的過程中,她不斷讀書讀書讀書,令自己最終要擺脫這個階層,有這種很有自覺性的工人,亦有成功走出這階層的人。當然對很多當時未有這條件,未有這意識的女性而言,她們未必有這機會。我只是想說的是,這一代似乎有這意識、有這學識,亦有這些所謂的機會時,但是否真的得到這些?開心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社會是否進步了,在這點上真的很難去講社會是否進步了。因為社會首先有否提供到一個給大家可以實踐到一些事的平台。這本身已是一個問題。」
「那一代好想讀書,但沒機會,她們自覺自己沒法向上流動,所以永遠只能夠做看來辛辛苦苦的工,永遠都離下班還早。到這代,所謂讀到書了,又可以大部分都得到不錯的教育,亦好像很多機會,但事實上他們的生活或他們的各樣又是否又有真正向上流動?又有沒有他們可以發展的空間?這個社會又是否她們可以生存的社會等等,每一代都有他們的問題。」
「書越讀越多,但其實可以做的越來越少。這裏(澳門)可以選擇的職業很少,對口的就更少。我為何還要讀那麼多書?也會有這些憂慮。讀完書後還應否回來?如不回來,永遠都是異鄉人。對比他們媽媽那一代,她們也是為了生存,所以迫着做一些可能她們如有更好的條件,她們就不會做的工作,但當時沒這些條件。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生存。」
平凡的意義 城市的DNA

導演李銳俊
車衣女工的經歷反映了澳門過去的一段社會狀態,一個個故事更是我們的身邊活生生的歷史。多年來,有關製造業有多輝煌的研究或許不少,但有關車衣女工的紀錄則是寥寥可數。「我想可能是這件事還未是很老,其實還很當下。」李銳俊說,「我們在說的『歷史』可能是十九世紀的澳門那類,這件事還很新。」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覺得這群體的故事很平凡。「她們(女工們)所有的態度都是非常謙卑,因為我相信她們就是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小齒輪』,所以你去問她時,她常會說:『這些沒甚麼好說、這些沒甚麼好說。』她們就覺得大家都是這樣,沒甚麼特別。」李卓媚也坦言,小時候對於媽媽是車衣女工沒甚麼特別的感覺。「覺得……就是很普通,很平凡。入到工廠,都會見到很多個媽媽,即別人的媽媽,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媽媽特別不同。」
既然如此平凡,為何要大花筆墨去記錄?「製造業曾是覆蓋咁廣的行業,而竟然沒人去紀錄它,或沒再去從一些不同的角度去審視這行業當時對人的生活的影響,或當時為澳門帶來的一種整個城市的氣氛,或整個城市的DNA,我覺得很奇怪。」李銳俊說。
「事實上她們是平凡,但不等於因此而沒她們的紀錄,因此而不需要被紀錄。如果完全不知道,第三代會變成怎樣,這是很有趣的問題。因為現在這代很可能正過着完全相反的生活。我們見過很多上一代可能死慳死抵,或做好多嘢,好努力,很有她們自己生活的哲學,是因為她們在那環境長大。她們會永遠都會認同人要勤力要努力要付出。」
「(初衷)除了想做些事證明她們存在過外,亦是想說她們那種辛勞,她們那種努力,想向她們致敬。很簡單的出發點。純粹見到她們曾經為這社會或為家庭曾付出很多。這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再肯定她們。我有少少覺得她們是一個時代的……不知能否說是『失語者』,她們不會自己出來講,她們亦不覺得自己有甚麼了不起。」李銳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