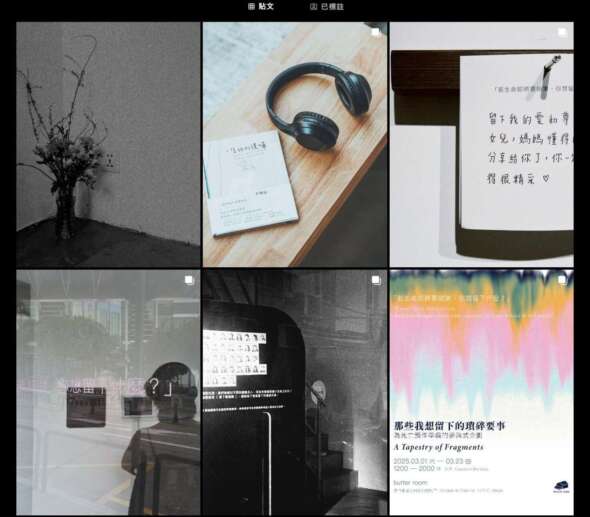攝影:何志峰
叩、叩、叩。門悄悄的從外面開了。
和平常的至尊無上威儀不同,一個老人穿著素色長袍,在燈芯亮光下密密縫補。
「我就知道是你,快過來。」
「陛下,和往年一樣嗎?」
「廢話!我縫補了很久,和當年女兒自凡間歸來穿的那件像不像?」
「像啊,針使得真好,縫得完好無缺。和初穿時的一模一樣。」
「你看看其他地方有沒有還要修補的?」
「嗯⋯⋯前前後後都好了。」
「你不要打擾她,每一年這個時候,她肯定還在織的,你偷偷拿進去她的衣櫥,放在原來的位置。」
「她還在織甚麼,她織了這麼多年,凡間那兩父子都夠穿了。」
「她就一年見一次,六個姐姐都嫁了,就剩下她一個,隨她吧。」
「真是的,怎麼就不嫁呢?!急死了。」
「你還好說。當年要不是你從頭上拔下那管花簪,這麼狠的一劃,她和那個牽牛的怎會糾纏至今!」
「當年我看到陛下你那麼生氣,必定有道理。所以我看不下去,她那麼忤逆不孝,自身的大事不讓陛下作主,把陛下氣成這樣,我真的受不了。」
「蠢!你真蠢!你也不想想,我是誰?!她犯的是天條,我怎能不管她。其他犯天條的我會治罪,自己的女兒犯天條,我更要認真治她的罪,不然我就沒法管了。但我發怒其實只是嚇唬嚇唬她,那牽牛的如果自己長進,女兒會想方設法讓他到我們這邊來,到時我就一併治罪不就好了?罰他們一起去撐天山,滅地火。沒幾年完了回來,我再封他去弼牛弼馬甚麼都好。事不就完了嗎?」
「可是……她當年和他連孩子都生了,陛下的顏面往哪擺?何況女兒是我生的,我的寶貝女兒不許一個替人牽牛的來糟蹋,我一簪沒有劃死他,算他走運。」
「唉,你真糊塗。你的簪沒有劃死她,可我們的女兒天天待在繡房裏,搖著那織布機。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難道這就不是糟蹋?她是我們最小的女兒啊,我的心肝寶貝。那時我心神恍惚,一想到她的事我便不好安睡。我說女兒的事還是少理,其實也輪不到我們去理了。她就是為了這一天而活著,傻傻的過其餘的三百六十四天。別再為她想甚麼,也不要再張羅甚麼,隨她吧。」
一想到小女兒一年都沒有邁出房門,每天都在搖織布機,當媽的心裡難過。想想她六個姐姐都嫁得很好,不是去當娘娘,就是去當夫人。享受榮華,備受敬仰。其實後來也替七妹張羅過婚事,好等她有一個歸宿。可是,不管哪一路的媒人、媽媽來到院子裏,怎麼叫也不肯從房門裏出來,總是唧唧唧的在裏邊響,連答應都沒一聲。來說媒的說兩句閒話就走了。早知道當日就不要那麼多嘴,那管劃破銀河的花簪早就不見了,可是銀河卻永遠都在。想到這裏,當媽的真是悔不當初。
「縫好了,拿去。她應該還在忙,悄悄的放回去,千萬不要讓她知道。」
「陛下,為甚麼不命人去縫。」
「糊塗!這種事可以讓人知道嗎?」
當媽的接過剛縫好的羽衣,小心摺疊包好,外人不會看到裏面是甚麼。逕自去到女兒的房間裏。
到明天,織布機就可以休息一天了。
但在休息之前,它運作得比其他日子更加頻繁。大人和小孩的四季衣裳,總是一套接一套的整件織出來。每當完成了一件衣服,就拿去年收回來的量一量,大人的還好,特別是小孩的,將舊衣服平展放在新衣服上,然後就會估摸著,到底身體長多大呢?手臂有沒有長長?肩膀寬了多少?兩邊夾下位置適合嗎?到這個時候,她永遠拿不定主意,畢竟一年不能相見,兒子長成怎麼樣她心裏沒個底,如果他穿了新的衣服,太緊的會不舒服,太寬鬆吧整個人看起來會不精神。如果孩子穿著不合適的衣服,會被其他孩子說她沒有娘親照顧,大家都有娘親照顧而自己沒有,小孩心裡頭會不是滋味,被其他孩子奚落一定很傷心。
有一年見他很不開心躲得遠遠的,他爹也支支吾吾的沒說甚麼,但看到孩子衣不稱身,心細的娘都猜得十之八九了。「兒子心裏不舒服嗎?」「村裏的孩子掀了喜鵲的巢,把雀雛弄下來,他知道了,跑去和小孩幹架。他還罵人︰『你這個壞蛋,你知道巢裏的小孩有爸媽嗎?』『那又如何?我知道你沒有媽!哈哈!』『甚麼沒有?我的衣服就是娘親給我造的,比你們的都好,你們看看!你們看看!連縫線都不會有,你們的衣服多爛啊!都要補破洞的。』『管你有沒有縫線,我要回家吃飯了,我媽現在應該煮好飯了吧。』可是他並沒有在意,兒子覺得穿到媽媽織的沒有縫線的衣服,即使不用洗,永遠都是平順整潔的,覺得十分驕傲,覺得其他小朋友沒有他幸福。」自此,織布機便沒有停過,因為,將兒子整件衣服織出來後,總覺得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她總是十分懊惱,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開始,重頭再織。
快到明天了,織女顧不著自己的睡眠,顧不著疲倦,織布機動得更快,她集中著手下的功夫,不知道的娘親已經悄悄的進入了她的房間,打開她的衣櫥,將那珍貴的羽衣掛回原來的地方。
「七妹,去睡吧,你不是等明天嗎?」
織女早已沒有憤恨,但她知道天命必須遵守。不管任何人,也只淡淡然回覆。
「待我織完這一條大人過冬的圍脖,還夠時間織一對小孩的襪子。母后你就不要管我了。」
其實這並不是管,早知道也管不著了。只是心疼她每天在沒日沒夜地工作。
「明天你不是要見他們父子嗎?太憔悴那就不好了,早點休息吧。」
織女頭也不回,織布機繼續唧唧唧的響個不停。當媽的才知道說了無用的話。這麼多年,女兒一直堅守住她唯一的,僅有的約定,就是每年的相會。
回想,七個女兒當中最小的一個,少女時候,七姐妹嬉嬉鬧鬧,總是有說不完的話,東海蓬萊,西方崑崙,觀花賞鳥,踏浪放鳶,好不開心。六個姐姐性格和善溫婉,都讓著愛撒嬌的七妹。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誰知七妹後來和牛郎互生情愫,這就大件事了。姐姐們都知道,她們七個的婚事將會得到父皇安排,會與其他仙家結合,在宮廟裏繼續受到世人的祟拜。這是她們已知的,可以預見的未來,女兒們只要好好地生活,接受一定會是幸福美滿的安排,那便會有所有人都羨慕不已的未來。
然而,七妹被姐姐們縱得太嬌了,與牛郎相戀後,義無反顧地誓要留在他身邊,六個姐姐輪流勸她,她也不理。最後更私下為他誕下兒子。還記得,當日父皇大怒,差一點把椅上的手靠抓裂,喝得在玉階下的二人喪膽。當娘的抵不過,馬上摘下頭上的花簪指著牛郎,命他從此不能再與七妹見面。他無可奈何的看著七妹,七妹兩眼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淚㾗,堂上所有人都以為只是戀人的分別,只有他看得出那是母親對丈夫和兒子不捨之淚。他馬上會意,如果當場死了,七妹和他所生的兒子便會成了孤兒。那一剎,只能是他們存在心裏的照應。那拿著花簪的手高舉,正準備要命之時,織女奮力向前衝去攔下了那使勁的手。霎時間,七妹的衣襟被撕出一道裂痕。人逃得脫,可以那手還是收不住,花簪漫天一劃,從此黑夜給劃出一道裂縫來,蒼穹的星星像流水一樣從高往低流注,從近至遠,順著那道劃痕流去,成為他們永恒的隔阻。
爾後,是波濤翻湧,是水清河晏,那全憑天帝主人的心情。
但不管怎樣,七妹是跨不過去的了。
天帝怒氣沖沖,指著玉階下的女兒︰「從今以後你們不能相見!」
她哭倒在玉階下,久久不能自已。堂上一片寂默,此時,七妹抬起頭,她兩眼的血絲滿佈眼眶,上一刻還是怒火攻心的父母,被她那堅決的眼神一瞪,頓時也目定口呆。
七妹許下誓言︰「非他,七妹終生不嫁!」
為父為母的,一時也回不過神來。呆坐在他們寶座之上,止住了堂上僅有的呼吸聲。
七妹二話不說,返回繡房內。就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只要有日出日落,便會有織布機的響聲。
每逢這一天的黃昏,放眼望去窗外的雲層總是透著華彩。雲層慢慢被風拉得稀薄,淡淡的跟隨著夕陽往西散去。空氣透著鮮草和樹木的清新,隨著月色初升,清涼的風慢慢滲泌餘暉煦暖。任個人在此時俯仰天地,都會自然而然的感到上天賜與和關懷,或又是惆悵夕陽已散盡了黃昏。然而,對他們來說則是約定的獎勵,規條責罰此時會在情理和在世人的期盼下暫時躲藏著。
微風朗月正是要為戀人們的約定而開道。
織女終於離開了她的織布機,將要給那父子的衣裳包好。窗外有一雙喜鵲飛進來,將那包衣裳栓在嘴上,飛在這位心煩意亂的女人後面。
她打開衣櫥,二話不說,拿起昨天被母后默默放回去,也是跟牛郎初相見時那一件羽衣。時間不多,趁還有一點點的晚霞,點上燭光,在鏡子裏好好看清楚自己。
每天梳妝,卻沒有好好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眼角有細紋了?是不是鼻翼的髮令紋長了?只盼著為父子的未來張羅,到了今夜的鏡前,卻深怕自己的容貌失落在他記憶之中。她很怕,真的很怕。想起聽過他每句說話,她還隱約記得那熟悉的聲音,然而,他的形相,卻越來越模糊了。當朝思暮想的人在腦海裏逐漸消逝,就是對她回憶和盼望的殘忍。往日花前月下海誓出盟,縱使在腦海中烙下完整的過程,隨著年月漸過,剩影殘像在心裏也只像結繩所記之事,只知道有發生過,繾綣溫柔會無情地被年月風化侵蝕。午夜夢中驚醒,發現記不住他所說的情話,手裏留不住他的溫度,她便會怕得發慌,因為現在的一切,建立在往日刻骨銘心的點滴,然而他的過去卻在心裏慢慢消逝,她怪責自己,不能容忍,不能容忍自己失去存在的方向。
回想起來,她並不介意牛郎出身貧賤,他的盡責和良善讓她有踏實的感覺,他吃稀粥她願意為他酙水,衣服髒了也會為他漿洗。她逐漸覺得自己出身在非凡的環境,並不是她自己所選擇,那只不過是命運的偶然,其實和他與生俱來的貧賤一樣,自己的華貴只不過是另一種身不由己罷了。當年看著出身卑微的牛郎,沒有任何家人、朋友、沒有任何背景,每天勤懇努力的工作,卻只能賺到僅夠糊口的微薄收入,不會埋怨且又甘之如飴。她學會工作帶給她實在的感覺,以她的能力,把衣裳給他們父子只是彈指之間,但她拒絕這樣做。她確信,人前穿著錦衣華貴的驕傲,倒不如坐在機杼前一梭一壓地織布,這樣的每天工作讓她心靈安慰。這是她當日看著他用牧草在牛背一下一下洗刷時所看到的勤懇,使她無視身份藩籬而由衷地傾心仰慕,也敎會了她每天對著織布機,看著一寸一寸的衣服織出來,想像將會穿在父子的身上而感到安慰滿足,那便是她的回報。每天的勞作讓她覺得生命沒有白過,她不需要別人同情,也不需別人讚賞,眼疲手傷成為存在的印記,唧唧的聲音成為她靈性的凱歌。
在妝台前,她毫不猶疑地穿回當天的羽衣,理回當日的髮式,戴回當日的耳環,塗著當日的脂粉和口紅,想著希望能給他立刻憶起當日初見的悸動,看著看著,心底裏的回憶漸次浮現。嘴角微揚,那是雨中他為自己戴上斗笠的時候,眼簾低垂,那是清晨靠著他肩膀的一刻。往鏡子裏再看清楚,幸而歲月並沒有在她臉上留下任何㾗跡,但她的心態卻隨著年歲而慢慢複雜起來,並不是她改變了初衷,而是年月的沉積使她的感覺變得更為複雜,難以言喻。今夜成為了三百六十四天離別的考驗,堅持對誰都不簡單。然而,盼望潛藏著未知,也引伸出恐懼。像每年一樣,她盼著這一天,卻也正正在這一天到來之時,害怕起來。
平常日子,他們並不能隨時互通有無,所有見面和通話對他們倆人來說皆是天方夜譚,沒有人敢押下自己的性命去為她們傳遞訊息,是徹底的音訊隔絕。他生活的點滴,只能在回憶中涓滴尋找,刮風下雨來得及躲藏嗎?老實的他會被人家欺負嗎?她平日每天都想著,到七夕的一夜,有甚麼話要對他說。千言萬語,家長裏短,有時甚至將要說的話寫下來,反覆揣摩,應該哪些先說,哪些後說,趁沒人的時候,有時還獨自偷偷練習,應該怎麼說才好?然而,此刻的恐懼和緊張,使她有如初見戀人一樣,亂了方寸。天色越黑,她便越亂,將之前練習如何說話的記憶通通忘掉。繡房裏比平時寂靜,但心跳的燥動與不安比平日的織布機唧唧聲更響,她作了不少次深呼吸,希望可以把內心的湧動壓下去,可惜內心的糾結一次比一次強烈。
已經是入夜好一陣了,窗外的鎧鎧白光映照進來。時間到了,織女看到窗外,一條星河,平平寂寂地默默流淌著。她來到星河的岸邊,那是當年母后用花簪劃過的裂口,看著這個裂口,這個將他們一家分隔兩地的裂口,當年的憤恨鬱結,早已結疤並長出肉牙。她已無暇細顧,顫抖的手心撫壓著起伏不停的胸腹,等待著喜鵲們的來臨。
這些喜鵲如期來到,當年的處罰明令天上地下仙凡不得給予他們任何幫助,但這些鳥兒卻置若罔聞。第一個七夕,喜鵲們分別在牛郎與織女的頭上出現,擾擾攘攘,兩人都不知是何用意,有啄衣領的,有爪衣袖的,有朝著一個方向唱歌的,給他們示意著前進的方向。他們對喜鵲並不陌生,初相識時的日子總是被牠們的歌聲包圍。沒想到,是被引到仙凡裂口,銀河岸邊,數以萬計的喜鵲們會聚集一起,排成一道橋,為著天各一方的戀人接通對岸。
今晚也一樣。
喜鵲分別找到兩人,歡欣歌唱。他們再一次被喜鵲們引導,來到銀河的兩岸。
牛郎看著對岸的那人,她的妝容,她的衣裳,都與初認識時一模一樣。他很想往橋上跑,可是卻舉步為艱,他的猶疑來自久別重逢的陌生,看著對岸的人,和以前一樣的光鮮亮麗,想到過往的相處,織女總是溫柔婉淑。好不容易才往鳥兒身上踏,內心沒有恢復平靜。他一直默默看著對岸的那個人,那個認識很久,曾經互相依偎,曾經互訴衷情,可現在卻是感到陌生的人。呆呆的看著,之前日日夜夜準備好的千言萬語,此刻,不知從何開口。
織女穿回這一身衣服,並不是因為穿起會更漂亮。而是這一套衣服是與他初相識時穿的,是那短短日子朝夕與共時穿的,是最後被令官譴回天上與牛郎分別時穿的。到這一天,這身她一直珍而重之存放在衣櫥深處的羽衣,便是二人記憶的憑證。
他們都知道,縱使他們默默看著對方,白白的各自心煩意亂也不是個辦法。星河一直流淌,不停的為他們相會的時間倒數著。害羞的小孩騎著牛在鵲橋邊下,顯得生澀,心裡卻著急起來。他們知道,兩人在對岸待久一點,相聚的時間就會少一點,所以再怎麼難,也必須往橋裏走去。他們一步一步的靠近,雪白的星光從橋底熠熠閃閃映照在兩人的身體,體態輪廓慢慢清晰,星河光輝映照著兩人的臉,他們越靠近,眼裏戀人的面容便越清楚。在記憶裏初識的緬靦,第一次依偎的羞澀,談笑的開朗,難捨的離別,漸次在腦海中浮現。縱使曾經月下相依,夕照相擁,沒有比現在星光之上靠近來得更動人。萬千喜鵲奮力扇動翅膀,星光之中空氣流動,更是難以言喻,不可能是秋夜晚涼,不可能是仲夏和風,氣流使他們更輕柔,讓他們飄逸出世。
穹蒼星宿,腳下銀河,天地間的牛郎織女,在記憶裏向新的未來走去。
再一次,牽著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