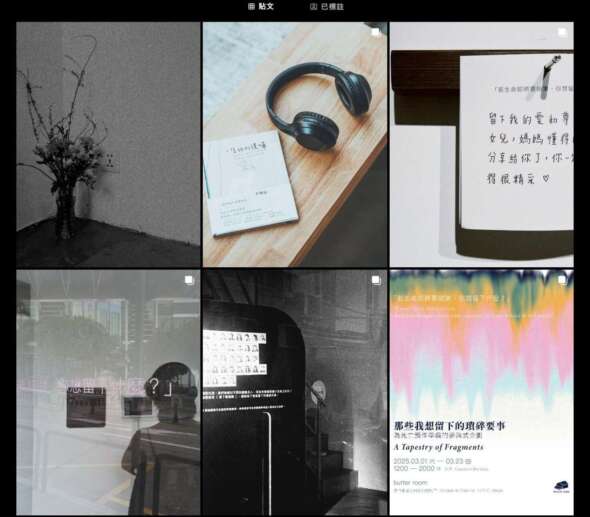翩翩將會在藝術節有一個演出,她演的是話劇,但卻被安排跳一支舞。
翩翩將會在藝術節有一個演出,她演的是話劇,但卻被安排跳一支舞。
自小時候被媽媽迫著去跳過一輪中國舞,上了中學就喊著停了。在排練場上認識了一個新的男生,說是希望找她去學跳舞。「我們去一齊去報TANGO好不好?」又說是政府補助不用錢。
她笑笑就走開,那個男友人也沒有再問。
對翩翩來說,身體的記憶已經很遠,現在不知道是否能勝任。但在她認為,沒有好或壞,每次演戲都會有新挑戰,試過踩高蹺,試過彈琵琶,又試過玩雜耍拋五個球,只要導演要求劇情需要,她就盡力在最短時間內學會,並沒有太在意。
昨晚戲排得太夜,吃完宵夜凌晨二時才回來。生理時鐘往後挪,中午12點才醒來。
快要出門口時,被穿著功夫褲的媽媽在廚房裡叫住。
「媽,排練不能吃東西。」
媽媽從廚房拿著大碗麵到客廳來,經過正想出門口的她時,報以一個嚴厲的眼神。
「過來,坐下。」媽媽將兩個大碗擺得好好的,筷子放碗邊,放得好好的。
還是頂不住媽媽的催迫,屁股還未坐上去,媽媽就開始講話了。
「有人把錢賺了、把午餐煮好了,端到你面前,還嫌三嫌四。你也不是中學生了,出來工作這麼久,知道錢是難賺了,啊,對了,我也沒有嚷著叫你拿甚麼錢回來,叫你吃個麵還好像求你一樣。」
「媽,這碗麵實在太大碗了,都夠我吃到霄夜了。而且現在吃到那麼撐,今次排的戲我要跳舞,等一下一動起來會吐的。」
「我日日都在公園跳舞,你跳的是甚麼舞?可以跳到你連飯都不吃。」翩翩心想:你的哪算是跳舞,不過是在公園舉舉手,走幾步,額上出兩滴汗,頂多算是運動吧。
媽媽十六、七歲時,本來在繡花廠裡繡花,第一起破四舊整個廠被鬥沒了,便被下放到生產隊,她的職稱是「農藝師」。所謂「農藝師」也沒有甚麼「藝」可言,就是拿著鋤頭在生產隊的田裏走來走去,哪裏有雜草就把它鋤走,田梗塌了便挖個土補上去。以前只是拿繡花針的手,現在叫她拿鋤頭,她起初對這個工作甚為抗拒,但原來她年紀最小已經被分配到最輕的工作,其他人幹的都是重體力活,不是在插秧割草就是去挑糞,她也沒有甚麼好說的。有一晚北邊的文工團來石歧表演《紅色娘子軍》,生產隊隊長把隊裏唯一一個名額讓給她,那晚她看得如痴如醉。
「好靚啊,怎麼每一個姑娘都咁靚,每一個的姿勢都好靚噶。」文工團女團員的氣質吸引著她,整場舞蹈她連呼吸都忘記了,忘了音樂,想不到演出的內容,在燈光的映照下,只顧看到女團員的汗,腿踢上來揚起的塵,甚至連眼神和晃動的辮子髮稍,每一寸動能游來移去,每一刻對她來說都是震撼的,這並不是看電影,看大戲可以比
這種震撼抑制不住她的身體,散場回家的路上邊走邊學著跳。
(好靚啊,如果是我多好啊。)
半年之後她跟著隊長到涌邊偷渡,準備到澳門後到香港,可是到了澳門後偷渡幾次去香港都失敗。在澳門她去了製衣廠當女工,隊長成了老公,去了工地作泥水工人。
直至五十幾歲,沒有製衣車間給她坐了,賭場桌前也站不來,才發現頭抬起來很困難。X光顯示頸椎都是骨刺。醫生說游水可以改善症狀,沒游多久,泳友當中有一個在文工團練過的,約她去公園跳舞。
生理時鐘自然作息,時間都是很慣性的,早上五時多天亮就醒來,六點左右大姨們就會出現在公園,或者有的七、八點帶了孫子上學就會到公園,十點左右太陽已經很曬,也該去買菜了,不然街市裏好的菜都被揀走,買好了就跑回家煮午餐和看電視劇。
「趕快吃了,吃了才可以去排練,碗放著不用你洗。你去忙你的吧。」
照舊去看她的電視,在Youtube看〈楊麗萍廣場舞〉頻道,一、二、三、四⋯⋯
門鐘響起。
門打開,看到一名金髮碧眼的女子站在門口,眼睛通紅,有點情緒激動。
媽媽認得她,在她早上去公園時,這個鬼妹便收工返家。心想一定是在夜總會做雞,污糟躐蹋。
「媽,這個女人說我們嘈到她。」
「又不是深夜,沒有噪音管制,不用理她。」
Tanya 在烏克蘭是體操運動員,十四、五歲(虛報,其實是十二、三歲)就代表國家參加比賽。有一次右腳腳踝受了傷,只好退役。剛好馬戲團徵人,她便跑去當空中飛人。空中飛人的技巧對國家級的體操運動員來說,很快就適應了。每次表演都是不同的觀眾,卻沒有被要求動作難度無止境的增加。遇見的人,去的地方,都比以前在訓練場多得多,散場後,男男女女有說有笑。好開心。
晚上的Party聲音太大,別說叫她記住,她根本聽不到媽媽在電話裡說,有人介紹了一個軍官來相親。這一番話在Disco 音樂中被醉了的手指按掉了。
直到有一天,38歲的空中飛人阿諾德在表演中失手掉下來。
在柱子的頂上,Tanya看到躺在地下的阿諾德右腿和右臂不停抖動抽搐,然後耳朵和嘴巴的血汩汩流出。這個畫面Tanya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第二天,她靠著那根空中飛人的柱子,腳怎麼抬就是踩不上那梯子,像樁柱一樣釘在地板,她再與那些高空裝置無緣。
她成了化大濃妝穿著短裙在馬戲開場、中場、散場之間串場的跳舞女郎。
伸伸手臂,搖搖屁股,扭扭腰,踢踢腿。沒多久,她便習慣賺這種青春錢,或說這個職位習慣更青春的人。漸漸的,在下班後,她開始會一個人去吃飯,玻璃水杯剩半杯伏特加,香煙一直飄到燈罩裏去。
今次聽到媽媽打來的電話,妹妹有機會被保送去舞蹈學院,妹妹查到,院長是她體操隊的前敎練,在體操隊退休後,便被安置到舞蹈學校去。媽媽希望她能去打個電話給妹妹,而且需要學費,希望她負擔一下。
在煙罩裏的煙彌漫混作一團,燈光下清晰可見, 當另一口呼出的煙,升上煙罩裏,裏面的煙便慢慢散出來。
Tanya焦躁、厭煩地站在鐵門外。楊麗萍還在電視裏跳著廣場舞。這兩母女並沒有理會她。
翩翩在餐桌上的電話響了一下,是一則訊息。
//到貨通知︰親愛的翩翩,您在淘寶購物已經到澳。單號3548153…//
(我從來沒有用過淘寶購物,怎麼會收到這種通知?)
翩翩並沒有理會站在門口Tanya的焦急和等待。她慢慢地去拿她桌上的背包和她的舞蹈鞋,準備出門。
「媽,我跟她說了,她還不願走。我走了。」
翩翩拿了自己的東西,從Tanya和門邊之間鑽出去,沒有關門,也沒有叫她走。
Tanya早就注意到地上有一雙舞蹈鞋,看著翩翩將舞蹈鞋拿起放入袋中,看著她的腿和腳,看著她在自己和門縫轉出去的身影,看著樓梯間的陽光洒在她身上的背影,一步一步的下樓梯。沒有幹勁,但不能說不乾脆,窸窣的身影還是使Tanya 看得出了神,剛剛不安定的情緒隨之平伏下來。
路上一直想著為甚麼會有通知叫她去取網購。應該是詐騙短訊,但詐騙短訊又怎會有人知道她叫翩翩?
在排練場上,導演叫︰「大家跳好一點,我們有機會巡演。」「耶!」「去哪裏啊。」「我計劃是去馬來西亞、星加坡、台灣等,有些劇團已經想邀請我們合作,但都得看我們能不能向文化局申請到資助。」
聽到消息,幾乎所有人都很雀躍。翩翩在出神,她的電話響起使她嚇了一跳。所有人都盯著她。
她躡手躡腳去接電話,是她的男朋友。
「喂,你幫我拿淘寶了沒?」「你怎麼留我的聯絡資料?」「你會經過嘛。」
很久都沒有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埋怨她沒有匯錢回家。Tanya手機訊號響起,是妹妹入學的照片,應該只有媽媽、妹妹,但旁邊多了一個穿軍裝的男人,比跳舞的妹妹高出一個頭,媽媽說他叫Viktor,半年前給你講過,他爸爸是你的敎練,這次入學他幫忙把妹妹的東西載來,還給妹妹四處張羅,買日用品甚麼的,你妹妹笨得要死,居然還能上大學,還好有Viktor,不然妹妹一個人去學校報到我實在不放心。媽媽說他快要升做中尉,快點回來跟他見個面吧。Tanya對Vicktor印象似有還無,但笑容倒是不錯。
「媽,你有跟我講過關於Viktor嗎?」「有啊,有一次打電話給你,太吵了,你掛了我線。我叫你來相親,就是他啊!」
「——排練時可以講電話的嗎?還有沒有人未關電話?——」
「導演罵人了,拜拜。」「等等。」「幹嘛?」「我昨天第一天上班了,馬上去找房子,下個月我們可以一起住了。」
我們可以一起住,是在一起住,這已經是求婚的代名詞。那年,男友高三,她高二。男友帶她去看戲,看完電影看話劇。總是膩在一起。之後還一起去參加表演工作坊,每一次都會有人說,翩翩,你的身體很好啊,喔,哈哈,謝謝,我沒有怎麼練過。長得漂亮,又高又窈窕,肢體又好,沒多久翩翩就成為劇界的邀演對象。男友初時(甚至現在)覺得蠻不錯的,她每一次參演都會去看,但她排練時間不穩定,休息時也不會見著面,他上課然後回家然後又上課,見面的時間常常對不上。之後,男友表演工作坊後選角常常選不上,心生怠惰就乾脆不去了,每天打網路遊戲打到三四點,一直睡到中午所以理所當然缺了早上的課,心情放在網上,網遊聊天網遊,沒錢他媽會給,或者有人叫就做一下臨時工。翩翩就去演她的戲,他倆人相聚的時間被不停錯開。
「畢業了,我不知道要幹甚麼。」穿著畢業袍的男友說,翩翩給他拿著花。「嗯。」翩翩也沒有想太多,演戲有薪水,夠她一個人用,明年才畢業的她還沒有想過找工作。
「要不要讀碩士班?」「你現在才想?碩士班不是畢業這一年去考的嗎?你今天畢業禮,要讀也是明年去讀啊。」
男友讀的是工商管理。畢業後在同學開的補習社給中學生補習之類,最近他打算開個網店,所以得每天都在家裏。
「生意怎麼樣?」「我在學淘寶。」
時間總是零零碎碎的,網上交易完(也不知道交甚麼易),得要等一等,便順便開個視窗打遊戲等著。他媽問「最近不見你去看戲?」「在家看片就好。翩翩演就去看一下吧。」就這樣過了幾年,他媽最近終於忍不住,托朋友在賭場裏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給他。那是一個管理倉庫的工作,很簡單,誰來拿甚麼東西便在電腦登記,少了哪樣就填個表拿去另一個辦公室,讓採購部購買。
「欸,你知道嗎?我的工作可以躲起來,我今天就在IPAD看了一整齣XX電影。欸,還有一件事,昨天半夜收工,有一個俄羅斯妹在飯堂哭,另一個俄羅斯男人過去安撫她還被她摑了一巴掌…」
「好了,大家都盯著我。我排戲其實是在工作,你知道嗎?我•不•是•在•玩。」
「記得幫我拿淘寶貨。」
「我可能要排到九點或十點,那個代購的店未關我便給你去取。」
翩翩沒應「要不要一起住」,就把電話掛掉了。
Tanya的室友,是和她一起在路氹城工作的女舞蹈員。昨天起不幹了,有一個美國人和她同居,說是要養起她,其實這個星期她躲著不太去跳就知道她懷孕了。今天房子空蕩蕩的,半個人也沒有,覺得份外孤獨,一個人起來吃了個昨晚的麪包,就去坐公車了。她今天的班是晚上十點至凌晨,一個人坐巴士經過友誼大橋,看到海上一輪大明月,一片雲都沒有,海面的微波像一片毛毛的地毯一樣墊著洒在上面的月光。啊,她突然想到這是一片海,對了,家郷的月光照著的不是海,是小時候的雪夜,更為動人。有一晚,她和妹妹不理媽媽在罵,一起在屋外玩耍,積雪平平的舖滿一地,映著月亮的光,亮堂堂的,可以清楚看到彼此的笑臉,看到妹妹蹌蹌踉踉的,腳插在雪地上,再拔起來才能走第二步,動作不是很乾脆,追她的時候月亮像白晝一樣洒在她的背影上,越走越遠。
對,就是今晚這種月光,但不是海,Tanya突然發現,這個海並不屬於她,她與這個海毫無關係。上班、下班、睡覺、休息,或者每節舞蹈之間的休息去抽個煙,或午餐晚餐吃飯,都是一個人。偶爾和同事搭個話︰好累啊,好吃啊,拜拜之類。她一直沒有想太多,可能自從離家到體操訓練營起,生活的前途迫得是一項接著一項,沒有太多選項,她一直要供養家裡,也不由得她有除了工作之外的另外選擇。她突然蠻羨慕那個離去的室友,不管是不是會成為某人的太太,至少成為母親,是人生的另一個選項,一個她可能未想過但好像比現在更安穩的選項。
即使是背對著下樓梯,翩翩也知道Tanya凝望著她。翩翩往回走上樓梯幾步,靠近Tanya,往門裏向媽媽說。
「媽,不要說人家污糟躥蹋,這個俄羅斯妹是在賭場購物廣場跳舞的。」Tanya不是俄羅斯人,但反正是白人在賭場跳舞的,通常都會被認為是俄羅斯人。
「即係廣場舞啦。」媽媽更認為做這種肉體工作的白人都是不正經的。
原來翩翩早就看過Tanya,她常常在賭場的購物廣場閒逛,每當有人表演,不管是石膏像、小丑她總是多留一眼。在名品店前,Tanya總是穿著可以搖曳下擺的裙,男舞者衣服總是腰細腳長,隨著三拍子悠轉,翩翩永遠是站著留到最後的一個。「好優美的舞蹈,這究竟是探戈還是華爾玆?」
莫說是翩翩,就是寫這篇小說的本人也不會知道,即使我知道翩翩看的是何種華爾茲,看這篇小說的你們也會有半數以上不會知道翩翩在看甚麼。當注目而視,然後觀看,很多問題會在剎那間動念想問,但轉過頭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很可能是連看過甚麼表演,也會迷迷糊糊,馬上忘記。唯一能記住的,就只有舞者的神緒。
「啊!」翩翩總是想到這些,她開始尋找這些觀看的意義。意義不清時,總是想走,可是她的眼睛卻又留住她的身體,Tanya跳得太好看了。
翩翩對演戲開始厭倦,這種厭倦並不是討厭,主要是因為倦。她的戲總是一個接著一個的來,有些演員會羨慕她,曝光率高,在同行和觀眾之中已經得到認同,這種認同使她覺得虛虛的,不知何來的空洞,在群體中永遠得對著別人微笑,這種微笑很多時想收起來。在賭場購物中心閒逛,其實是一個逃避怎麼走都會碰到熟人的社會的方法,這個地方的人總是川流不息,異樣的時空和異樣的人使她覺得在旅遊。在這裏她很快認出鄰居Tanya,這幾年總是看到她在跳,舞姿優美,永遠掛著笑容。
翩翩心想,她這樣笑,這樣跳,不累嗎?這個笑容都保持了好多年,她是怎麼保持呢?
Tanya的笑容觸發了翩翩的空虛,這種空虛延展到她每一場戲開演之前,她知道等一下漂漂亮亮的走上台,然後會有掌聲,或者支持者的歡呼,或者掌聲寥寥數天後會有一些耳語和謾罵,然後又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開演之前她就知道作這個演出後這個世界任何人都不會有任何改變,可能有好評或者劣評,但是還是不會改變。「我在做甚麼?」、「我在幹嘛?」完了場她會問自己。看著時鐘跳轉,也分不清秒針向前跳還是向後跳,這一小時前的呼吸和一小時後的呼吸是不是究竟老了很多?這些思緒歸入寂靜之前,總是在轟炸她。
這種累意,翩翩在家門找到了答案。剛才Tanya 的出現,眼睛滿佈血絲,頭髮蓬鬆,面容憔悴。
在梯間的翩翩突然回頭,看著Tanya。
Tanya 終於被理解,內心激動,淚如泉湧。
就在看完〈紅色娘子軍〉的第二天,她一個人拿著鋤頭在田梗上走,腦海裏還是昨夜的舞姿,跳著走路使泥土上的足跡深淺有緻,與平時不一樣。
這時,生產隊隊長把她拉到一邊說︰「你散場為甚麼走到前台了?你拿的是公社內部招待票,你知道嗎?」「你怎麼知道?」「那是領導和幹部的票。你被人認出來了,公社裏幹部都議論紛紛,大家都在想你怎麼會有票?」「所以呢?」「我們被查出來就不成了。」「那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如果被發現,我打算走。」
到了很久很久之後,公園有幾個大姐都在年青下放時看過類似〈紅色娘子軍〉的演出。媽媽才細想︰原來到處都有人看過,怎麼我當年靠近去看,就好像成了犯罪似的?我被人認出來又怎樣?如果被認出來搞不好會因為我條件好,將我編入舞蹈團也說不定,這不是好事嗎?到底是不是他想騙我一起偷渡,騙我一起來澳門?看完舞蹈我也沒有亂說誰又知道我看過跳舞?偷渡之前生產隊裏其他人對我也沒有甚麼異樣。我也沒有付錢給偷渡的蛇頭,他怎會熱心替我付偷渡的錢?就這樣思來想去,越來越像是當年只有十七歲的她,被生產隊隊長哄騙來一起偷渡的。
但想也沒有用,也不知道找誰追究了。當翩翩還在上學時,一次工地意外,一個大水泥磚從高處往下砸,就砸中正在休息的他,當場死了。她和翩翩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生活巨變,唯一能做的就是夜裏背著翩翩哭。早上在車衣,晚上俯著哭,頭就這樣一整天都彎著,之後也抬不起來,才知道滿頸椎都是骨刺。
翩翩六歲那一年,媽媽第一次看到小學畢業舞蹈表演,原來學校有舞蹈班,跳中國舞,課外活動得另收費。媽媽希望翩翩去學。她學了兩節課,老師問媽媽,這孩子是不是真的有興趣?老師說︰讓她挺腰她只隨便的挺一挺,讓她抬腿拉筋她腿也只懶懶地伸了一伸,不想來就不要來了。媽媽問翩翩,怎麼了?翩翩說,老師叫的我都有做,不明白老師氣甚麼?老師好兇,好煩。媽媽問,你不覺得家儀和家麗兩姊妹跳得好漂亮嗎?是啊,她們跳得還不錯。你不想和她們一樣嗎?她說,喔,沒有想過。媽媽小時候在鄉下看過北方來的姑娘跳的〈紅色娘子軍〉,多好看啊,完場後大家都企立鼓掌,那時我才比你大沒幾歲,在人群之中剛好可以鑽進去前台。每一個人都又高又漂亮啊。然後舞團宣佈因為好不容易才來一趟,會去惠州和肇慶,還會去珠海和深圳。那時我只會耕田,連廣州都未去過,看到她們可以到處去我羨慕得不得了,我心裡想,如果是我多好啊⋯⋯
翩翩覺得媽媽很煩,不想理她,直至回到家。爸爸總是會問翩翩︰今天學了甚麼舞步?這時翩翩才精神,腰挺得前所未有的直,拼了命將腿伸得前所未有的遠。老師只跳過一次說是下節課才敎的舞步,翩翩已經馬上跳給爸爸看。直至快要撞到狹小的客廳的枱椅之前,爸爸就會伸出手臂一下抱住她。
「爸爸,好看嗎?」「全世界跳的最好就是翩翩。」「是嗎?我以後只跳給你看。」
跳舞和游泳不同,游泳只有往前游,呼和吸在水底和水面之間,沒法讓人注視你。去公園跳舞就不同了,一班大媽手腳比來劃去,當然不能和記憶之中那班紅色娘子軍相提並論,路人不習慣了不會在意細看,但彼此之間的對照觀看,在一個空間裏共同舞動,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當中的興奮。每天一睡醒就去跳舞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媽媽享受著每天汗水不停濕透衣服的美好。到這個年紀還有這個機會,只有她心裡知道是多麼難得。並沒有想和當年的紅色娘子軍比過高低,但遲來的舞蹈,對她來說每一分鐘都不想浪費。如果說舞蹈是讓她能分散注意力,不如說舞蹈讓她的生命變得充實了。翩翩長大了不用她操心(也操心不來),她總是公園裡最早到、最晚走的一個。她學會上網看廣場舞敎學,一、二、三、四,每天在電視裏響著。
「媽,今晚我回來吃飯。」「你不是說今晚有排練嗎?」「不排了。」「今晚沒有飯吃,工會組織我們去中山參加廣場舞大會,我和群姐和金鳳去珠海地下商場度身造衫。你自己在外面吃吧。」
在更衣室裏,差不多穿好今晚的演出服,媽媽的短訊傳過來︰妹妹入學了,她很好。另外,Viktor所屬的山地正在烏東地區和俄羅斯作戰。俄軍用山地砲狂轟Viktor在山裡的駐地,他失踪了,看來凶多吉少。
“Tanya, Where is your face?” 經理氣到馬上用粤語補一句︰「你的眼耳口鼻呢?」臨出場前經理說一說,她才發現還沒化妝。「那你怎麼出場?剩下一個男的怎麼跳?」
Tanya這種心不在焉也不止今天,她的俄羅斯男舞伴也忍了很久:「你不想工作,就不要害我。」他說的話好像一枚飛彈精準地打中她心裏去。
她沒有不喜歡她的工作,她沒有想過去害別人,甚至她沒有想過要和人合作。她今天跳不了,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讓眼淚靜靜地流下來,她到往常可以稍稍逗留的員工餐廳。乾乾的臉被紅疼疼的淚水輾過,好像龜裂了的泥土突然澆了水一樣,她覺得她的臉好灼熱。
俄羅斯男舞伴找到她,氣衝衝的說︰「你不要那麼任性?你不想工作我還要工作。」Tanya忍不住一掌打到他臉上。
翩翩沒有甚麼心情排練,其他人則處於巡演在即,可以到處去的興奮之中。為了打破在歡呼之中的無感,翩翩給男友回電,大聲地宣告她的無力感。
「如果是你媽的主意,肯定是要你結婚,而不是你說的一起住。你媽早就向我提下半年甚麼時候是好日子適宜結婚的。可是⋯⋯你?我現在告訴你,下半年我要去巡演,我去定了。你之後也不要再來找我!」
還站在門口的Tanya 好像被電視傳來廣場舞機械的節拍困住了一樣,一臉無奈。翩翩往回走向她,握著她的手腕輕輕將她帶開。走進家裏將她的Ipad和耳機給媽媽,關了電視,平和地看Tanya一眼,翩翩稍微點一點頭,關了鐵閘便下樓去排練場了。
媽媽洗碗出來,看見鐵門外Tanya獨自回家的背影,然後將木門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