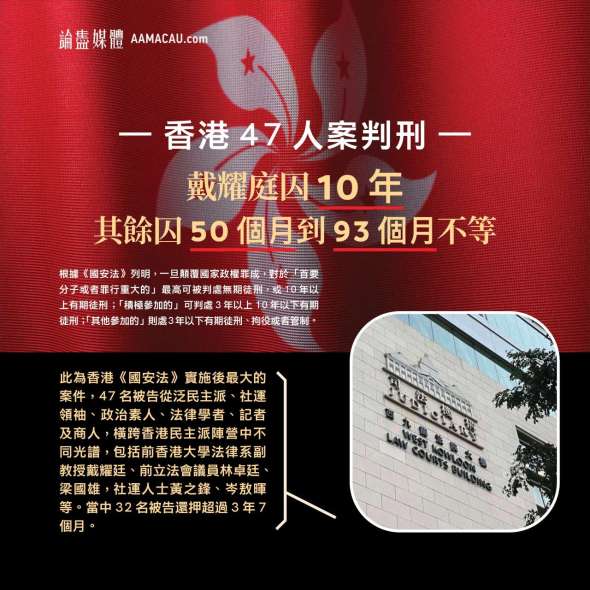早前在第四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看了以色列電影《男人的階梯》(Afterthought),故事發生在以色列的海港城市海法(Haifa),城裡發生的人和事,似乎跟澳門有點相似。
《男人的階梯》呈現的海法,一邊是面對大海的繁忙海港,而城市的另一邊,則是依著迦密山(Mount Carmel)而建的城區,在最下層山腳的舊城區,房屋大多較老舊,居住的多數是收入較低的基層人士,到山的中段,則有很多社會主義式建築的房屋,屬於中產區,而一路再上到山頂,則是較浮誇、很資本主義式、較富有的區域,這三個不同階層的社區,由數十條公共階梯串連起來。
影片由一個360度自轉pan shot長鏡頭開始,畫面首先呈現的,是海法日間的繁忙海港碼頭的大遠景,畫面一直向右pan,開始出現綠油油的迦密山,接著再繼續pan,漸見山腰上零星的小房屋,畫外音慢慢滲出電台廣播及人們電話交談的聲音,你一言我一語的開始出現越來越多房屋,山腳和山腰上的樓房越見密集,有的是小平房,有的是帶點格格不入的高樓大廈,此時畫外音的電話交談聲開始出現不停的咳嗽,是的,山體被大肆挖掘,花草樹木被剷掉,換來是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大自然山林頓變石屎森林,空氣也自然變污濁,看看我們的澳門,就是很好的例子。
影片的第一個鏡頭用了360度自轉pan shot呈現了整個城市的「狀態」後,開始聚焦在山腳下一間簡陋小平房,屋內住有一對中年夫婦,老婆是有點名氣的歌手,老公Moshe則收入低微,只靠寄放在山腰小商店的一件「投幣式機動騎馬仔」為生。老婆因在回家途中遺失結婚耳環,Moshe於是出門替老婆沿路尋找失物,沿著階梯不斷的往山上走。與此同時,一位住在山上較高處的年青人Uri,因感情生活弄得一團糟,又不想去服兵役,又想找一處烏托邦靜心完成自己的小說,於是一直沿著階梯下山,打算登上山腳對面的貨輪碼頭,坐船離開國家遠走他方去。
Moshe和Uri兩個男主角,沿著階梯一個向上走,一個向下走,途中遇到不同的社區街坊,有的是相識多年的好友,好像Moshe碰到一位事業頗有成就的律師好朋友,好朋友勸他,為何要花時間大海撈針找耳環,倒不如好好利用時間去找份收入穩定的工作,Moshe卻笑說自己有工作啊,就是那件為小孩帶來歡樂的「投幣式機動騎馬仔」。Moshe代表的,正是對昔日簡樸社會懷緬的老居民,慨嘆今天的以色列社會越來越物質主義,小孩只愛沉浸在手機裡的電動遊戲,不像昔日那簡單的社會,家長投一枚硬幣,小孩便樂乎乎地騎在機動馬仔上玩耍。
Moshe沿著階梯一直上山找,終於發現耳環身在何處,它不是丟在梯級上,而是在某位電視台男藝員的手上,他更得知,這男藝員原來是他老婆的外遇,且在一起已好幾年。他明白了,在回家路上丟失了耳環只是謊言,老婆根本不在乎那耳環,更希望老公與其花時間找耳環,不如好好去找份工作。老婆不在乎,因為她的心早已離開Moshe,只有Moshe才在乎那遺失的耳環,因為它正是二人的結婚禮物。
社會變質了,就連枕邊人也變了,夫妻間原來早已存在謊言,懷念昔日純樸社會的老實人Moshe,心情頓時沉下來。
往下走落山的Uri,其實好想逃離這國家,除了想逃避弄得一團糟的私人感情外,也在逃避價值觀不斷變得跟自己格格不入的社會,他想找一片淨土去完成他的小說,但這片淨土,顯然不在本土裡,唯有登上貨輪,跟貨物一起「出口」到外國去。
一個上,一個落,結果Moshe和Uri二人在山的中段相遇,原來二人已相識多年,因為Moshe正是Uri的小學老師,導演安排他們相遇的位置,就是二人當年的小學,他倆多年沒見,雙雙面向著那所小學細說當年,兩個昔日是師生的大男人,均在生活上各有苦況,雖然沒有很直白地訴苦,但相互對生命、對社會看法的交談,卻不其然互相啟發了對方。
Uri終於到了山腳,登上對面碼頭的大貨輪,正準備遠走他方尋找心中的烏托邦時,卻因沒買海上航行保險而要離船,他眼白白目送貨輪離去,轉身走回頭路,沿著階梯向上,一邊走一邊想到又要原地踏步,憤慨之下把階梯上有點鬆脫的磚塊拔起,並大力的把這些磚塊不斷向後拋(那刻忽然讓我想起香港年初一晚的旺角事件),卻被街坊上前趕走。Uri繼續往上跑,走進登山纜車站,在那兒搭訕了一名少女,二人一起坐纜車上山,Uri希望可進一步,少女卻表示已有男朋友,或許,這是上天要Uri先理好自己本身已一團糟的感情生活,不要再「節外生枝」了。Uri最後到達山頂,坐上一部載他去服兵役的車輛,是的,一切也沒法逃避,逃不掉這城市,唯有想辦法讓自己適應這土生土長但卻變得格格不入的家鄉。
Moshe人已中年,沒有一份穩定工作,跟妻子的婚姻又出現問題,且更住在較窮的山腳社區,即使心地善良,在港澳社會的「標準」來說他就是一個「loser」。他抵達山頂的高級社區,走進一家大型購物中心內,見一老婦人在哄正在扭計的孫兒玩「機動騎馬仔」,他於是把身上謹有的幾塊錢投進這馬仔內,馬仔開始起動了,他抱起這小孩,放他在「馬背」上,讓昔日小孩愛玩騎馬仔的畫面重現,想像自己回到從前那沒有謊言、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簡單快樂的時光。
Moshe懷念昔日的海法,就像好多澳門人懷念澳葡時代的澳門,那時的澳門雖然不富裕,但城市空間沒有現在這樣擠迫,坐巴士截的士比現在容易很多,且樓價便宜,大部份人輕輕鬆鬆工作便可以買到舒適的房屋,吃一頓飯也價廉味美,高樓豪宅也比現在疏落很多,在路上散步也可呼吸到新鮮空氣,但現在的澳門,很多人都想好像Uri一走了之,但因為沒錢沒資格移民,加上樓價太高供不起樓,倒不如把打算供樓的錢花費在旅遊上,於是有不少人一年都會去幾次旅行,借旅行來短暫逃離澳門,而每次旅程完結,就會像Uri一樣,始終離不開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唯有學習讓自己適應這本來應該屬於澳門人,但卻變得有點陌生的家鄉。
《男人的階梯》似乎跟澳門一起呼吸,都是徘徊在懷緬和逃離,電影節的紀念特刋有節錄導演Elad Keidan的一段話:「現代的以色列急於在古蹟上建設,成果就像一堆瓦礫……柏林圍牆倒下之後,變革也來到以色列,即使我國一向屬於西方。變了質的美國夢侵蝕我們同舟共濟的國民身份,購物中心、有線電視及高層住屋瞬間湧現,而且無聲無息。我們的父母早已質疑社會大同,現在越加祟拜個人利益。海法的山邊舊城,反映了昔日價值被掏空,這區就像一條來自遠古的蜥蜴乾屍。」
似乎澳門的情況也差不多,大型酒店賭場、高樓豪宅、珠寶金店、藥房、連鎖化妝品店瞬間湧現,而政府和發展商也夾手夾腳拆拆拆,近幾年已有很多值得保留的舊建築被剷平,且在民間反對聲音不絕之下卻堅持拆愛都、拆山頂醫院近加思欄的葡式灰藍屋,更讓貪婪的發展商踐踏路環,破壞疊石塘山體,並興建佔地相當於五個標準足球場、樓高達四十層的高樓豪宅。澳門昔日的美,就被政府高官和賤格發展商合力一起掏空了。
某些高官和建制派議員常說:「我們要向前看!」這個「前」是甚麼?是「前」還是「錢」?是眼白白看著發展商為了錢而繼續掏空澳門?!是眼白白看著某位高官為了增加個人的荒謬政績工程而把澳門變成蜥蜴乾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