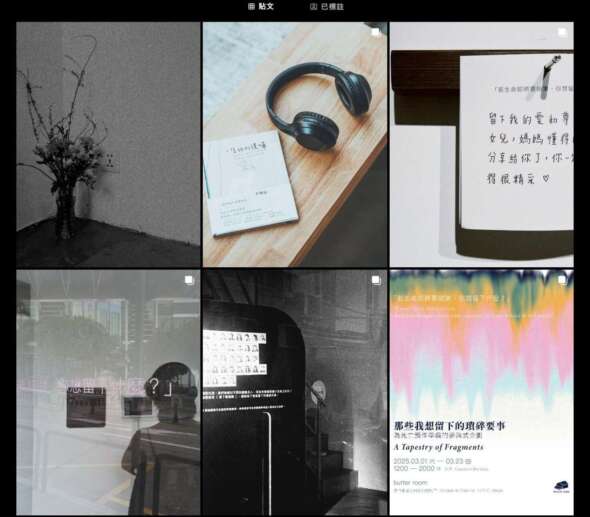端午節前一天,從昔日老師口中得悉一個非常令人惋惜的消息,筆者兒時的學姐、本澳的殘障硬地滾球代表隊成員,於前往波蘭參加「BISFed2015波茲南硬地滾球世界公開賽」期間,突感身體不適,隨後送院救治,於六月十七日不幸離世。當然,死因會否有其他內情,怎麼一個運動員會突然發生此等突發的事,甚至會方對身障者參與運動的體能以及身體素質要求等複雜的問題,皆非常值得研究,不過,筆者暫時未能掌握太多資訊,並不打算作一些揣測和評論,因這對大家都很不公平。筆者只希望她的家人、朋友、隊友以及身邊的人,能放下傷痛,過好每一天。甚至時常憶起她曾經的努力,讓她成為我們軟弱時的支持。
筆者對她的回憶,始於大概十八年前,當時,我們都是某校的融合生,她是個肢障者,她比我高兩級,每天早上,無論晴、陰、雨,她爸爸都用單車載她上學、放學,也是由爸爸用單車載她回家,後來到中學後,也許是家中經濟條件好轉吧,交通工具由單車變了電單車,兒時我們會一起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這爸爸經常鼓勵我「無論如何,要讀飽啲書」,然而,這在那個年頭,是一個很先進的想法,至少,當時校內其他融合生的家長,都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大部分身障者的家長,對身障者的期望,都是過得一天就一天,我相信正正就是這位父親「先進」的思想,影響着他的女兒,成就了她後來學有所成,也在無形中祝福了筆者本人。
當然,單靠父親一人的期望,總不能這麼簡單,每個融合生的成功,校方、老師、同學、朋友等,缺一不可,例如她要去音樂室上音樂課,總不會是老師親自把她的輪椅推下去,同學這時候便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最實際的,她要解決「大小二事」,也需要學校職員協助;在面對情緒等方面問題時,社工也要及時提供支援,此等種種一切一切,真的很難以一千幾百字來一一道來。不過,大家需知道,這些事,全都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何問題?
根據教青局資料顯示,本澳《特殊教育法》於1996年出台。那個年頭,無人會關注太多這些學校的融合生需要,局方不會提供什麼所謂評估,也不會資助你買些什麼輔助用具,教師沒有什麼「一百三十小時培訓課程」,在類似這種情況下,老師依然願意繼續教,當時的老師學歷都很高嗎?筆者相信,當時部份老師,連「融合教育」四個字都還未聽過,學校依然願意這樣接納一個學生,同學也照樣與班內的身障者相處。當時,無人會三朝兩頭就開個什麼記者招待會,喚起傳媒關注這些學生,也不會搞些什麼研討會,向政府領取資助邀請嘉賓來教我們(甚至政府)怎樣做,同學也不會說什麼「我們不懂與身心障礙者相處,要求搞些什麼培訓、說明會」等的東西,大家依然在互相尊重、有愛的氣氛下,讓願意讀書的融合生,享有讀書的機會,透過「讀書」,打破大眾認為他們充滿厄困的人生。
當然,我不是說政府甚至民間團體現時做的工作都是枉然的,因那個年頭的不足,令當時的身心障礙者遭到很多不公甚至不理解的情況,也爭取不到他們應得的權益,例如課外活動等。但正因政府現時在措施方面「踏前了一步」,有助鼓勵身心障礙者的家長,把子女送到學校去,也因為民間團體的努力,政府更關注這一群人的需要,媒體以及社工等的進步,讓更多人了解到身心障礙者的感受,教導學生們要尊重,締造平等社會。
不過,硬件的進步是容易的,觀念的調整,才是最難,也是問題關鍵所在。我們總不能像澳門社會一樣,資源充足了,質素反倒卻下降了。因為政府提供了培訓的平台,因此協助融合生的責任就全壓在受訓過的老師身上,因為輔助用具先進了,同學反而更少關心「如何好好與融合同學建立良好關係」,因為傳媒以及民間團體的聲音大了,身心障礙者本身,每每遇到任何問題,便馬上「疾呼了再算」,從不內在反思怎樣克服困難。這無助於推進本澳的融合教育,甚至共融社會,反而只會造成更大撕裂以及更多的不理解,最後影響自身群體將來融入社會找工作。現時社會上雖然多了很多「有識之士」投身於教育事業,不過產生的,更多是「教育評論家」,老實說,共融問題,就如性別平等、種族共融一樣,爭論多三五個世紀,可能也無法歸納出「好的定義」。教育不踏前,學生就無機會,最後受影響的就是學生,所以,假若個個都做「評論家」,沒人真正為融合生做點實事,我這位學姐的故事,便可說是「後無來者」。同時,筆者也見識過社會上有如此這樣的一類人,他們不是評論家,他們貌似也是為有需要的人盡點力的,不過每次做完後,都會「利用」「面書」和「朋友圈子」宣揚一番,美其名喚起別人關注,更多其實是在宣傳自己「功德無量」。然後被受助的當時人看到,馬上泛起一種「被使用了」的感受,繼而懷疑對方的真誠,誤會也就由此而起。
我常跟視障朋友說,你們是「盲人」,但不要把自己搞得像個「蠻人」一樣,也跟聽障朋友說,別人叫你們「聾人」,你也不應把自己關在「籠」裡。學姐美珊,雖然人已遠去,但她親身說明了一件事,從來只有自身努力所說出來的話,才是最有力的說話。
望與所有身心障礙者、健全同學、老師、社會人士以及所有讀者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