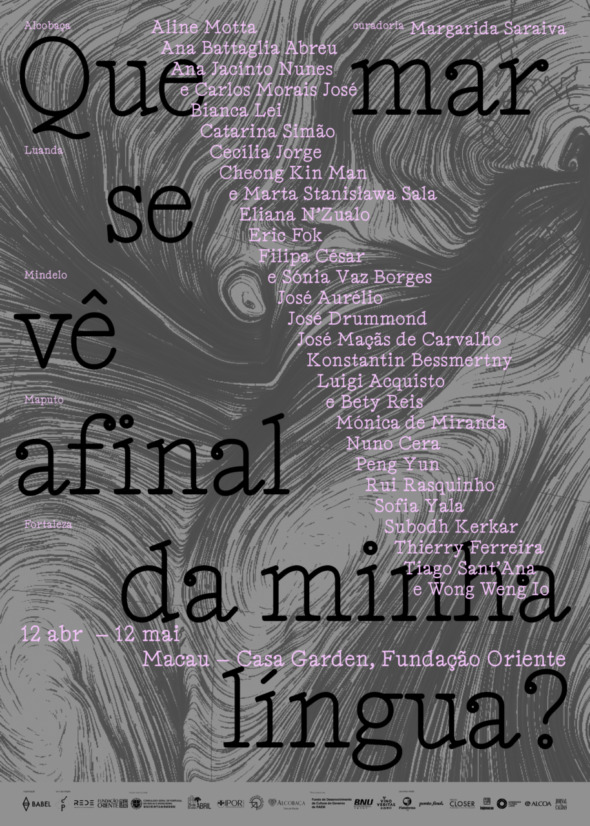這幾日腦袋熱熱的,為的,竟是藝術。
藝術二字,從小被告知的,是畫畫、音樂、雕塑的代名詞,它是特殊人享用的;行蹤隱秘,多在各種空闊莊嚴的博物館里陳列着,只可遠觀。「俺不懂藝術」,是普通人拒絕進入藝術博物館的理由。子女選擇了藝術家作為職業的華人家庭多被以為家門不幸,「藝術能當飯吃嗎」,這是家長們的鄭重勸誡。而這幾天我所看的紀錄片,我所聽到的講座,給了我很大的震撼,為我腦中理科生慣有的藝術正了名。
原來藝術是可以當飯吃呢!看《稻米是怎樣煉成的》,幾位香港的藝術家捲起褲腿,走進淤泥里,種起稻米;「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學者,也念着佛經就種起田來。若只是這樣籠統說來,像是個類似古人歸隱的故事。但故事須聽細節。這種稻的細節先是一本寫不完的書了。也曾在柬埔寨同一幫志工一起耕作過一塊200呎見方的小菜田。光是掘土、做田壠、用現成牛糞施肥、播種,已讓十幾人精疲力盡了。何況種水稻是一個經歷育種、播種、建防雀網、收割、打穀等諸多工緒的漫長過程。更不必說日晒雨淋、面朝黃土背朝天,還有咬人很疼的紅螞蟻,那是農人的日常了。
離開冷氣辦公室,做這辛苦萬分的農活做甚麼?新生活運動呀。在被地產霸權壓得透不過氣的香港,尋找一種自己自足生活的可能。他們就是「菜園村生活館」的開創者,當年香港反高鐵丶反強拆的示威轟轟烈烈,他們算是「幕後黑手」。一群藝術家,用把身體交還給土地的方式,跟聲勢洶洶的發展主義作抗爭,明知自己不過是站在雞蛋的那一方。電影里有一幕,綠油油的菜田外,天秤丶推土機忙碌的身影,發出嘈雜的聲音,藝術家們則在擊鼓,既有一種無力感,又感覺充滿希望,令人陷入思考:到底人是該繼續用推土機征服世界,還是應該稍停,去探索更加自己自足,擺脫與土地的疏離的新生活的可能性?雖然最終的收成只能勉強收支平衡,但這與大流逆向而行的充滿思索的種田行為,在我看來,就是最迷人的藝術了。
而竹圍工作室的蕭麗虹與吳瑪俐的環境藝術,則讓我看到藝術可以是每個人的日常,同吃喝拉撒一樣。早期吳瑪悧開辦玩布工作坊,讓深陷婚姻絕望的主婦,用傳統縫紉講出自己的故事,得到自我治療,再同別人分享作品找回自信,從而生命被翻轉。又策劃「北迴歸線環境藝術行動」,在嘉義縣的各個村落派駐村藝術家,用藝術來建立學習社群,在當地營造了令人讚歎的社區文化。藝術除了純粹的藝術,還應該有回應現實,充當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橋樑和推動社區文化的功能,吳瑪俐這樣說。
為了可以長久的持續,吳瑪俐選擇了自己生活的地方──樹梅坑溪,嘗試用藝術重新縫補生活與土地的裂痕。可是這並不是藝術家一個人的事,而是整個社區的事。她想到利用穿過他們土地的一條小溪的水作連結,這條溪從上游的清澈野溪變成下游污穢的排水溝,過去的美好記憶和現實的反差讓沿溪的居民有了對話的可能。至於如何對話,吳瑪悧想到舉辦一月一次的早餐會,早餐會採用當地食材,且提供了當地社區公私部門的對話的空間(在現今都市,大家各說各話,對話是多麼難能可貴)。她還邀請藝術家進駐校園,開設藝術課程,跟未來的主人一起,在破碎的土地上想象新的可能,最終達至改變環境与生活方式。讓這個「臥房城市」變成「都市村落」,每個人都是藝術行動的一分子。
駐村的藝術家們用各種創意,比如在被人們嫌棄的青苔和鐵鏽上作畫,為「垃圾靜物」拍攝肖像,創造全新的舞蹈形式Eco Dance,把自己變成一個盆栽跟村民們對話,聆聽對樹梅坑溪最真實的聲音。這些融入村民日常的一系列藝術或行動的最終結果,不僅推動了社區文化,得到官員為改善環境作的承諾,甚至還推動了環境立法。現在台灣法律里有強制推行環境教育課程這一條,也是這次藝術行動所爭取到的。
這讓我想起英國的生態藝術家大衛黑利的藝術行動──將烏佛斯頓的一條地下化的小河挖出來恢復生機。這期間,他走出藝術工作室,也經歷了與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對話。
不只著眼於內在的探索,還走向大眾的參與,和較明顯的現實效果,這些,便是環境藝術的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