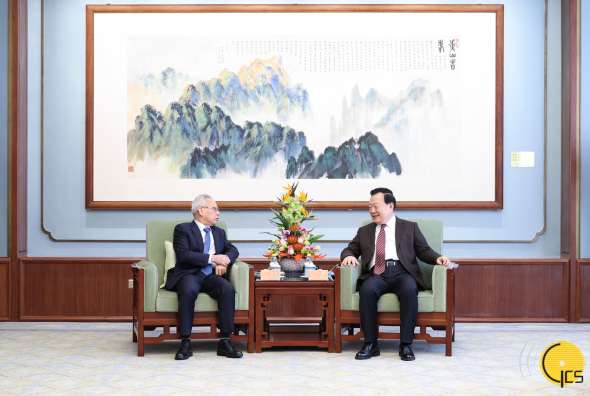如何行文,思緒很混亂,因為要紀錄的感情太複雜了。要寫的是自1989年6月4日以來這二十四年壓在心頭的一種不能言傳、無以名狀的痛。而它又如一位稚齡逝去的朋友一樣沒有人知道,沒有人了解,像傳說一樣被懷疑。可怖的是認識它的人也漸漸把它省略,它的形象開始變得糢糊,它的事蹟開始被淡忘,它的渴望與追求無人提起遑論繼承,甚至人格被歪曲、德行被誣陷也沒人肯為其平反,它只是一度沒痊癒而隱隱作痛的傷口被時代擱在一隅不曾處理卻跟其他傷口爛在一起。年輕人混在當中不得以看見,不知其所以,只聞其腐爛的氣味,也正因為習以為常,就不願多理。然而腐臭告訴我們死亡的危險,流血告訴我們失血的可怕,於是有人願意以死亡換取生命,以失血阻止流血,以失去自由解放自由,企圖告訴我們存在的矜貴、茍活的卑賤、仁德的尊嚴、卑鄙的下流,結束指鹿為馬的年代。
這可能僅是一篇私人日記,也是唯一公開的一篇,目的是拒絕遺忘。
跟其他走過那年那月那日透過各種眾多資訊渠道跟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上萬條生命同呼吸的所有中國人一樣目睹了一場滅絕人性的屠殺,雖然我並非親歷劫難的人,沒能像採訪事發當天的香港記者和事發時留守廣場的香港學聯代表同學一樣跟你說第一身見證。也沒能像眾多六.四生還者、倖存者,或因此坐過牢,或因此流亡去國;成了民運人士的昔日廣場上的學生、工人和巿民 一樣跟你說他/她們的慘痛經歷和去國悲情。我的說服力絕對不及一張血腥鎮壓的圖片。我的感染力絕對不及廣場上人山人海、旗海蕩漾、標語綿延的氣勢,以及那篇賺人熱淚的絕食宣言。我的影響力絕對無法與隻身擋坦克,其英勇震撼世界被外媒譽為Tankman的王維林相比。然而,這一切卻使我的生命產生了巨大而不可逆轉的變化,也許打從我以大學生的良知參與「澳門東亞大學關注北京學運小組」的工作開始及至於新華社澳門分社門外靜坐、設靈弔唁,一步步已被感化和感召:改良社會的責任認知愈發堅定,理想願景努力可近的信心,遭屠城後才會產生巨大的情緒落差。一種倖存者才有的死裡重生,為死去的而活的使命猶然而生。因此我的生命不再只屬於我個人。我必須用得其所。
又或者與其說得偉大,不如說得渺少自私一點,也許民主傳承是一種心理贖罪,因為廣場上眼見同代人之殉而我們卻安然無恙,我們憑甚麼有這種逍遙的福份,他/她們反貪腐、爭取言論自由的遺願一日不達,六四不平反,死難者家屬不得自由,不獲賠償,迫害還沒停止,屠城兇手仍不能懲治,這種種不能就是我們的失義,就是我們的罪。
故為死傷者討回公道,為民主薪火相傳,努力推進逐步實現地區的政治改革,為中華兒女開創一個更美好的生存環境,更符合公義的社會制度,更清明的政府,我們責無旁貸,因為我們擁有未來就必須掌管未來不應再由極權支配擺佈,這是我們的權利與義務,而逝者沒有。
五四是近代中國一場對民主科學的啟蒙運動,多番歷劫後的中國無以為繼。六四是現代中國再度對民主自由的啓蒙運動,經歷過六四洗禮的人,對民主追求有一份堅定的意志和毅力,可惜運動因為長期受壓於極權而變成忌諱,遂無法整理出一個具前因、後果,脈絡清晰有系統的文化精神體系。
一個時代對各種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的熱衷,促進了思想自由,激蕩起討論交流,對大量外國資訊的開放,對高階學術、對公義道德人權的渴求,正是那些被政權冠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化內涵作為後盾而帶動了這場波瀾壯闊的抗爭。可是,這些對改造社會的知識追求卻被「疏導」成今天不擇手段的金錢追求,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發展還是墮落都被混淆得徹底了。
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體制改革,就如一個長短腳的跑手,先天缺陷將是其成就的局限。長此下去,勉強落場只會令身體痛楚加劇,虛脫倒下,旁觀者無以施救!
一個道德敗壞不思悔改的殘暴政權,歷代史實早就告訴了我們它的下場。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於是無數的虫背上了義
就注定給踩在地上
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
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然而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殺人者無報應
我只相信
只要願意播種
終有一天所有人也會
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我要告訴大家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註:詩句分別出自顧城的<一代人>、北島的<回答>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懿靈只作抄錄拼貼編排而已,是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