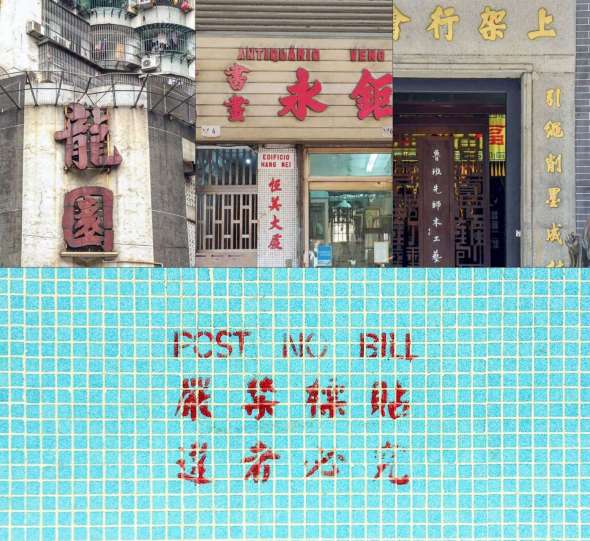日前,參加了一個反對海洋公園奴役海豚的活動,其主打口號非常有意思:「海洋劇場強洗腦,扮晒保育呃(騙)細路!」海洋公園,向來都是小孩子的夢想天堂,有青山綠水藍天白雲,加上海豚海狗的表演,創造了一個鬧市中的海洋世界。人們不需遠赴深海,便能與海洋生物共融。是真的嗎?有可能嗎?童話的幻象,往往悖離現實。動保團體告訴,當園方人士宣稱海豚是「自願表演」,「喜愛玩樂」的時候,這美麗的童話背後,是海豚必須每天表演六場,才得裹腹,身體會因過度表演而致「跳躍乏力」、「翻騰失敗」,甚至不育及壽命減少。童話會洗腦,這才是真相。
近日,香港社會在熱鬧討論反對「國民教育」,擔心相關課程會產生「洗腦」的效果。事實上,紅色政權和其他獨裁政權透過課本、宣傳品、電影甚至音樂進行「洗腦」,已不是新鮮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九三四年,德國納粹黨上台翌年,希特拉飛往紐倫堡召開納粹黨大會,並邀請非常崇拜希特拉的導演Leni Riefenstahl’s以這次黨大會為題材,拍攝了《意志的勝利(Trimph of the Will)》,電影中運用了獨特的拍攝手法及華格納宗教式的音樂,成功塑造了希特拉「神」的形象,凝聚民心,成為二戰期間德軍雄獅的精神堡壘。從今天的眼睛去看,《意志的勝利》當然是一部成功的洗腦電影,如果不是,美英等國不會一直禁止該片上演,直到二零零四年才解禁。然而,如果今天的政治人物要繼續進行洗腦,還會用Leni Riefenstahl’s的拍片方式嗎?如果他們聰明的話,應該不會。看看前兩年北京拍的《建國大業》便知。電影中,天安門城樓上向萬眾揮手的毛主席,已經走入凡間,他會大醉陶陶,會睡懶覺,會發脾氣。為什麼?因為導演深懂,這是一個英雄沒落,個人主義抬頭的年代,再為毛澤東展開造神運動,只會引起觀眾反感。只有突出政治人物人性化及溫情的一面,才更易讓人動容。這是一種洗腦嗎?當然是,但它會被指罵作「洗腦電影」嗎?比較不會。更不用說,肥皂劇、瘦身廣告、口沬橫飛的phone-in節目了。
於是,我們看到,原來,「洗腦」至少有兩個層次的,一是「可辨認的」,像今天大家反對的「國民教育」;另一種,可能是大家「視而不見」的。第一種,比較容易辨認,像香港特區政府要施行國民教育,部分教材中,居然毫不掩飾支持目前「執政集團」的模式「進步無私」。這對於每年還有十多萬人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來說,情何以堪。更何況,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香港人」的身份短時間內出現,有時候,它跟「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並行;有時候,它更可能超出「中國人」。於是,我們看到,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一浪接一浪,群情洶湧,數以萬計人士走上街頭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設立。
相對於第一種鮮明的洗腦教育,第二種,卻是像針孔一樣細,它無孔不入,深入社會不同系統,像遊樂園、教會、家庭、學校、媒體等等,這些洗腦,大家都「看到」,卻較難「認出」,所以稱作「視而不見(invisible)」。譬如,一些主流媒體及政治人物整天宣稱要「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然而,什麼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們的定義是「法治」和「民主」。於是,法治與民主,就成了香港「不可被懷疑的信仰」。然而,其他的核心價值呢?像公義、公平這些價值,是否更在法治和民主之上呢?法治和民主的存在,是否只是追尋一個公義和公平社會的手段呢?有關這一些,都極少被提及,尤其香港經歷「六七騷動」及七十年代金融服務業全面開放,新自由主義橫行,公義,尤其是公平,甚至是社會主義,往往被污名化。於是,我們看到,在這個社會,綜援制度,本來是補充社會機制中的漏洞,讓一些無法在這種機制獲得合理生存條件的人的一些補償,然而,透過媒體及部分公眾人物的渲染,卻變成了「養懶人」的制度。另外一些社運人士,提出「全民退休保障」,希望曾經在這個社會辛勞工作的人,晚年生活可以獲得基本的自主及保障。然而,這種對老人家的保障,卻被扣上「社會主義」和「福利主義」之名。問題是,為什麼在部分國家裡,人們在這些制度之下,工作時數得到保障,住房得到保障,貧富懸殊相對接近。而香港,貧富懸殊為亞洲最嚴重,堅尼系數為0.537,排在全球前列,住在劏房的人口倍數上升、薪水永遠追不上通漲。可惜,這些情況又被「自由市場」的美麗光環所蓋過,變得不被重視。
於是,我們看到,當反對國民教育的有數萬人參與,而且聲勢浩大的時候,打著「反對資本主義」旗幟的「佔領中環」行動卻被匯豐銀行及政府部門合力夷平,而前往聲援者,只有零星數十人。
有人說,「反資本主義」,是痴人說夢話。也許是的。然而,即使不是「反對」,我們總可以「反思」吧!一旦反思,就會發現,資本主義進行的洗腦,何其無孔不入,何其鋪天蓋地。從海洋公園的海洋劇場,月熊被抽膽汁,生意人不是為了賺錢又是為了什麼?了解海洋生態,不是應該到海裡去嗎?想要清肝火燥火,不是去喝一杯夏枯草便可以了嗎?為什麼要殘酷對待動物呢?原因很簡單,不將產品的製造過程包裝得美麗一點、形容得艱辛一點,又如何收取更高的價格。然而,在這包裝的過程中,就是有動物會受苦,而這是我們「視而不見」的。
一九六七年,傅柯(Michel Foucault)和杭士基(Noam Chomsky)接受荷蘭一個電視台邀請,出席一個對談節目,在談到改造社會的時候,傅柯提到,一般人會認為,是政府透過行政部門、軍隊和警察,在控制社會。然而,要注意的是,政治權力無孔不入,它同時滲透進學校、家庭、傳播媒界等機制,然後用不同的形式呈現。這是傅柯有關「權力」的最初步思考,到了1975年,他完成《規訓與懲罰》後,這個有關權力無孔不入的分析,更是完整。因此,當我們在思考「洗腦」的時候, 也須同時認清:「可辨認的」,以及「視而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