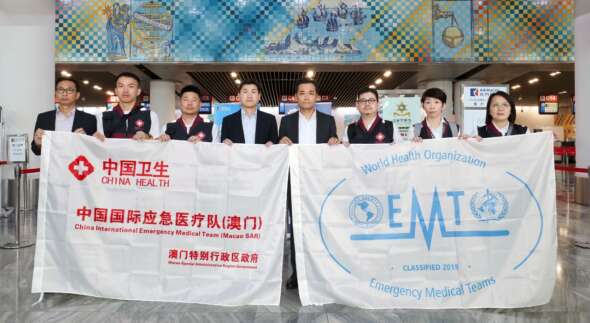當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地理學家、社會思想家David Harvey,在他的文章〈地租的藝術:全球化、壟斷與文化商品化〉中,提出「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概念,用以解釋「文化商品化」(也就是現在澳門很流行的名詞: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在其運作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矛盾。我想在這裡介紹一點David Harvey「壟斷地租」的含意,以及對文化創意人該如何面對國家/政府高調推動文創產業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對一貫反智的社會來說可能無聊,但對牽涉其中的文化創意人來說,卻是一個另類的思考角度,以及作為一種機會和應有警惕的提醒。
David Harvey使用「壟斷地租」這個抽譯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冊的概念,指稱社會行動者透過佔有在某些關鍵面向上,具有獨特而不可重複性的資源,例如:可出產頂級美酒的葡萄園或是位於市中心的房地產,並延伸概念到目前越來越多的「文化商品化」現象,在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
文章一開頭,即說:文化已經成為某種商品。但是一般人仍然認為,文化產品與諸如衫裙、手袋和鞋類等尋常商品不同。雖然,界線已經非常模糊了,例如村上隆為法國品牌路易·威登設計的手袋等產品,即難以區分是商品或藝術品;又或者近年連中國也已經成形的以畫廊、拍賣會為基礎的藝術品炒作市場,則藝術品完全成為了投資產品。那麼,這許多堪稱文化的現象,其作為商品的地位,應該如何與其特殊性質取得協調?值得文創人注意和思考。
亦即,今日的文創人、以至藝術家對比小商人階級、工人階級,有多少自主性、特別之處?在一九六0年代的西方,藝術學院是激進討論的溫床,藝術家是前衛精神的代表,質疑現實政治、不與主流社會價值和權力妥協。他們後來歸於平靜和專業化,嚴重削弱了活躍騷動的政治。在一九九0年代的澳門,亦曾經出現過這樣的藝術群體,經歷了類似的歷程。
近幾十年來,都市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在國際上變得重要。都市企業主義是指都市治理中的行為模式,它混合了國家權力(地方、都會、區域、國家或超國家),以及市民社會裡各種組織形式(商會、工會、教會、教育和研究機構、社區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等),以及私人利益(企業與個人),以便形成推動或管理某種形式之都市∕區域發展的聯盟,國家/政府的權力則充分穿透了本來存有戒心的文化藝術圈。而一個城市對本身文化的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等宣稱,構成了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那麼還有什麼領域,可以比歷史建構的文化產物和實踐,以及特殊環境品質(例如獨特的城市氛圍、世界文化遺產等),更適合提出這類宣稱呢?因此,文化創意產業則往往成為近年都市企業主義建構城市形象、城市發展的策略性選擇。
David Harvey以巴塞隆納近期的歷史示範為例子,發現該城市對知識和世遺產業、文化生產的活力和騷動、簽名式建築和獨特美學判斷的培養,在許多地方(尤其是歐洲)都成為都市企業主義的強大構成要素。巴塞隆納在歐洲城市體系裡崛起,佔有優越地位,部分是基於它穩定地積聚象徵資本,以及累積區辨標記。就此,對於特殊的加泰隆(Catalan)歷史和傳統的考掘,其強盛藝術成就與建築遺產(當然是高第〔Gaudi〕)的行銷,以及獨特生活風格和文學傳統的標記,都逐漸呈現,並有洪水氾濫般頌揚其獨特性的書籍、展覽和文化事件加以支持,構成了完整的文化創意產業系統。
隨著以巴塞隆納作為一個城市的集體象徵資本為基礎(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為表彰其建築成就,頒給整座城市獎章後地產價格就一飛衝天;澳門歷史城區得到列入世遺名錄後的城市變化效果,可堪相比),展現出豐富的汲取壟斷地租機會,其無可抵擋的誘惑,就吸引了更為均質的多國公司商業化踵步其後。後期的水岸開發,看起來就和西方世界其他地方是一個模樣,令人茫然無助的交通阻塞,導致了開闢穿越舊城區的大道的壓力,國際連鎖商店取代了地方商店,縉紳化(gentrification)移除了長期居住的人口,破壞了舊都市紋理,巴塞隆納因而失去了某些區辨標記;甚至還出現了某些明顯的迪士尼化跡象。這種矛盾充滿了疑問和抵抗。要頌揚的是誰的集體記憶?誰的美學才真的算數?為什麼要接受任何形式的迪士尼化?
巴塞隆納的例子,其實急速出現在澳門鄰近的城市中,從本地文創人津津樂道的北京七九八藝術空間、上海田子坊,以至在政府推動下,每個亞洲城市都會出現的文創產業空間,等而下之的是三、四流城市的以文創產業空間、活化舊區為包裝的地產壟斷地租項目。高度管理、要求營商效率的所謂文創商品旗艦店,不就是迪士尼的管理邏輯嗎? 最近北京藝術家在不同的藝術村中被地產商趕走,即是這種趨勢的最真實呈現。
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西方文化藝術的生產者,例如音樂家、畫家的身份從專門服務於宮廷與教會的僱傭漸漸轉向成了市場上販賣自己作品的自由藝術家。從以前那種只替貴族主教服務的狀態漸漸變成了市民階級文藝消費者的供應人。隨著文化藝術生產者的收入來源改變,地位亦從依附於權貴的「家臣」逐漸變成具有獨立自我意識的「藝術家」。觀乎本地文創人士,既希望政府全面扶持文創生產或其實已經成為政府服務的長期供應者,又多次希望公權力介入要求本地或跨國資本購買本地文創產品。文創人不應該保持警惕嗎?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文創人既接受國家/政府及資本全面的穿透,如何仍能保持具有獨立自我意識的「藝術家」?如此一來,國家/資本經常在文化生產者之間造成廣泛的異化和怨恨,他們經歷了自己的創造力遭受因經濟利益而被挪用和剝削的經驗,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整體社會也會因為本身的歷史和文化受到商品化剝削而憤恨(想像一下澳門人對歷史城區、生活環境變成旅遊景點的感受)。對抗性運動的課題,便是要關注這種普遍的異化和剝削,並且運用特殊性、獨特性、真實性、文化和美學意義的確認,開啟新的可能性和替選出路。
對於抗拒自己再次成為權貴的「家臣」,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人士作出了各種的努力和嘗試,例如展現於西雅圖、布拉格、墨爾本、曼谷和尼斯,以及更有建設性的,於阿烈格爾港(Porto Alegre)二00一年世界社會論壇,都指明了這種替代政治。它並不完全敵視全球化,但要的是非常不同條件下的全球化,奮力爭取某種文化自主性,以及支持文化創造性和分化,以社會連結為焦點,積極建構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新的真實性、原創性和傳統的定義。對澳門文創人而言,真正有前途的出路,一如十七、十八世紀之間得到獨立的文化藝術生產者,是你的產品真正可以呼應市民的生活狀態,可以表達當下社會的不滿,而非寄望當權者為你去創造出虛假的大眾消費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