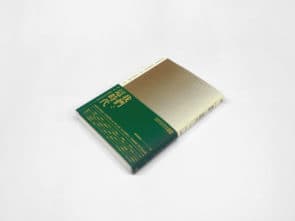傳說中的一口井。
也許閱讀從未在澳門流行過。 更遑論與書店、獨立書店、出版業發展及困境等有關的討論。 本期封面專題提及香港和台灣的各式書店,在當地早就開得成行成市,無論是大型連鎖書店或微型獨立書店,一概任君選擇⋯
不知名流行病肆虐,全城恐慌,各地政府處理手法尤值得商榷。事情發展得看似迅速,令人措手不及,我還來不及看《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來把裡面的不平等世界和現實作對比——過去在種族屠殺和傳染⋯
經過南灣的人都知道,現在的海灣其實不太能稱得上是「灣」。那蒼海有點遠離視線,冷看熱鬧劃破湖面;不太蓊鬱的人工孤島肅立在人工湖泊之中,早被新的鳥群所指認。兩旁安插高低不一的大樓干擾思緒,打擾那試圖⋯
「不好意思,反送中或其他政治議題都不能做。」我收到出版方這樣回覆我,然後我被他們 DQ (Disqualify)了。 大約四個月前,一個自詡為出版 Zine 的澳門藝術團體,邀請我做一本 Z⋯
老實說在懂事以前,我從來不曾停下來觀看過下環街,現在回想,我都不自覺地跟着她走,不,應該說是她總牽引着我,守候着我的成長,在同一條街上,虛無地來來回回穿梭。當長大後忙於生活和工作,經過不同的城市⋯
這是一個多麼漫長的六月啊。 全世界都在觀看着香港瀰漫的淚水和血汗,跨越界限,我好幾次看着天空和雲影交織着光,從中等待黑暗再度來臨,月光和烏雲每翻一頁,凝視着細縫那擠出的暗光,映照出受傷的人淌着血⋯
在新年長假期,我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旅行了一趟。 由家門開始算起,大約十五分鐘就可以走到市中心,然後到達那片所有本地人都會面有難色地搖頭的地方,也是所謂古蹟臨立的老城馬路,塞滿車水馬龍的觀光人流,無⋯
在所謂高科技的年代,我們要得到資訊很方便,資源看似免費無限,虛擬平台是我們習慣依賴的溝通方法,世界隨時在身邊也是理所當然。過去,我們不懂所謂資訊是平的道理,盲從順勢活着活着,現在,我們卡在一塊世⋯
每到節日,就要忍受大量劣質的人造景色。 每次面對這個城市的美感,供我仰望的事都讓人敢到無力,這個在空間中發生的事,總隔着不同的碰撞,失序。「真的討厭死了」,路上行色匆匆的人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說。而⋯
我在這個六月,做了一個關於創作的實驗:辦了一個關於 Zine(小誌╱獨立誌)的展覽,確實有種沒頭沒腦的衝勁。老實說,本身吸引我的並不是 Zine,我對 Zine 也說不上特別鐘情。反而是我過份堅⋯
一個城市生存的蛛絲馬跡可以從她的墓園裡找到。 澳門之所以獨特,並不是她有不會打烊的賭場、所謂中西交融的人文風情、日不落的拍照打卡古蹟遺產,以上皆是,但也皆非。因為這裡從很久以前就有人在生活,而人⋯
這時代一瞬即逝。時代──每個時代都自認是現代人的我們,沒什麼人在乎這所謂現代,我在故我在。社會瀰漫着平靜和等待,也說不上暗湧,人們並不悲慘,但也不太幸褔,埋頭工作,偶然喧鬧劃破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