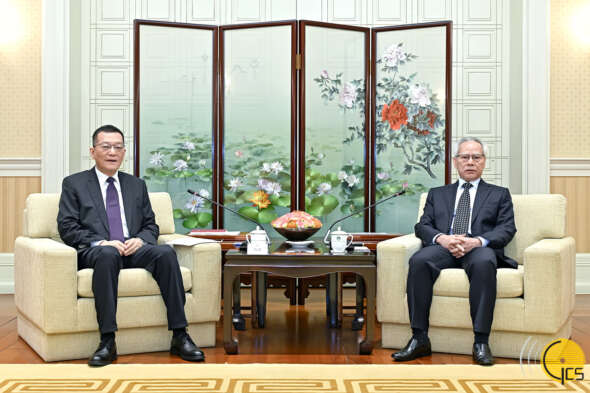婉儀見到我,還是有點意外的樣子,雖然我已經告訴她,來了,在新馬路,很亂。還是來到了,第一次,我在對面就猜到一定是這裡了,婆仔屋,牛房,叫甚麼也好,很藝術的小舊地方,我很少去。他們在小吃談笑,她送我入房間—也就是她的展覽空間,說,裡面有你見過的。
婉儀見到我,還是有點意外的樣子,雖然我已經告訴她,來了,在新馬路,很亂。還是來到了,第一次,我在對面就猜到一定是這裡了,婆仔屋,牛房,叫甚麼也好,很藝術的小舊地方,我很少去。他們在小吃談笑,她送我入房間—也就是她的展覽空間,說,裡面有你見過的。
我想我當然會見過。她的房間。
我們在倫敦。她的房間就是她的廚房。睡的地方在樓上。我們在廚房喝茶,吃她煮的麵條。房子很冷。多年後我仍記得,很冷很冷,在房子裡要穿大衣的房子。我站在細小的客廳和她說話。
因為冷的緣故,到廚房就暖和起來。
她後來說在廚房見到我在下面球場跑步。頭髮揚起。那時候我們都留著長頭髮。
我以為我在說她,我見到你在下面球場跑步,頭髮揚起。
我真的見過,那一幅清裝女子,翹起腿,臉容換上婉儀的樣子。
她將這幅畫掛在廁所門上。在廁所我細細看這幅。
真奇異。我再見這幅畫,安好如昔,在一個場地。
我們都經過時間了。畫沒有。
我見過,我怎會沒有見過。十一年前,她做了一套布包書,書打不開她說是女書的秘密。但我從來沒想過書打不開。對我來說,沒有書是打不開的。
它不過沉默。它沒有拒絕。
圖像原來是朋友替我們拍的劇照,我的腳,我以為承受眾多的腳嘿其實,很普通的一雙腳,在她的女字重疊。
是不是那時我們還沒有現在那麼老呢,我記得布的昏黃,但是簇新的昏黃,而不是現在的,已經褪色,斑駁暗淡的黃。
我拿起書,想,這些書比從前好看。
因為我看過了,又再看到嗎?
但那一列布襆女字陰陽吊我沒有看過。粉筆捲字我也沒有看過。灰與破瓶我都沒有看過。
我也不知道她生活的一些部份。她去了澳門教書後我們便很少見,也很少傾談。
我沒有看過,但我知道。
我知道她父親的逝亡。她時常說父親。她的廚房其實就是她父親的藥行,都是瓶瓶罐罐。
我見到灰燼就知道了。那時她喜歡收集腐葉與骨。給我看她學做的,魚的標本。
焦木框架,我見過照片,沒有見過實物。
—-見過那麼重要嗎?我望著那一列重複的黑布包框。我見過和沒有見過沒有甚麼分別。
她的手。我見過多幅她的手的鉛筆畫,已經無法記得幾時了,可能她一直都有做。都在做同一幅畫—-我還是以畫來形容。
我們從維多利亞站一直走,走了幾個地車站。我記得我說想有一架單車。她有一架單車。
她說女書,那時候她剛開始。她說把博士唸完就結束,我說好哇。
我們是因「女」而相識。到後來我面臨生命的困境,與「女」無關,不過是人的基本存在問題。
因此我對她的「女」沒有很接近。
我也曾經以為我需要一個房間,我們都讀過維珍妮亞. 吳爾芙。
但後來房間崩倒。我很少讀女性作家的作品。
所以來看這個展覽,我有一點猶疑。
到我見到那幾隻手的時候,我就明白,作品可以超越形式。
其他人都不明白,當有人說她的作品難以接近的時候,我想開口說不。但我沒有,因為這不是我說話的場合。這是她的房間,她的物。
我經過,觸摸,回憶。
那是幾隻石膏手掌。兩隻用長袖連著,一隻手心向天,一隻手握著一皺紙。
那幾隻石膏手掌是我和她一起做的。在西貢她的小房子。
那是我生命最難過的幾年。她把頭髮剪得很短,人很瘦,小吃偏苦,無味,我說你真像小尼姑。
能夠做甚麼呢,我們一起做面具,然後我說,不如你做手。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做,不是很嚴肅的甚麼創作,好像兩個女子在士多打麻將,或做甚麼找零快的女紅,我們小孩的那個年代,我見到的師奶們(當時師奶是尊稱,有正常家庭的才叫師奶,我記得有個跛腳女子,被人叫黃狗婆,其實她一點都不婆),都在打麻將,做家庭手工業。
或工廠女工吧。我記得我中學去做女工,在生產桌上就講賽珍珠的《大地》給工友聽。工友都聽得很入神,說好聽。
女工—師奶,分享手作的樂趣,或悠悠時光。
或者那些時間,和婉儀一起做石膏塑模,既是治療,也是學習。
但我們不過在談這談那,不時興起罵起人來,冇有攪錯,等等,最粗魯不過如此。直到可以見到日落。我們說收工了,下去喝茶,吃點小點,她那些寡色寡味的小吃。
我做的面具都扔掉了,我沒有想到她留下那幾隻手,還做成了一件一件作品。
女書不過是某村某落的成員之間,一種傳遞形式;正如音樂,地氈圖案,都可述說,都可承傳。
我見到這許多年的作品,慢慢生成一間房間。房間有門,有框,有打不開的窗口。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間房間的存在。而當我們見到這一間房間,愈來愈完整,也因此,我也會視之為,房間也同時開始消失。
形式已經不重要。
我們說親密不是說部落的一種消失了的傳遞形式,我們說女容也不是說被複印在清裝女子之上的,婉儀的面容,我們說枯毀也不是焦木與骨灰。
我們說顏色也不是黑白灰。說空間也不是畫中的留白。
房間設置好,我們便不再需要房間。
如果藝術的終極是自由。經過美。
從可見之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