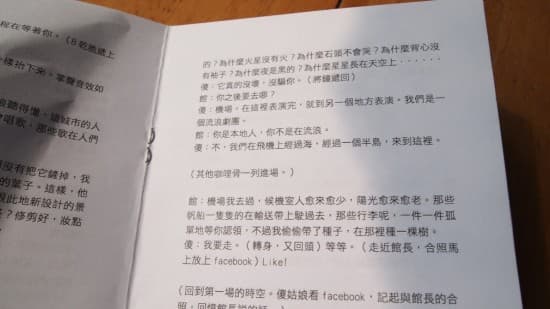在近年一些回應本地都市急速發展的劇場作品中,莫兆忠的《咖哩骨遊記》是唯一以地誌學(topography)形式來書寫的作品。故事講述一班遊客根據觀光博士咖哩骨的遊記而開展了『矮人國』的旅程,但很快他們便發現,遊記中所記載的許多地方,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找尋的過程中,產生了由「地方」到「自我」認同的游離和失落。這是一篇以想像和比喻構建的地誌學,以可堪玩味的隱喻和詩意的語言描畫出一幅虛擬、奇幻的城市地圖──矮人國的怪老樹碼頭、遺物回收博物館、即食麵博物館、照相機博物館、已經消失的名叫記憶的河流、傳說、詛咒、喚起死者生前記憶的彼岸花、矮人國的邊緣……一幕幕充滿心思的奇幻意象,對照着正在消解中的城市,作者的種種質疑、不安,尤其對發展中城市人文價值和文化獨特性被改變的憂慮,魔幻地揭示着現實,就像那彼岸花的香味,喚起了我們的記憶和思索。
地方認同:只是一場沒有『目的地』的旅行
故事從《離境》開始,這是一場沒有『目的地』的旅行,旅客們只要『能離開就好』(P.4),語帶無奈,但又非常真實,尤其在人稱『過客城市』的此城,尤其在過往,許多人都選擇離開這裡到外面求生活、求發展。事實上,這是一個『離開』頻仍的城市,有關的地方認同,只是一場沒有『目的地』的旅行,是找不到落腳生根的種子。
『毎個人有每個人的旅程/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情緒/我在一個半島上面/在海上面/我在一個新大陸上面/我在盛世的荒原上流亡/毎個人都帶着一粒種子/我可以在哪裡種一棵樹?』(P.5)──劇本中節錄袁紹珊《Wonderland》的詩句,這首詩就是在離開澳門的路上所作,抒寫那於現代都市、盛世荒原中未能抵岸的旅程,以及其中的精神流亡,這成為整個劇作的核心意象,串連起接下來的旅程。
『從記憶消失那一天起,咖哩骨就開始寫他的遊記。』(P.7)從這裡開始,『矮人國』成為一個在各種浮光掠影的旅遊敍述中不斷被想像重塑的『地方』,原有面目日漸模糊,終致難以辨認,記憶終於消失,對『矮人國』的介紹亦只剩下旅遊指南中的景點和眾多博物館。『矮人國』在『遊客』的敍述中,只是資料說明,沒有深刻的情緒和印象,『矮人國』就如全球化影響下那些變得大同小異的城市,只能靠生產各種『博物館』來擴充自身特色──甚至擺放不屬於本地的東西也無所謂,只要能產生旅遊和經濟效益就行了。(『即食麵博物館』P.9)
旅遊的興盛使城市發展完全傾斜,本來極為表面的觀光印象,却竟作為『城市』的主體。『久而久之,矮人國,也就成了一個除了道路就是景點和博物館的地方,甚至連道路也被塑造成奇觀供人遊覽。』(P.7)
這些年在被遊客『攻陷』和被規劃成『旅遊休閑』後,作者的警戒再明顯不過,更具諷刺的是,故事中保存死人物件的遺物回收博物館,成了唯一可印證人們生活的確切『存在』,而這個『存在』,是通過『不存在』來證明的,『不存在』還包括備受忽略──『奇怪的是,像矮人國這個那麼重視遺產的地方,從事遺物回收的人卻只有一個。』(P.18)
其他博物館得到保存和發展,然而堆積着人們過往生活物品、承載著記憶的遺物博物館却要拆了,就如那些對獨居老人的遺物不感興趣的親屬一樣,只看重更具旅遊和經濟效益的那些遺產,任由記憶清澈之河被填塞,怪老樹被修剪成觀光品牌,城市彷如中了咒──『矮人國的天空毎晚都要下煙花,至少四百年』(P.23)。
要去的地方似乎總找不到,遊記中的地圖不再存在,遊客只好繼續上路,但『目的地』是哪裡?似乎沒人說得上一個確切的地方,只是猶豫不決地重覆地勤人員的話『去自己?』,什麼?哪裡?自己?劇作者阿忠在《創作筆記一》中說:『大部人都表示對“自己”的形象不太清楚,甚至恐懼,而旅程中最大的障礙竟是缺少了“地圖”(沒有方向和目標)與勇氣。這正是面對“自我認同”問題時的焦慮吧?於是,誰在修剪我們心目那棵自我的“怪老樹”呢?是推土機?還是一個患有焦慮症的自己?如果,我們正處於高速成長中的澳門,視作一個正值發育時期的青少年,這裡是否也出現了上述“自我認同”的焦慮?』(P.39)
遊客在枉然的尋找中患上了焦慮症,城市愈發膨大,也患了焦慮症,沒了方向。沒了目的地。“認同”留在陽光愈來愈老的候機室,等待離開。
自我認同:我只是一個『遊客』
『移動』作為這個時代的特質之一,『移動』的提高讓不同地方的人們開始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遊客』——『一樣的裝束,一樣的姿態,一樣忘記了自己的姓名似的,遇人便自稱旅客,或索性自稱觀光博士咖哩骨。』(P.7)
樂於以『遊客』的身分介入一座城市,產生旅客式的印象和感想。一次一次的移動,『遊客』會不會最終無法辨認回家的路?而變成永遠在路上流浪的奧德賽?故事正是由這樣一群『遊客』來敍說的。
然而這些『遊客』的身分很可疑,他們過去可能曾是這裡的居民,但却只承認自己是『遊客』,他們根本忘了,或者不想記起:
『館:你們不是遊客。
A:我們?
B:我們不是遊客是誰?
A:我才不會住在這種地方。
館:你們是本地人,沒理由啊,本地人不會來這裡的。
B:對啊,我是來旅行的……
館:我知道了,你們「現在」是旅客。對了對了,你一定是小時候在這裡住過,然後到了外面生活……』(P.21)
是不想認同或乾脆忘了自己過去的城市?如文本中那個淒涼的預言:『矮人國的子孫毎天日落之前,會有三次認不出自己。』(P.23)認不出、不想認,無法建立認同,城市中了咒。
潛藏在整個文本中的『遊客』,只是一個替代身份──以第三者的身分來掩飾那無法認同的複雜情感。正如到了國外每當被人問到是從哪裡來的?那種不太能直接說出 『澳門』的不自然,尤其在二十年前,或甚至現在。
另一方面,『遊客』也是那個不得已的『自己』,是個人在急速變化的城市中突然轉變的身分,遺收博物館被拆掉,社群記憶隨著不斷變更的地圖和景觀而逐漸被清洗──『這裡每三個月就要換一次地圖。』(P.16)在愈來愈陌生的城市中,發現自己有一天也成了『遊客』,移動在新建街區和填平了的海洋上,無處立足—『咖喱骨彷彿走遍了矮人國,郤又走不出矮人國。毎朝醒來,咖哩骨都以為自己經已離開了矮人國,然而真相卻是矮人國正一步一步地離開,國人每日都彷彿身處異地。』(《咖哩骨遊記》p.17)
劇要終了,人們開始在漫天煙火下逃走,帶着行李向不同方向奔去。
『傻:在這裡表演完,就到另一個地方表演。我們是一個流浪劇團。
館:你是本地人,你不是在流浪。
傻:不,我們在飛機上經過海,經過一個半島,來到這裡。』(P.29)
在貝淡寧和艾維納所合著的《城市的精神》一書中提到,一座城市經過長時間累積演變而形成的生活風貌、所呈現的歷史景觀、當地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觀等,構成了一座城市的精神特質,也是現今城市對抗全球化的一道重要防線,這種城市精神被傳承、被發揚、被嚮往,塑造出在此生活的人們的地方認同和群體歸屬感,也締造出一種無可替代的文化,只有具備這些特質的城市,才能吸引遊客的到來。
然而城市發展中,最不被認清的正好就是這種以『發展』之名來淹埋的城市精神,以及被認為無關重要的社群記憶。矮人國的子民,面對『處處是地標』的發展和改變,望着滿天的煙火繼續流竄,繼續問:『哪有這麼多東西可以代表澳門?』(P.15)他們徘徊在不知要往何方的候機室裡,等待終於有一天,有人說:『你是本地人,你不是在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