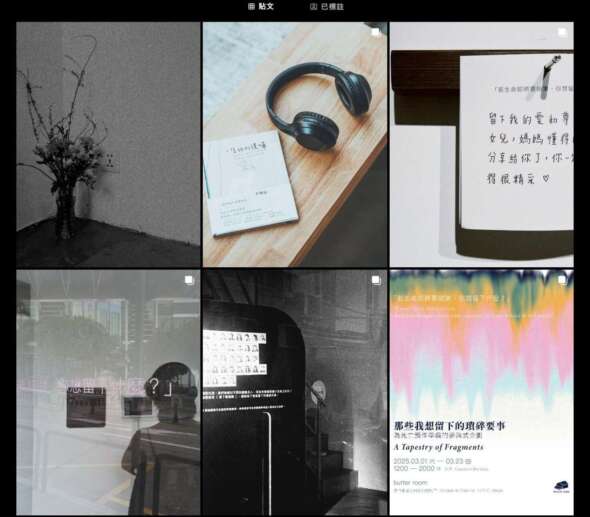來源:Freepik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的那一個周末,正坐在家裡發呆,手機裡卻不停傳來訊息,是網路平台上的自殺消息,一個星期六,我看到的有三單,有朋友看到四單。從那一天到執筆這天十天不到,又陸續看到了幾單。有朋友告訴我,真實發生的更多,很多都沒有媒體報道,如果沒人報料,便沒有人會知道。這個城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連特首賀一誠都在立法會承認「近年居民自殺死亡個案數偏高」,但令人氣忿的是特首竟然說學生遇到感情「小問題」就輕生,沒有一個人所遭遇的困擾應該受到如此輕視,自殺更是極為嚴肅的生命議題。在當下此刻,自殺本應是其中一個極需關注的公共議題,但為何卻似乎甚少在我們的公共領域中被嚴肅談論?更加缺乏對此社會現象的研究和有關論述,無論是探討成因或預防對策,論述相關影響還是自殺者遺族等問題,都甚少成為公共議題,談論氣氛之薄弱,就彷似這裡從來沒有這些問題似的。
據《論盡)》報道,賀一誠認為,本澳自殺個案包括在讀學生及長者,而自殺涉幾方面,或因感情或個人健康。「我哋澳門有很多(自殺個案)係在讀學生,(或因)感情有少少問題」;亦有很多是長者,「佢得咗某種病,佢厭倦」;亦有一部分因為生活壓力自殺。生活太複雜、壓力太大,「生活壓力重,呢個造成好多抑鬱症,很多問題會發生。」
《正報》報道就指,賀一誠所概括本澳自殺三大主因,一是許多是在讀學生因感情遭遇「小問題」就跳樓輕生,二是長者得病厭倦輕生,還有一部分是生活壓力問題。
只談「維特效應」的弊端:扼殺了公眾對自殺議題談論的機會
這個城市有一種論調認為,這種「不談論」是一種善意,因為愈多談論就會愈容易引起關注,就愈容易使社會大眾對自殺行為的模仿,產生所謂的「維特效應」[1](Werther effect)。因此,媒體的報道愈簡單低調愈好。(最近的新聞有時連死者的基本資料也欠奉,如大約年齡、姓氏等,至於所屬學校或職業等就更是敏感資料。)甚至認為自殺新聞愈迅速被人遺忘就愈好,以免會產生「維特效應」。然而,「維特效應」指的是一些不負責任的、帶有渲染色彩的公開報道,並非所有報道或議論皆會帶來負面效應,有另一種稱為「巴巴吉諾效應」[2](The Papageno Effect)的說法,就正好是需要社會有更多公開的對自殺議題的討論,利用媒體的影響力向公眾提供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法,來達到預防自殺的目的。換言之,如果因為一句「維特效應」就使社會對自殺的報道趨向簡化與扁平化,這只是助長了對問題的迴避與掩蓋。
近日香港電影《年少日記》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部電影受到社會大眾的讚賞與關注,電影中也有學童自殺的鏡頭,那是否會因對「維特效應」的擔心就把這些鏡頭刪掉?或者把放映期間所發生的香港學童自殺都歸咎於該電影引發模仿效應?並沒有,反而是因為電影裡真實呈現學童的困境,包括家庭及教育制度的功利與壓迫問題,而引起公眾的共鳴與討論,引起更多的關注,這就是引發了「巴巴吉諾效應」,藉由電影的傳播及公開討論引發了大眾尋找解決問題的積極態度。

香港電影《年少日記》海報
自殺並非單純個體行為
另外還有一種論調認為:自殺是個人問題,不應拿來公開討論。是的,如果有留意媒體對自殺的報道,「個人問題」、「情緒問題」、「感情問題」等似乎便是自殺原因。據悉,本澳警方甚少公佈自殺原因,有時最多提及輕生者有健康問題,似乎只要把嚴肅的生命問題化成「私人問題」,公眾便不應再對別人的隱私有任何置喙,這位自殺者的檔案便可永遠闔上。
的確個人的生活形態是應該受到尊重,個人問題也的確不應被報道,但在信任與尊重的前提下,被聆聽卻是對受創個體一個重要的支持,而自殺也並非只是個人行動和選擇,同時也反映出自殺者所面對的社會問題,連續出現具一定密度自殺行為更是一種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要把社會現象當成事物來研究。」正正就是法國社會學奠基者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這本書中所寫出社會學幾項基本的研究原則中最重要的原則。
涂爾幹所著述的《自殺論》(1897年)是最早從社會學角度來研究自殺成因並分析自殺行為的著作。他首先反對自殺乃先天因素的論調,在研究中提出四種自殺類型:
(一) 利己型(egoistic suicide): 即自我中心型自殺。這是由於社會散漫、群體連結低、以及缺乏社會整合而造成,個人難以與社會融合,無法在群體中被整合。這些個體屬於社會適應困難者,愈是被團體孤立、疏離的人,其在社會中的自殺率就愈高。
( 二)利他型(altruistic suicide):由於社會高度凝聚、教條式地讓人接受社會目標,社會過度整合。自殺者出於高尚的信念,感到有自殺義務而產生的自殺現象,也就是為過度認同與共鳴導致個人之犧牲。例如為宗教信仰或政治忠誠而自殺等,乃為過度認同而導致的個人犧牲。
(三) 脫序型(anemic suicide):即迷亂型自殺,是由於社會失序、崩潰的狀態下而引發個人的失控行為。如社會出現劇烈變遷、經濟蕭條等,或當所依靠的社會規範無法發揮功能時,或因離婚等問題發生,使個體無法以理性的方式處理生活危機時,個體感受虛無而無所適從,無法以理性方式來解決問題。
(四) 宿命型(fatalism suicide):當個體被太多的規律及控制所約束,限制了個體的自由,使個體感到沒有存活的未來,故強烈的社會規範使個人自我抑制過甚的時候。
這四種類型的自殺行為,都與其所身處的社會密切關連。涂爾幹指出,自殺是社會情緒的外顯表現,反映的是社會的狀況,自殺者的精神健康問題可能只是一種顯露方式,要緩解自殺問題,需要的是積極解決社會所積存的問題。
此外,涂爾幹還對於人們曾使用解決自殺的兩種對策——嚴刑峻罰和教育,提出異議。他認為這兩種做法都因為沒有認清自殺的社會性質,所以都將會是徒勞無功的。
涂爾幹從事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多年,他認為,教育只是社會的反映,因此並非預防自殺的最可靠手段,教育基本上複製了社會,而不是創造社會。只有在社會消除各項弊端之後,教育才能得到相應的改變,走向正途。
壓抑和保持緘默只會使傷痛延續
當一些議題被劃上了紅線、建立了禁忌,不再容許在公共領域中被理性討論,或者只劃歸為某類專業人士才能觸碰時,社會的封閉氛圍將使其他受到相似問題困擾的人們更形孤立。當個人對困境感到難以啟齒或進入失語狀態,失去求助的動力,無法接觸問題真實狀況的大眾,則可能會因為無能為力的感覺與日俱增,而對問題變得日漸麻木(想想那些在自殺資訊下的留言),事不關己的情況將可能使人際關係更形疏離、冷漠,這樣的社會是人們樂見的嗎?

茱蒂絲.赫曼教授在她的經典著作《創傷與復原》。(來源:網絡)
美國精神醫學教授、女權運動者、國際心理創傷權威茱蒂絲.赫曼教授在她的經典著作《創傷與復原》[3]中,一起首便把自十九世紀末到當代心理創傷研究的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步步維艱的過程與脈絡寫出來。其中,她指出關鍵的一點是:「要讓創傷的事實得到大眾注意,要有適當的社會背景。」,是否能持續對心理創傷進行有系統的研究,或研究能否得到公開討論,「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
赫曼所專注的創傷研究中有許多是曾遭受性侵、家暴的女性,她提及,正因為過往的社會中「女性生活的真實面貌被隱藏在個人的、隱私的生活領域中。對隱私權的高度重視形成強大的障礙,人們難以覺察真相,女性生活的真實面貌幾不可見」。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婦女解放運動興起,大眾才真正了解到,最普遍的創傷後壓力症患者並不是上戰場的男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女人。」
她認為,要讓受到性侵害與家庭創傷的研究得到社會的認受性,是要當「社會大眾開始體認到女性與兒童地位低落的事實」,大眾願意為婦女權益挺身而出,這樣才能「一起對抗社會上否認和要求噤聲的力量」。否則,這些創傷事件只會「無可避免地被壓制與遺忘所取代」,「壓抑、解離和否認的現象不只存在於社會的意識中,也存在於個人的意識裡。」
赫曼說,對於這些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個體,她們最希望得到的是別人的信任、尊重和不要遺忘。那麼,對於自殺的亡者呢?自殺議題是社會共同面對的創傷,迴避和保持緘默並不會使創傷痊癒,只會使真相繼續被掩蓋。
「她也曾經活過」
通常我得知自殺事件正在發生,是靠朋友在FB群組裡的通知。眾所周知,現在提供資訊最快的並非媒體,而是人們在平台和群組裡的即時報料。每當有人發現哪裡的馬路被封了,或哪裡有人危坐高樓,就會在平台上立即發佈,很多時都有明確位置,甚至有圖片有影片,然後下面必然引來一堆留言,就如圍觀人群的七嘴八舌,但就在死者的縱身一躍之後,這則消息只是一瞬間,就會如同其他網絡上的消息,不論其大小或其嚴重性,很快就會被其他更具刺激性、娛樂性的消息掩蓋過去。
「無聲的血,流淌在冰冷的瀝青上
那鮮紅色是多麼美麗,
哭泣著,哭泣著,
我們在電視顯像管外面
一無所知
⋯⋯
女孩最後流下的眼淚,
是證明她活過的鮮血,
最後卻在短短的兩秒鐘內,
就被陌生的大人清理乾淨了。」[4]
如果自殺是一個人要向周遭發出的最後吶喊,那麼,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想說的是什麼?他想讓人們知道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可以早點知道,那位危坐於高樓之上的人為何走到這一步?他遭遇了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早點知道,即使我們未必能提供實質的幫助,但至少可以給他更多同理與關注,或者就只是真誠的聆聽,告訴他我們明白他的傷痛,或者這樣就可以讓他不用走到這一步?
但一無所知的我們,會有這個機會嗎?
[1] 歌德於1774年發表了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由於小說在當時所造成的轟動,小說主人公維特的結局也掀起了當時年青人的自殺風潮。1974年,社會學家大衛·飛利浦斯(David Philips)將這個自殺模仿的現象命名為「維特效應」,他在〈自殺的影響:「維特效應」的實質和理論意義〉一文中認為,大眾媒體對自殺新聞進行大肆的宣傳報導容易使自殺率有上升趨勢。
[2] 巴巴吉諾為莫扎特歌劇《魔笛》其中一個主要角色Papageno。巴巴吉諾因得不到愛人的心而試圖自殺,在他準備自殺時,另外三個角色現身並提出一些解決他的問題的方法,最後使巴巴吉諾打消了結束生命的念頭。
[3] 創傷與復原(30周年紀念版):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2023)。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左岸文化。
[4] 摘自日本年青創作歌手愛繆(あいみょん)2016年的名曲《她曾經活過啊》,歌曲描寫一名女子的自殺以及社會大眾的冷漠,在自殺問題同樣嚴重的日本社會,尤其年青人之間迅即火熱,大受歡迎,歌曲也被一部描寫人們生活困境的電視劇《只想住在吉祥重寺嗎》起用為主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