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有一群婚後才正式來澳生活的外地配偶,每天嘗試融入社會並照顧家庭。過程中,她╱他們在澳的伴侶及家庭是其最有力的支撐,但若不幸遇上伴侶施暴,一夕間生活便頓失所依。婚後遇家暴的外地配偶,在選擇繼續留在施暴男身邊保家庭「完整」與離開之間掙扎,無論留或走皆兩難。一旦離婚或會影響居留權,無法留澳照顧小孩甚至失去撫養權。來自內地的Min(化名)在婚後遭遇家暴,現時正處在人生交叉點,望最終能有尊嚴地生活。

本澳有不少外地配偶在婚後才到澳生活,需要重新適應社會環境及建立社交網絡。疫情期間更減少了與原居地親友的聯絡。
Min表示,自己這種以探親證居澳的內地妻,最慘下場可能是「一無所有」,「帶侮辱感回到鄉下無法生活,甚至可能會想尋死。」
Min在數年前從廣東嫁到澳門,現在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小朋友。她說,當年是廣東的親友介紹認識先生,在拍拖時也知道伴侶多少有暴力傾向,但未料在婚後第二個月就遭遇家暴。「拍拖時未有疫情及養家壓力,佢未有暴躁一面,而且佢承諾過唔會打女人。一直等到結婚後認為我走唔甩,佢就開始郁手。」
婚後遇暴力及經濟剝削
更怕胎兒營養不良
第一次施暴是在懷孕前,丈夫特意用力打Min的頭,外觀傷痕便不太明顯。當時動手的地點是在街上,「光天化日、無任何先兆。」丈夫打人時表情甚至是「心平氣和」。待Min反應過來,頭部已是又痛又暈,「係一拳鎚落頭頂中間,之後幾個月頭頂、後頸、成個頭都痛。」
「他帶我去睇醫生,一路上仲鬧我,好暴躁,甚至埋怨我為他帶來麻煩。」Min說。
結婚一年後,Min有了小朋友,但因未夠分數申請單程證,未有正式身份,須斷斷續續拿著探親證在澳照顧小朋友,亦無法工作。在懷孕期間,Min所有經濟來源都需靠丈夫,惟經常遭剋扣生活費。
當時Min對本地社會不熟悉,多拿著生活費到超市買凍肉和即食麵,懷胎數月被醫生提醒胎兒有機會營養不良。Min形容,嫁到澳門初期已被丈夫經濟打壓,證件又無法工作,「我無任何錢同機會去街市買餸。」
Min的生活須依賴丈夫一家人,惟丈夫的家人卻對Min被施暴表現得冷漠,毫無意見,甚至冷嘲熱諷,更因小朋友的「現金分享」、「消費卡」、「利是錢」等生矛盾。「佢同媽媽一齊想搶我個仔嘅現金分享,我唔同意。一週內向我家暴三次。」
初時Min是不敢報警的。一來在澳沒有依靠,生活全依賴夫家;二來擔心會影響居留身份。「佢打我,我從來無報警,第一次或第二次我去社工局備案。只有今年才報警。(被打後)關節炎反反覆覆,無法食嘢同戴耳機聽歌或坐巴士(有不舒服),甚至無辦法接受巴士嘅聲音。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佢媽媽都話係我自己身體原因,唔係佢個仔造成。佢媽媽縱容佢行為,細佬關房門當睇唔到。(丈夫)都趁關上房門無人就郁手。」

Min表示,自己決心報警的原因是擔心家暴對孩子的影響。
家庭輔導服務為誰解決問題?
Min認為,當時是自己給了機會,選擇與先生結婚。多年相處自己亦比較清楚先生的情況,嚴重的情緒問題導致先生暴力橫生,「佢無法維持社交功能,會好暴躁同粗魯、固執,影響工作⋯⋯需要個人成長方面、情緒同睡眠方面嘅輔導。」
當Min因家暴向社福機構求助時,她的個案被轉介去社福機構的家庭服務中心,幾年間不斷被「轉嚟轉去」,個案沒被接手,直至去年才正式開始其個人輔導。
她表示,輔導的內容主要是了解期間家中所發生的事、小朋友以及丈夫的狀態,「半個月一次,穩定少少就三個禮拜一次,近期一個月一次。本來準備結案,最近又發生咗家暴。」
她又指,輔導過程中沒有看到丈夫的情緒問題得到處理,即使自己多勤奮去接受輔導亦無法解決問題,問題始終在伴侶身上,而對方無論如何都不會去接受輔導。「需要輔導嘅人係我先生,同佢講都覺得無關痛癢,佢認為佢無問題,係我有問題。」
Min也直言,自己去的機構或其他機構所安排的輔導幫助不大,只看到表面情況。「睇到我心理狀況可能強大過我先生,但好多時都靠我自己去覺醒。」若情況許可,最需要的就是先生的個人輔導及婚姻輔導。若社會機構可安排家訪,觀察一家人如何食一餐飯,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個案的實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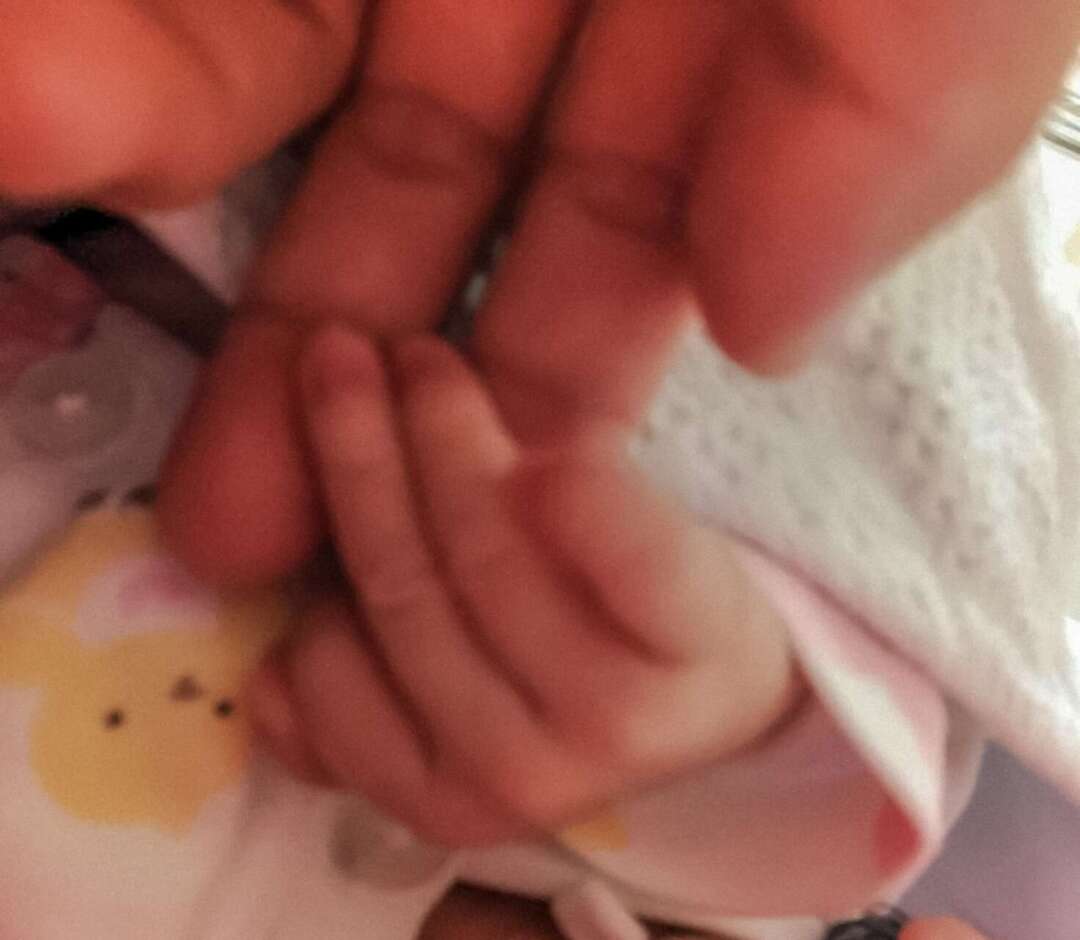
Min表示,如自己這種以探親證居澳的內地妻,最慘下場可能是「一無所有」,「帶侮辱感回到鄉下無法生活,甚至可能會想尋死。」
遇多次家暴終報警需莫大勇氣
對於受家暴傷害的婦女與兒童而言,若想與施暴者分開生活,須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才有可能脫離夢魘。Min曾入住院舍一個多星期,之後就搬回廣東住一段時間,惟當小朋友不在身邊時,她便終日提心吊膽。
事實上,像Min這種內地來澳配偶在本地沒有幾個朋友可支持她╱他們,在疫情期間與內地親友的聯絡亦減少,造成更困難的局面。
最後,讓Min決心報警的原因是擔心家暴對孩子的影響。她表示,丈夫經常在小朋友面前爭吵、動手、威脅自己,自己發覺只有兩歲幾的孩子受嚴重影響,開始有暴力傾向,「小朋友去親街都話要買長刀,話要買嚟殺爸爸,語氣平靜,日常傾計咁。點解?『因為爸爸好大聲鬧媽咪。』我就好驚訝,兩歲幾小朋友講出殺人仲要係爸爸⋯⋯先生嘈交時話要殺咗我,話要返鄉下搞我阿媽之類。在我報警之前,喺電話同當面都有講過,小朋友都在場目睹家暴。」
因擔心長久下去暴力環境會影響小朋友成長,Min終鼓起相當大的勇氣才下定決心報警。然而,無論在報案過程或在思索日後如何走時,她坦言,每走一步都倍感艱難、常浮起放棄的念頭。若因離婚、刑事追責等或會影響自己在澳居留,以後便很難與小朋友一起生活。
雖然《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下稱《家暴法》)出台後,家暴在澳已是公罪,惟Min認為部分警方及社福機構人員對家暴的認識尚有許多不足。
帶著小孩去驗傷
報案奔波、饑寒交迫
她表示,自己今次報警須到司警及治安警處落口供,前後用了近九個小時。警方對身體受傷情況問得很仔細,也有驗傷,但對於丈夫的精神及經濟控制方面的侵害卻不多理會,也明確拒絕聽Min陳述精神方面遭受的虐待。司警亦表示含有暴力語言的微信錄音不可當作證據,只有文字訊息可以。
Min表示,若警方無法理解家暴經歷,而多次通報家暴紀錄一旦無法成為佐證,即使多次通報和舉報也沒有意義。
有關家暴佐證方面,澳門家暴受害人互助會理事長葉濃喜亦提到,許多家暴都在受害人的私領域發生,如房間等場合,若有錄音、錄影證據是未經雙方同意的,這些未經同意採錄的證據能否在庭上當作佐證仍是未知。
Min形容,報案當日簡直是饑寒交迫。從下午五點直至隔日凌晨三點,自己帶著小孩走去醫院驗傷、在司警局及治安警局間奔波落口供,「每一刻都想放棄。」在警方的分工上,重複家暴案件屬司警職責,而單次傷人要找治安警,故需要分別在兩單位單獨落口供至少三小時,面對相當大的身心負荷。
當時Min受了傷感無助,幸得社工學者何穎賢(Ceci)陪同及鼓勵,一同面對及完成繁瑣的報案程序。

內地配偶Min表示,自己與暴力的老公在結婚一年後有了小朋友,但因未夠分數申請單程證,未有正式身份,須斷斷續續拿著探親證在澳照顧小朋友,亦無法工作。在懷孕期間,Min所有經濟來源都需靠丈夫,惟經常遭剋扣生活費。
在澳數年卻未有正式身份
一旦離婚或影響居留權
Min也想過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離婚、離開夫家,但基於身份問題,她很難做這個決定。除了擔心居留,憂慮無法在澳照顧小朋友之外,更很難向夫家爭取贍養費。
現時Min最希望就是陪伴在小朋友身邊見證其成長,若因家暴而離婚、打官司,最後不單有可能導致居留失效,或亦影響爭取親權, 這對她而言便是失去了一切。「揸探親證嚟澳門嘅婦女最慘下場就係付出六年全職照顧小朋友,自己職業同時間耽誤咗六年,最後可能會失去小朋友撫養權同居留權,一無所有,帶侮辱感回到鄉下無法生活,甚至可能會想尋死。」
現時Min仍打算嘗試,陪伴、開解有情緒困擾的丈夫。自她報警後,丈夫亦被要求接受強制輔導。對她而言,離婚是最後不得已的打算。
訪問期間,Min亦多次提及自己在澳多年,惟澳門身份對她似遙不可及。現時她仍尚未夠分數申請單程證,沒有「非永久居民身份」。即使現時不選擇離婚,也要再等七年以上才有機會獲永久身份,期間都有可能繼續受到家暴。
Min希望政府的居留政策可嘗試為遭遇家暴配偶找到調整空間,讓她╱他們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外,亦可有尊嚴地留在澳門生活、工作、照顧小孩。
後記
在早前受訪時,Min剛好帶了小孩回家鄉暫住。事實上,由今年七月起,她與小孩便斷斷續續住在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庇護院舍。期間,丈夫表示掛念小孩,故在友人陪同下她亦曾見過丈夫。她等待已久的單程證有望在未來數個月批出,對之後可能走的路或更清晰。
至於早前報案,Min自己則已「打定輸數」,認為入不了家暴罪,甚至連傷人罪亦未必入到,因那時她並沒有表面傷痕,亦沒有任何跡象呈現其頭部受傷的狀況,而警員亦只是目測她的頭而已。
Ceci表示,最近見過Min及其小孩。在住庇護院舍間,她的孩子因被同一院舍的其他孩子攔阻,急於找正在廚房洗碗的Min而想爬過欄杆,導致下巴受了傷。「她(Min)不會為了自己的事哭,但是她會覺得兒子這樣被人欺負,在院舍被人欺負,然後受傷⋯⋯(她)就會被其他人責備,是她沒有好好看著小朋友。她覺得很難過,所以她在中心哭得很厲害⋯⋯第一次爆哭、六神無主。」
Ceci又表示,若Min能有一個居民身份,即使是非永久,她便就可以找工作,這樣「她的心可能會比較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