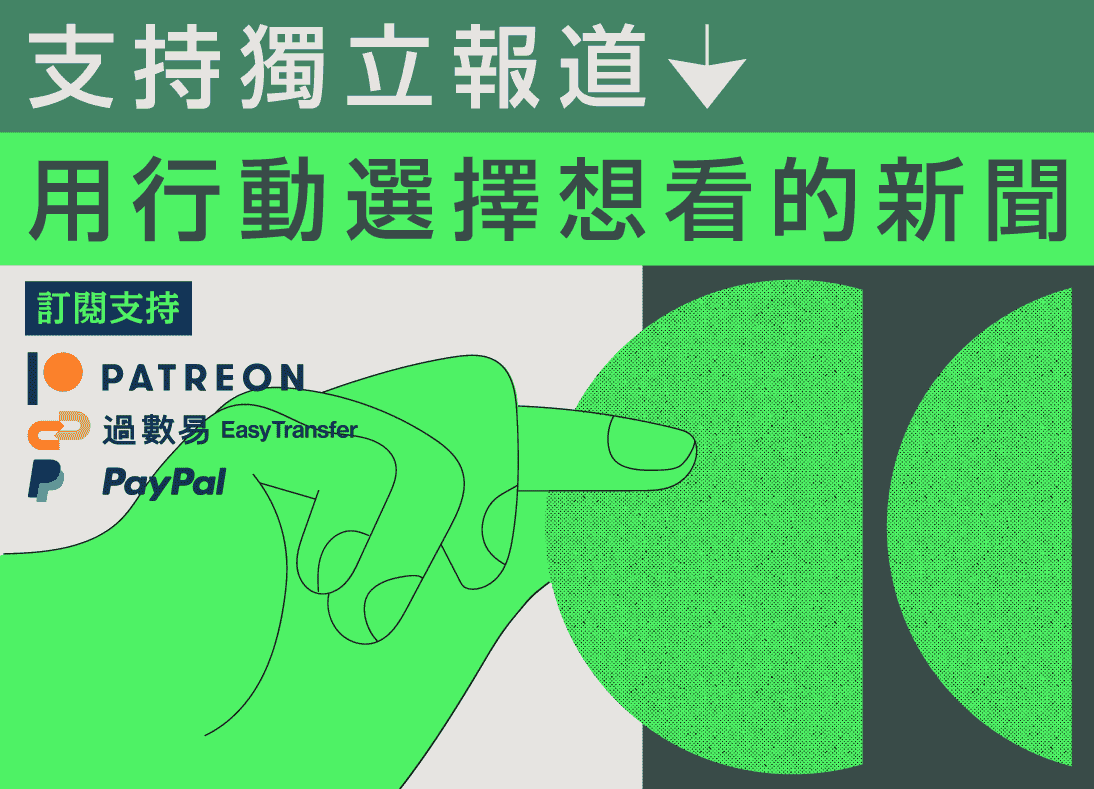在收到你已經離開的消息的當下,我腦海裏泛起了你的聲音,記起你患上癌症之後日漸消瘦的臉容。我沒有半點悲傷,反而鬆一口氣。
或者你並不喜歡被人看見你愈漸虛弱的外表。再想深一層,可能是因為你畢生都在履行記者的職責,活出了無悔的人生,你的精神不滅,你在言談之間所展現的氣度與能量建構出一種龐大的形象,早已植根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作為一名新聞系學生,我在十三年前,抱著好奇的心態,選擇到本澳某報館擔任實習記者。在大學的課堂當中,我大抵對澳門新聞機構的親政府程度,有一種初步的印象,不過這種印象很快被兩個月的實習期扭轉了,亦為我曾待在這一行十年注入一支強心針。
當時政府擬就俗稱「公職法援」法案立法,引起社會不滿。我在某次到立法會小組會進行採訪工作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你,你就在「散會」的時候,竭力向列席會議的時任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提出一堆尖銳的問題。

華生:在以往十年的報館生涯中,每日回到公司,回到枱頭都會先看到這張不知是哪位前輩放置的舊照片。亦即是說,我每日寫稿,都會先看到你,原來這就是每次同你飲啡時你所提到的,回歸前的日子,當中綻放著永遠說不完的故事。
回想起那時代的官員,好像比較好勝,亦比較不畏懼在鏡頭面前與記者理論。那一次,你與陳司唇槍舌劍近三十分鐘,這對當時未習慣長時間提起錄音筆及相機的我,除了感到疲倦以外,亦感到耳目一新。
當時我領會到,原來在前線記者當中,也有一群熱愛發問,竭力對不公義之事向政權提出提問的人。至於記者的報道,編輯如何刪減,那是另一個層面的事了。
你熱愛爭辯,每一次提問都中氣十足,或者有人會認為你的發問過於冗長,但我認為這種講求前文後理的提問風格,往往能讓每個人都知道甚麼才是具有良好公民質素的思路與想法,這正是你的感染力的來源。每一次與你一同採訪,你都沒有因為受訪者左閃右避而失去耐性及理智,並時刻對答案保持警惕。
在往後工作的日子裏,我還記得,如果在早上碰到你,你會習慣用手機瞪大眼睛檢視那些已經出街的報道,鉅細無遺地確認被刪減的一字一句。
我已經忘記在立法會等候小組會「散會」的時候,渡過了多少青春。而每當有你出現,你都會樂於請我們這些後輩喝咖啡,分享以前的採訪經歷,以及澳門曾經發生的人和事,並了解我們的想法。最重要的一點是,你從來不以前輩的身份自居。
你所分享的故事的核心,永遠都在追憶和感嘆澳門過渡期至回歸初期,新聞採訪環境的寬鬆和自由,即便採訪總督、葡萄牙總統的時候的採訪安排亦如是。
幾年前,我們在立法會巧遇正在訪澳的前澳督李安道將軍,你就立即上前拍照,之後駕輕就熟地,像見到老朋友一樣與他進行了簡短的訪問,當時你臉上露出的笑容,至今我仍無法忘懷。
記者十年生涯一晃而過,離開了這一行接近一年後,你請我到「金船餅屋」飲咖啡,邀請我加入《論盡》一同工作。這段期間,經常聽說你要打針、診療、食藥,你的臉色愈發蒼白,經常說痛,但你仍堅持每月在例會當中出現。對社會政策上可能潛藏的危機,你仍然熱度不減,及時地在通訊群組中,從不錄音地用文字寫下你的看法,儘管大家都希望你減少看手機,避免頭暈眼花。

編按:二〇一八年前澳督李安道來澳時的受訪情景。小毅有次分享那次採訪時說:「李安度總督,當年在葡參加鮮花革命的少壯軍人,民主革命成功後到澳門做總督。二〇一八年,李安度重訪澳門,到立法會參觀。我本來只是拍幾張相,但突然間覺得要做訪問。好彩,嗰陣時立法會工作人員沒有趕走我哋。(打擾主席與貴賓)我記得,訪問有問到澳門當年沒能民主化的話題。記者,隨時隨地扑咪」她就是這樣的敬業樂業。
今年三月的一個凌晨,我收到你的「急call」,我以為發生了甚麼大事,原來你只是叫我在早上到一個癌症病人分享會進行採訪。我在記憶之中,很少直接收到你的電話。
到達現場,病魔纏身的你,發問比我還要多。你一直在讚嘆你的主治醫生的仁心仁術,同時亦非常關注癌症病人康復的心路歷程,不忘將這些生命正向的訊息,通過報道分享給大眾。
採訪完成後,你請我喝了最後一杯咖啡。十幾年來,我們很少單獨吃飯,今次飯局當中,你終於不談澳督、特首,你談到一九九三年「灣仔之虎」陳耀興在澳門被槍殺的事件,記者到達現場並拍攝到血腥照片的經過,其實你也很清楚我的專長以及感興趣的話題。
收到今次寫稿的邀請,原本的主題是關於你曾與我們分享的採訪故事及經歷。相信不少人對你談澳門回歸前後的故事都十分感興趣,但每當他們向你提出將這些口述經歷蒐集成書,或者就此向你提出採訪要求的時候,你又會說「自己只係聽返嚟」而一再婉拒。
你盡記者的天職,畢生以近乎拒絕老去的姿態走在新聞前線,行事風範人所共知,但另一方面又永遠保持低調地默默做事。
你經常採訪他人,自己卻不愛成為受訪者。我在學習傳統新聞理論的時候常常謹記:記者應避免成為新聞主角。你的離去,亦意味著過去一代傳統報人的功架與典範漸漸消失,成為了我們的追憶。
小毅,你的離去對我而言,永遠都是感謝及追憶,遠多於傷感。如同在你的追思會上,你哥哥說「你的精神沒有離去」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