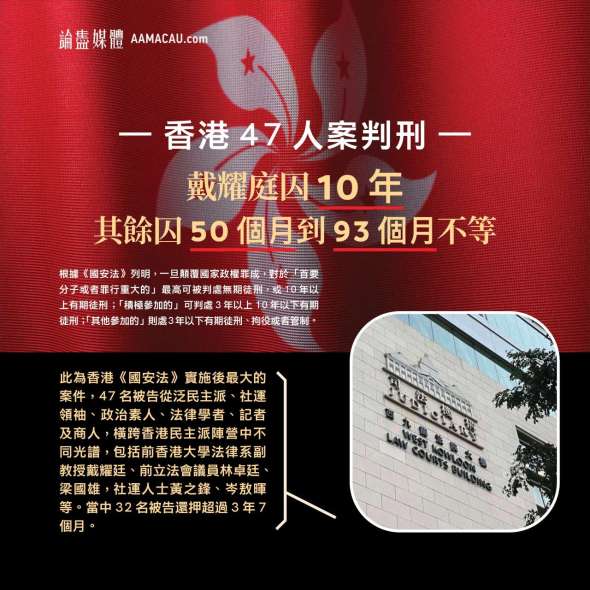8月11日的晚上,我與朋友在燈光明亮的食店中,不敢相信手機顯示出來的新聞,不敢打開那些滿是鮮血的視頻。平行時空的另一端,是明目張膽的暴力:地鐵裡放催淚彈,走在街上突然被打、被捕,地鐵裡突然被推下電梯、被開槍掃射,許多人頭破血流,有個女孩重傷至殘……就算示威,就算衝突,他們只是平民、學生,並非罪大惡極的殺人犯,更沒有精銳武器作反擊,何況現場還有許多無辜市民,何以至此?!到底這個政權有多害怕和憎恨手無寸鐵的人民,才可以做得出這種殘暴的行為?!
8月11日的晚上,是顛覆人類文明想像的一夜。我們自以為生活在一個文明、先進、發達、物質豐裕、人身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但原來一切都可瞬間灰飛煙滅,歷史大倒退隨時發生:指使黑社會打人砍人、喬裝示威者、插贓嫁禍、濫打濫捕、攻擊醫護、記者、近距離開槍、爆頭、爆眼⋯⋯這不是太平盛世的罪行,我們在戰時的德國嗎?還是非洲的盧旺達?抑或80年代的南韓?我們活在歷史的車輪裡,不斷周而復始,文明會極速衰落,只因一些人永遠拒絕進化。極權獨裁國家才有的殘暴鎮壓,為的是以恐懼管治和操控人民,而製造恐懼的人,本身就是活在恐懼中的人。
當敵人如此野蠻和巨大,惶恐與無助籠罩了城市,留下給人們的只有憤怒和眼淚,不,也不是只有這些。
我想起同是關於恐怖攻擊的一部電影《我的巴黎舅舅》,幾個畫面一直留在腦海裡。
David快速完成工作,踩著單車前往巴黎東邊的Bois de Vincennes,準備會合姐姐及朋友一同野餐,慶祝姐姐考獲車牌。這是一個愉悅的黃昏,城郊四下無人,清爽的風吹得樹木沙沙作響,空氣中彷彿飄著花香,David的臉上掩不住笑意,也許還哼著歌。他騎著車像飛行般滑過馬路,經過那些莊嚴不語的雕塑群,一切是如此美好,就如尋常生活裡的每一天。忽然有些重型機車肆虐般高速掠過他的身旁,叫囂且張狂,他感覺事態不尋常,但又說不出什麼,好像害怕也說不上,只是惘惘中有種威脅⋯⋯電影在這裡突然無聲,一種莫名的寒意滲透全身。
接下來的畫面是刻意的抽離。在悲劇發生的現場,被無差別襲擊的人們驚恐、哭泣、大叫都是拿掉了聲音的緩慢動作,從傷者身上湧出的鮮血配合著草地和燦爛的黃昏,像一幅中世紀描述受難者的油畫,動作都被定格在災難的刻度上,人們那錐心之痛,就是一種永恆。
人對無法相信的災難突然降臨。本能地都想逃離,有時意識上會產生強烈的抽離,感覺自己只是一個旁觀者,彷彿一切都不是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心理學上稱此為「情緒解離」,是身體自行產生的情緒防衛機制,像一種臨時的鎮痛劑。
恐襲發生後的第二天,David和Amanda與整個巴黎一同「解離」了。他們漫無目的地到處走著,與受傷的巴黎一樣無語。公園門外有重裝備警察在把守,勸喻他們離去──「今天不宜去公園」。他們不知要到哪裡去,他們更不知道的是:原來好好的生活哪裡去了?媽媽哪裡去了?
教堂依然,廣場依然,鴿子依然,塞納河依然;他們坐在欄上眺望遠處,卻什麼也沒有看到。很多事情好像仍是那樣,但卻又不可能一樣了。
當David和Amanda的意識突然回來,察覺世界的殘暴和悲傷早已無可挽回。此刻,他們的淚流下來,但他們的意志,也更為堅定。他們與巴黎市民一樣,不願輸給恐懼和傷痛。
法國人權鬥士和外交官、〈世界人權宣言〉起草人之一史蒂芬・黑塞爾說:「恐怖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發洩憤怒的形式,然而這是一種負面的思考,應該要懷抱希望,而不要憤恨。」
人們照樣上街、工作、照料傷患,甚至回到出事的公園,以回復日常來對抗暴力,對抗命運的不公。儘管悲傷仍會不時湧現,努力仍會被痛楚瓦解,憤怒和失望都搞和了,有時會分不清彼此,但巴黎人仍要尋回希望,尋回愛的能力,「不任由仇恨滋長」。電影裡人們不願屈服在傷痛中的部份,很平常,很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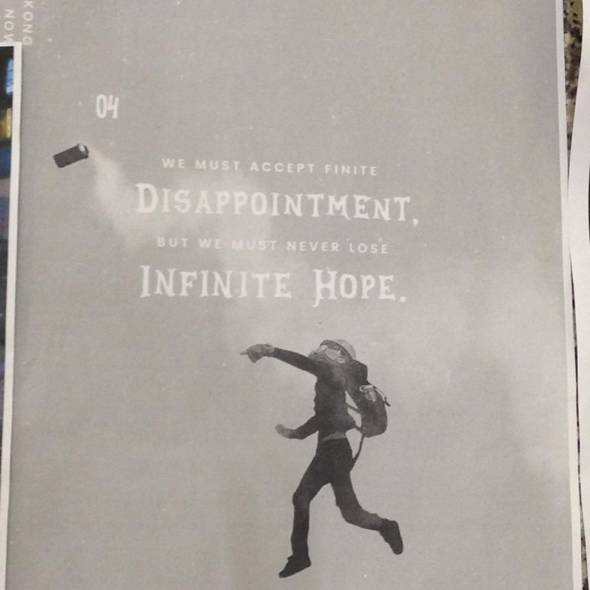
當然香港現在的情況,比起突然降臨的恐襲還要可怖,那是統治者的強權和暴政,步步進迫,連續不斷的惡意攻擊!
好多個無法平靜的黑夜,看著強權一次又一次,做出超越道德底線的事情,現實陷入黑白顛倒的瘋狂之中,迫使人們憤怒;憤怒,才有可能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黑塞爾在他那本著名的小書《憤怒吧!》中,如此頌揚憤怒:
「憤怒是抵抗運動的基礎。抵抗就是拒絕接受羞辱,就是追求道義上的合法性,而不是法律上的合法性。」
他還說:
「創造即是抵抗,抵抗即是創造。」
在這次運動中,香港年青人的創意、堅定和勇氣,還有高尚的公民素質(相比起對手的下三濫招數),都為這句名言提供了最好的示範,使世人看到一種全新的抵抗運動模式。
黑夜也許漫長,好好保存憤怒的力量,不要讓悲傷、恐懼把生活奪走,不要任由期待、想像、希望和美好的事情被遺忘,不能認輸,被傷痛和失望支配,要收復失地,回到日常生活中,繼續滋養力量,讓信念生生不息。
每天醒來,跟自己說,你還活著,這就是你最大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