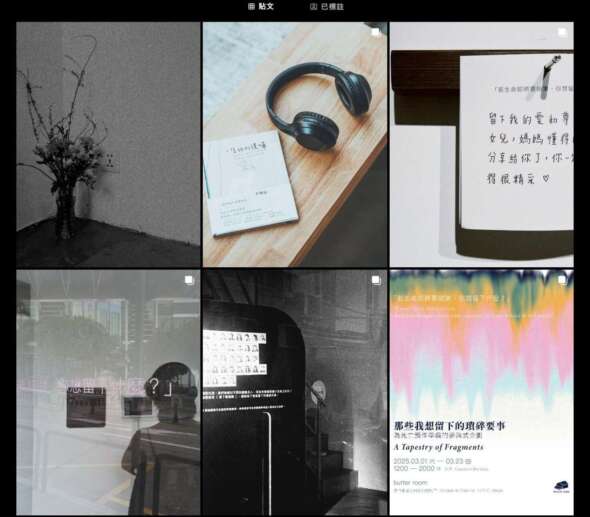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慾望孤荒》劇照(相片由文化局提供)
這些情景不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嗎?
看似寧靜的黑夜裡,常常被突然提高分貝的聲音插入:失控的歌聲、誇張的笑聲、或一句超大聲的髒話;憤怒的咆哮,分不清男女的撕扯、扭揑,時高時低;無法停止的小孩哭聲、打罵,然後更放聲的喊叫;還有靜寂中突然的巨響──「嘭」,似乎是一個很重很重的東西從高空掉下,跌在四樓停車場的鐵篷上,那種聲量,使人禁不住懷疑是一個電視或是什麼……女兒小時候常被這種聲音嚇到,她總會充滿疑慮地看著我,我們會一起猜想──到底是什麼掉下去了?漸漸地,我們已習慣了這種不知來自哪一樓層哪一時空的聲響,那些哭泣、吵架、打鬧、心碎、醉酒及其它……不過是正常生活的正常部份。這些充滿畫面但又讓人不想追究太多細節的聲音,早已充盈四周,多在黑夜,也在白天。直到那一次。
大約下午四時多,又有一聲十分巨大的「嘭」,我是在家工作的人,白天也會聽到這些來歷不明的聲音,本來不太在意。但那一聲有點不尋常,不知為何令人很在意。到了傍晚,我在家中樓下看到幾個司警在管理處查問什麼,但網上看不到任何相關的新聞。到晚上十一點多,我忍不住打聽了,原來下午四時多,有一個人在我們所住樓層的上方跳樓自殺,我聽到的,應是他/她在世上發出的最後聲音。但,僅此而已,一個聲音,一個死者,沒有新聞價值的平常人。即使有個簡短的新聞,但其實什麼內容也沒有。就這樣,一個生命結束了,而我對他/她一無所知。我們住在相同的大廈,可能在面對相似的生存壓力,可能經歷同樣的傷心失望,可能也一樣喜歡某些食物,某些歌曲。但我只聽到他/她發出的最後一個聲音。

《慾望孤荒》劇照(相片由文化局提供)

《慾望孤荒》劇照(相片由文化局提供)
不知為何在看《慾望孤荒》時,我想起了這個從高處墜下的鄰居。發生在舞台上每一個人身上的事情,都像填充了那些日常聲音背後的畫面。
《慾望孤荒》所呈現的是對身體的肆虐和殘酷,演員自虐式的力量令人不忍卒睹,那種力量是來自現實的地獄,也是來自內心焦灼的憤怒和孤寂。在一個訪問中,編舞者之一的Gabriela Carrizo說她的作品常來自現實的延伸,舞台上的角色都是現實處境中的真實人物,他們在社會上有各自的背景和經歷,從他們的衣著行為便可以辨識出來:大肚的妓女、自凟的筋肉人、聲如洪鐘的瘋婦、乞求佔有的妻子、分裂的丈夫、憧憬愛的無家者等……他們可能都是我的(你的)鄰居,或者同路人。喜歡自電影中尋找啟發的編舞者,把舞台也設計得像一個電影場景,甚至加入一些電影特效於其中,會令人想到某些經典場面,但又一閃而過,留下懸念,到底舞台與電影是兩種不同的敍事媒介,身體語言的抽象特質與敍事的邏輯,交織出一種脫離常規、荒誕跳躍的表現形式。
舞者們的處境互相交叠,有時分不清誰是誰,他們在命運面前喪失身份,卑躬屈膝,他們求援無望,陷入絕望的深淵。舞者把身體無限的扭曲、變異,直接傳遞痛感的演出方式,使人想起過往慣於以「奇觀」吸引大眾的傳統表演,一如馬戲團所慣用的手法,不論人或動物,不正常身體才值得被注意,他們源源不斷地為觀眾提供扭曲的殘酷快感。然而,偷窺者舞團在做的是剝開表皮的工作,而我們,成為旁觀他人痛苦一個多小時的觀眾,成了名符其實的偷窺者。但,與坐在馬戲團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快感,只有痛感。痛得冷漠,痛得無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