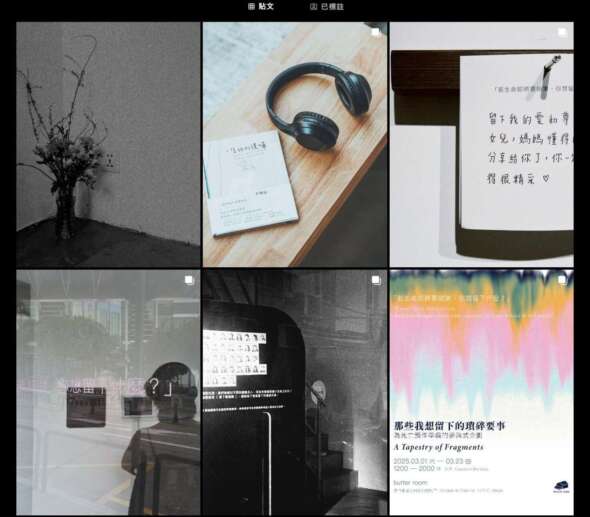ж”қеҪұж©ҹгҖҒеҫ®дҝЎгҖҒFacebookгҖҒиөҙеҸ°е°ұеӯёгҖӮ
и‘ЎеңӢиҸңдҪңзӮәйҒҠе®ўзҫҺйЈҹгҖҒиҢ¶йӨҗе»ідҪңзӮәжң¬еңҹзҫҺйЈҹгҖӮ
и‘Ўиҗ„зүҷеңӢж——иүІзҡ„йӣһе•„зұігҖҒж“ҚеҢ—дә¬еҸЈйҹізҡ„йҒҠе®ўгҖҒеЎ«дёҚеҮәзұҚиІ«зҡ„жҫій–Җдәәпјӣз…©жӮ¶зҡ„дёҠзҸӯж—Ҹе’ҢеҸӘжғіжә–жҷӮж”ҫе·Ҙзҡ„жё…жҪ”еҘіе·ҘпјӣдҪҚж–је…Ёзҗғз”ҹз”ўз·ҡжңҖеә•еұӨзҡ„з”ҹз”ўе·ҘдәәиҲ…иҲ…пјҢжңүйҢўеҲ°еҸҜд»ҘеңЁйҒҠиүҮз”ҹжҙ»еӣӣе№ҙзҡ„е§ЁеӘҪпјҢгҖҢеӨҫеңЁе…©иҖ…дёӯзҡ„жҫій–ҖдәәгҖҚгҖӮ
и«ҮеҸҠиә«д»ҪжңҖи®“дәәе°·е°¬зҡ„пјҢеҫҖеҫҖжҳҜ當жҲ‘еҖ‘и«–иҝ°гҖҢжҲ‘еҖ‘жҳҜиӘ°гҖҚзҡ„жҷӮеҖҷпјҢеҜҰйҡӣдёҠпјҢжҲ‘еҖ‘еӨ§еӨҡеңЁи«Үи«–зҡ„пјҢеҚ»жҳҜгҖҢд»ҖйәјдёҚжҳҜжҲ‘еҖ‘гҖҚгҖӮ
гҖҢйӣ¶и·қйӣўеҗҲдҪңзӨҫгҖҚж–јеҸ°еҢ—гҖҢзүҜе¶әиЎ—е°ҸеҠҮе ҙгҖҚдёҠжј”зҡ„еҸ°зҒЈзүҲгҖҠеҪјжҷӮжӯӨеІёгҖӢпјҢд»ҘдёҖеҗҚиөҙеҸ°е°ұеӯёзҡ„жҫій–ҖдәәзӮәдё»и»ёпјҢиІ«з©ҝе…ЁеҠҮд»ҘгҖҢдёҖдәәдёҖж•…дәӢгҖҚзӮәзҙ жқҗпјҢз·Ёз№”иҖҢжҲҗзҡ„ж•ҳдәӢжһ¶ж§ӢгҖӮе„ҳз®Ўжң¬еҠҮзҡ„з·Ёе°ҺжүӢжі•зӮәдёҖдәәеҲҶйЈҫеӨҡи§’гҖҒеӨҡз·ҡзҷјеұ•гҖҒзўҺзүҮеҢ–еҸҠжү“з ҙи§Җжј”з•Ңз·ҡпјҢдәәзү©гҖҒең°й»һгҖҒиӯ°йЎҢдёҚж–·иҪү移пјҢж•ҙзҗҶиө·дҫҶпјҢеҚ»дёҚйӣЈзҷјзҸҫжң¬еҠҮзҡ„й—ңйҚөи©һеҸҘпјҢд»ҘеҸҠйҖҷдәӣе…ғзҙ зҡ„йҖЈжҺҘй—ңдҝӮпјҡ
дёҖгҖҒжҫій–ҖдәәеҲ°еҸ°зҒЈжұӮеӯёеҫҢпјҢпјҲеңЁFacebookдёҠпјүеҚҒеҲҶй—ңеҝғеҸ°зҒЈзҡ„жҷӮдәӢпјҢеӣһеҲ°жҫій–ҖеҚ»ж„ҹеҲ°иҮӘе·ұиҲҮпјҲе……ж»ҝйҒҠе®ўгҖҒе·ҘдҪңиӢҰжӮ¶зҡ„пјүеҹҺеёӮж јж јдёҚе…ҘпјҢиҰҒеЎ«зұҚиІ«жҷӮеҸҲеЎ«дёҚеҮәдёҖеҖӢеҸҜи®“д»–ж»ҝж„Ҹзҡ„зӯ”жЎҲпјҢжңӣеҗ‘йӮЈеҖӢпјҲжј”е“ЎжҘөеҠӣеҘ”и·‘гҖҒйЈҪеҸ—жү“ж“ҠгҖҒй•·и·Ҝжј«жј«д№ҹиҰҒз”іи«Ӣеұ…з•ҷзҡ„пјүеҸ°зҒЈпјҢж·ұж„ҹз–‘жғ‘еҘ№жңүд»ҖйәјзҗҶз”ұпјҢзӮәеҸ°зҒЈзҡ„ж–°иҒһж·ҡжөҒж»ҝиҮүпјҢеҸҲжҲ–пјҢеҗ‘йҒҠе®ўи§ЈйҮӢжҫій–Җзҡ„йЈҹзү©е…¶еҜҰжІ’йӮЈйәјйӣЈеҗғгҖӮж–јжҳҜжј”е“Ўзҷје•ҸпјҢжҲ‘жҳҜиӘ°пјҹжҫій–ҖжҳҜд»ҖйәјпјҹжҲ‘жҳҜжҫій–Җдәәе—Һпјҹ
дәҢгҖҒй–Ӣе ҙдҫҝе®Је‘Ҡзҡ„е®ҝе‘Ҫи«–пјҡгҖҢжҲ‘еҖ‘жҳҜдёҖеҸ°ж”қеҪұж©ҹпјҢдҪ дёҚиғҪжұәе®ҡиў«жһ¶еңЁд»ҖйәјдҪҚзҪ®гҖӮгҖҚж–јжҳҜжңүиә«еңЁзҸ дёүи§’ең°еҚҖпјҢ當зүӣд»”иӨІжҙ—ж°ҙжҠҖе·Ҙзҡ„иҲ…иҲ…пјҢе’Ңе«ҒдәҶжңүйҢўдәәпјҢжңүйҢўеҲ°еҸҜд»ҘеңЁйҒҠиүҮдҪҸеӣӣе№ҙзҡ„е§ЁеӘҪпјӣиӢҰжӮ¶дҪҶжҳҜе№ҙиј•гҖҒе……ж»ҝеёҢжңӣзҡ„зӨҫжңғж–°й®®дәәпјҢиҲҮжҜҸеӨ©еҸӘжңҹеҫ…дёҠзҸӯдёӢзҸӯй ҳи–Әж°ҙзҡ„жё…жҪ”е·ҘгҖӮд»–еҖ‘иў«е®ҡзҫ©зӮәеҪјжӯӨдёҚиғҪзҗҶи§ЈпјҢдәҰеҰӮдёҖеҸ°ж”қеҪұиҲ¬еӨұеҺ»д»»дҪ•иғҪеӢ•жҖ§е’ҢиҮӘжҲ‘ж„ҸиӯҳпјҢдёҖеҰӮжј”е“Ўе•ҸгҖҢеҗҢжҳҜз”ҹиҖҢзӮәдәәпјҢзӮәд»ҖйәјдәәиҲҮдәәд№Ӣй–“зҡ„йҡӣйҒҮеҸҜд»Ҙзӣёе·®еҰӮжӯӨзҡ„йҒ пјҹгҖҚеҫҢпјҢз”ұиҺ«зҫӨиҺҠйЈҫжј”зҡ„е·ҘдәәеҸӘе–ҠдёҖеҸҘгҖҢйӮҠиӯҳе‘ўе•ІйҮҺе•ҠпјҒгҖҚпјҲеӨ§ж„ҸпјҡйҖҷдәӣжқұиҘҝпјҢжҲ‘е“ӘжҮӮе•ҠпјҢдёҠзҸӯе°ұжҳҜеҰӮжӯӨпјү然еҫҢз№јзәҢе·ҘдҪңгҖӮеүҚиҖ…зҡ„иә«д»ҪеҚұж©ҹпјҢжҳҜеҖҹз”ұе°ҚжҜ”еҸ°зҒЈгҖҒеҸҠе°ҚеҸ°зҒЈзҡ„й—ңеҝғиҖҢдҫҶпјҢж–јжӯӨпјҢйҖҷеҖӢеҫһ經жҝҹйҡҺзҙҡе…ҘжүӢзҡ„гҖҢжҫій–ҖдәәгҖҚпјҢиў«жһ¶иЁӯеңЁжҘөеәҰеҜҢжңүиҲҮиІ§зӘ®д№Ӣй–“пјҢжј”е“ЎиӘӘжҫій–ҖдәәгҖҢе°ұеңЁд»–еҖ‘е…©иҖ…д№Ӣй–“гҖҚпјҲе…ҲдёҚи«–йҖҷеҖӢж”ҫзҪ®жҳҜеҗҰеҸҜиЎҢжҲ–йҒ©еҗҲпјүпјҢе…©еҖӢе•ҸйЎҢгҖҒеҸҠе®ғеҖ‘жүҖи©Ұең–жҸҗе•Ҹзҡ„жҫій–Җдәәиә«д»ҪеҚұж©ҹд»Қ然зӣёдјјпјҡжҲ‘дёҚжҳҜд»–еҖ‘пјҢжҲ‘дёҚжҳҜд»–еҖ‘пјҢйӮЈйәјжҲ‘еҖ‘жҳҜд»ҖйәјгҖӮ
гҖҠеҪјжҷӮжӯӨеІёгҖӢжүҖж§Ӣе»әзҡ„пјҢжҳҜдёҖеҖӢиҮӘжҲ‘йӮҠз·ЈгҖҒдёҚж–·жҺ’йҷӨзҡ„жҫій–Җдәәиә«д»ҪгҖӮйҖҷзЁ®йӮҠз·ЈиҲҮж–ҮеҢ–и©•и«–дәәжқҺеұ•йө¬жӣҫиҝ°зҡ„дёҚеҗҢпјҢе·®еҲҘжҳҜйҖҷеҖӢгҖҢиә«д»Ҫзҡ„жЁЎзіҠгҖҒиӘҚеҗҢзҡ„з©әзҷҪиҲҮж–ҮеҢ–зҡ„ж··йӣңгҖҚдёҰдёҚеё¶жңүгҖҢе……ж»ҝеүөйҖ жҖ§зҡ„еҠӣйҮҸгҖҚпјҲиЁ»1пјүгҖӮеӣһжӯёжӯӨеҠҮпјҢе…¶з«Ӣе ҙжӣҙеӮҫеҗ‘жҠҠеҸ°зҒЈдәәгҖҒдёӯеңӢе’Ңжҫій–ҖдәәпјҢ當дҪңжҳҜдёҖйғЁе…Ёз„¶иў«еӢ•зҡ„ж”қеҪұж©ҹпјҢеҰӮжһңдәәжІ’жңүеүөйҖ гҖҒйЎӣиҰҶжҲ–ж“ҙй—Ҡиә«д»ҪжЁҷзұӨзҡ„иғҪеҠӣпјҢжҲ‘еҖ‘дҫҝеӨұеҺ»дәҶд»Ҙе®ЈзЁұгҖҢжҲ‘жҳҜжҫій–ҖдәәгҖҚдҫҶж“ҙй—Ҡжҫій–Җдәәиә«д»Ҫзҡ„дё»е°Һз«Ӣе ҙпјҢиӘ°зҹҘйҒ“е‘ўпјҢдҪ з”ҡиҮіеҸҜд»ҘиӘӘгҖҢжҲ‘жңүйҖҷеҖӢз–‘жғ‘пјҢжүҖд»ҘжҲ‘жҳҜжҫій–ҖдәәгҖҚпјҢдёҚжҳҜе—ҺпјҹжҸӣеҸҘи©ұиӘӘпјҢжӯӨжҲІзҡ„е…¶дёӯдёҖеҖӢе•ҸйЎҢе°ұжҳҜпјҢеҰӮжһңеҺ»е•ҸгҖҢжҲ‘жҳҜжҫій–Җдәәе—ҺпјҹгҖҚзҡ„йҖҷеҖӢдәәпјҢдёҰдёҚе…·жңүиғҪеӢ•жҖ§пјҢеҸӘд»»з”ұз’°еўғе’ҢеңӢж—Ҹж”ҝж¬ҠдҫҶз•Ңе®ҡзҡ„и©ұпјҢйӮЈйәјпјҢйҖҷжҲІзҡ„жүҖжңүжҺўз©¶пјҢе°ұиЁ»е®ҡжҳҜеҫ’еӢһз„ЎеҠҹзҡ„пјҢйҖҷдәӣеңӢзұҚе’Ңиә«д»ҪпјҢд№ҹеҸӘжҳҜдёҖеҖӢжӢҝеҮәиӯ·з…§дҫҶзңӢзңӢе°ұеҸҜи§Јжұәзҡ„дәӢжғ…гҖӮ
жӯӨеӨ–пјҢиҰҒеҺ»жҺўз©¶жҫій–Җдәәзҡ„иә«д»ҪеҚұж©ҹпјҢеҸҰдёҖеҖӢжӣҙе®№жҳ“иҗҪе…Ҙзҡ„йҷ·йҳұжҳҜпјҢ當жҲ‘еҖ‘дёҚж–·жҺ’йҷӨд»ҖйәјдёҚжҳҜжҫій–ҖжҷӮпјҢе…¶еҜҰпјҢдәҰжҳҜжӯЈеңЁжҡ—зӨәдёҖеҖӢжӯЈзўәзҡ„жҫій–Җдәәиә«д»ҪпјҢдҪҶйҖҷеҖӢжӯЈзўәзҡ„жҫій–Җдәәиә«д»ҪпјҢзңҹзҡ„еӯҳеңЁе—ҺпјҢд»ҘеҸҠпјҢзӮәдәҶжӣҙеҘҪзҡ„зӨҫжңғпјҢйҖҷеҖӢжЁҷзұӨжңүеҝ…иҰҒеӯҳеңЁе—ҺпјҹйҖҸйҒҺжҺ’йҷӨпјҢеҺ»зўәиӘҚиҮӘе·ұзҡ„жҫій–Җдәәиә«д»ҪпјҢе…¶еҜҰеҚҒеҲҶз„Ўжғ…е’ҢеҚұйҡӘгҖӮ
ж–јжҳҜпјҢ當演員иӘӘеҮәпјҡгҖҢеҰӮжһңжҫій–ҖжҳҜдёҖеҖӢдәәзҡ„и©ұпјҢд»–иӮҜе®ҡ已經зІҫзҘһеҲҶиЈӮгҖҚжҷӮпјҢдёҚе…Қи®“дәәйҢҜж„•пјҢе’Ңе°·е°¬гҖӮеӣ зӮәжҫій–Җзңҹзҡ„дёҚжҳҜдёҖеҖӢдәәпјҢйҖҷиЈЎжңүеҫҲеӨҡдәәпјҢжң¬е°ұдёҚеҸҜиғҪеҸӘж“ҒжңүдёҖзЁ®жҖ§жғ…гҖҒең°дҪҚе’Ңиә«д»ҪгҖӮеҗҢиӯүпјҢжҲІдёӯеҮәзҸҫзҡ„еҸ°зҒЈе’ҢдёӯеңӢеҪўиұЎпјҢд№ҹдёҚе…ҚиҗҪе…ҘдёҖе…ғгҖҒзүҮйқўзҡ„иӘӨи§ЈгҖӮ
е…¶еҜҰпјҢй–ӢйҰ–йҷіеҲ—зҡ„зЁ®зЁ®е…ғзҙ пјҢдёҰдёҚзүҙи§ёгҖӮеҚідҪҝеңЁзҸҫеҜҰдёӯпјҢжҲ‘еҖ‘д»Қ然йңҖиҰҒең°еҹҹиә«д»ҪпјҢе®ғд№ҹдёҚи©ІжҳҜжҺ’йҷӨзҡ„е·Ҙе…·гҖӮеҰӮжһңеҸҚе…¶йҒ“иҖҢиЎҢпјҢжҲ‘еҖ‘еҺ»ж“ҒжҠұжӣҙеӨҡзҡ„еғ№еҖјпјҢж“ҙй—ҠгҖҢжҫій–ҖдәәгҖҚзҡ„иә«д»ҪжғіеғҸпјҢе–ңжӯЎзҡ„и©ұпјҢйЎҳж„Ҹзҡ„и©ұпјҢдҪ еҸҜд»ҘжҳҜжҫій–ҖдәәпјҢд№ҹеҸҜд»ҘжҳҜеҸ°зҒЈдәәпјҢдҪ еҸҜд»Ҙд»ҖйәјйғҪжҳҜгҖӮз”ҡиҮіпјҢдҪ д№ҹеҸҜд»Ҙд»ҖйәјйғҪдёҚжҳҜпјҢдҪҶдёҚйҳІзӨҷдҪ еҺ»еҒҡд»»дҪ•дәӢжғ…пјҢеӣ зӮәжҲ‘еҖ‘дёҚйңҖиҰҒеӣ зӮәжҫій–Җдәәзҡ„иә«д»ҪдҫҶи®“жҲ‘еҖ‘пјҲеҸӘпјүй—ңеҝғжҫій–ҖпјҢйҖҷжЁЈиұҲдёҚжҳҜжӣҙиҮӘз”ұгҖҒжӣҙзҫҺеҘҪе—Һпјҹ
иЁ»1пјҡеҸғиҖғжқҺеұ•йө¬зҡ„гҖҠи¶Ҡз©әзҷҪпјҢи¶ҠжңүеҸҜиғҪжҖ§в”Җв”Җжҫій–Җдәәзҡ„иә«д»ҪиӘҚеҗҢиҲҮжӯёеұ¬гҖӢпјҢhttp://mypaper.pchome.com.tw/chinpang/post/1320258022гҖӮ
жј”еҮәпјҡйӣ¶и·қйӣўеҗҲдҪңзӨҫ
жҷӮй–“пјҡ2017/07/22 19:30
ең°й»һпјҡзүҜе¶әиЎ—е°ҸеҠҮе ҙ2жЁ“и—қж–Үз©әй–“
дёӢдёҖзҜҮж–Үз« пјҡжҷәж…§еҹҺеёӮгҖҒзҡ„еЈ«гҖҒж°‘з”ҹгҖҖйҒёиҲүи«–еЈҮ第дёүе ҙгҖҖеҗ„зө„жҠ’е·ұиҰ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