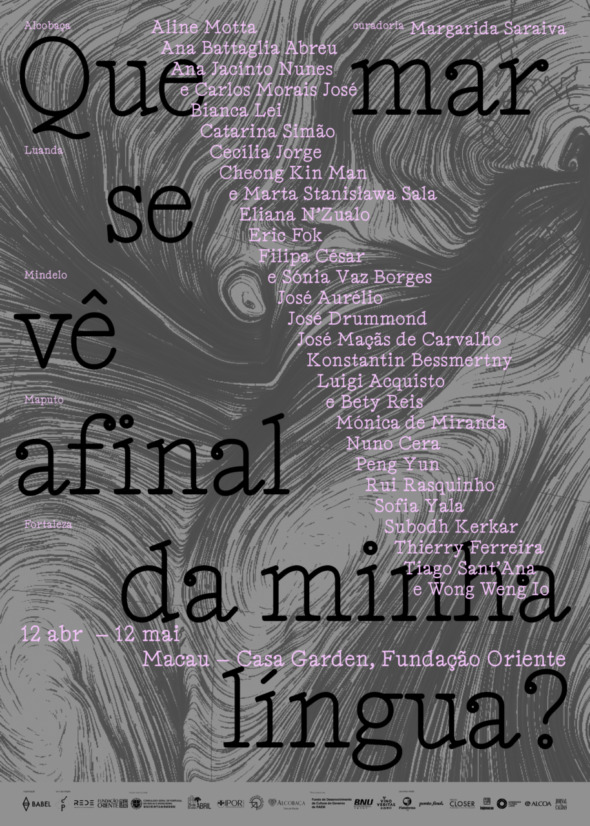「保留建築物對於下一代,能給他們什麼嗎?我看不到這樣做會有更好的福祉。」早在這城市舉辦被戲稱為「盂蘭盛會」的武林群英會之前,掌管城市文化命脈的最高部門負責人曾這麼說過。此時此刻,我們被教育成對每年燒錢的紙紮景色視而不見、強化城市及文化發展視而不見、對硬生生照亮暗巷老街的探射燈視而不見、高官亂花錢對法律制度視而不見、抱怨着招不到的士卻對交通問題視而不見;慢慢我們的影子消失在城市中,一聲令下政權有辦法令黑夜不再,白日永恆耀眼,因為我們都太渺小太卑微,我們對於我們視而不見。
推動的不只是經濟,還有人巨大的私慾。
倘若,城市辦節慶活動,對這被經濟主導的城市年代,是必需的。可是,從美學到經濟、從舖天蓋地的宣傳到在地體會,我完全感覺不到政府的野心。在大灑金錢之餘,怎樣能挽回市民缺乏參與的那份自卑感,提高經濟又不影響生活?我看不到這個可能性——一個都看不到。全球所有城市都在比國際化,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我懷疑長期受世界忽視的自尊心,在這一刻全部引爆,但每每瞻仰到的是一堆破銅爛鐵,憑空製造出來一堆次等貨。
城中人對所謂旅遊項目百感交集,我們用文化做口號,用古典美學作為後盾,卻用小孩般的身軀招搖於市,令城市由生變死,且不論有沒有帶動觀光,整個城市的美學更讓人擔憂。
然,什麼叫城市的美,美的本身,有什麼目的。
都市的美從來不是一棟建築或一個布景可以代表,是整個城市的藍圖、是日常生活、是整個城市有沒有照顧到口中所說的大部份人,然後還有被犧牲了的那些什麼,得的總和,是為藝術。我們的生活就是一種藝術,那個讓生活在裏面的人能記得這城市的方法。如果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那麼,城市美學是習慣的藝術。有人的地方才能有藝術存在,社區就是藝術得以發揮的場所。沒有人,公園再美輪美渙,也是廢墟;沒有人,花了多少錢的藝術造景就如森林中的枯葉沒有兩樣。藝術在社區就是無處不在,無論是文物、文化、生活或社區,都是人去賜予她生命。現在的空間愛講「打造」,幾乎是製造封閉空間的等義詞,再在空間的邊緣鑲一圈金箔,人湧入空間得到短暫的微醺後,依然是帶不進他們的生活。
思想家莊子早在二千年前,就寫下了他對社會的觀察。美人西施患心痛病,日夜皺著眉頭、按着心口,同活在一條村的其他醜女子看到,以為西施的美是來自這姿態,也學着西施皺眉的樣子,以為這樣就是漂亮,結果鄰人們看到醜女子覺得更可厭可憎,效果適得其反。
節慶很熱鬧,不如公園實在;空間打造再狂野,不過是另一座無情的大廈,肉眼中這開放的空間有幅看不見巨大的牆,牆的最上方下著飄然的細雨,籠罩著我們生活的街頭。
美學、社區和記憶,三個密不可分的名詞,其中隨便一項被摧殘,其他的不要打算可以獨善其身——那個叫「愛都」的廢墟,以前是這城市第一家賭場;據說這山上以前有守備軍,雖然城牆如預言一樣消失了;這河畔很美好,這排房子住的是原居民,但我不認得現在住在裡面的小吃部員工和展覽館守衛;那個超乎同代人能想像的建築,是我們的城,當年人人都以為這地方永遠不落。
我來不及看繁花盛放,但總能在記憶中找到這座城市輝煌的畫面,這座古城在百年前就懂得自創美感,現代人自愧不如,卻又無一承用原有的美感;把古地圖打開,這裏是世界的門戶,當時多少要到中國朝聖的外國史節、文化學士,都會先到澳門學習中華文化,先呼吸中西融合的空氣,免得水土不服;也絲毫不用去擔心美感,曾經所有美學和工藝都是世界最新,擁抱著純粹的生活,所有的工藝不費吹灰落在眼前⋯⋯那時沒有文化局、都市更新,更沒有「光輝五年」,現在身後的布景,需由我們自己去想像。
我們不信預言,我們也活在嘲笑聲中。
每個人,都是在上班時日夜策劃放假離家出走的大計,由旅行變成了逃難,無一想留戀活着的城,由一個遊人變成了旅行難民,回家後,娛樂結束後,幸褔的想像瞬間蒸發,空虛的心靈不好意思再討論我們的城市。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一書中說過,地獄就是我們各自身處的城市,考驗我們怎麼在這地獄存活,方式有二:一是成為它的一部分,緊緊地依附著地獄,當幸福的傻瓜;另一個方法是找出不是地獄的美好事物,保持她們的美好,「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後者深知這城市的極壞,明白終究沒法阻止城市的改變,一如我們只想築起一道牆,去阻擋地獄的過來。
實際上,在美學面前,要先談公義。美學和藝術不得不變得神聖,因為他的公眾參與都被人為操控所隔開,同時變得好昂貴。你可以詛咒這城市到處都醜、控訴活動經費浪費金錢、某個造景花得不值得⋯⋯由群體控制的社會被個體所決定,永遠只會落得如此淒涼,你的控訴只是一群面目糢糊的人在自怨,政權最後還是被大眾消化,甚至被原諒,這就是問題所在。程序沒有公義,就永遠沒有美的城市,沒有人能計劃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談何美感。現在的控制者目的不為什麼文化,他們只是看到舊了就翻新、老了該拆、指令下來就按下開關罷了;然而我們也未必是善良,嘲笑聲沒有停止,有事就倒頭大睡,信奉睡一覺萬事能辦好的流行哲學,有想法的又不作為,全城人都要負責,你你我們全部是幫兇。沉默、無知不是洗脫的理由,伊底帕斯在不知情下犯下淪理大罪,即使拯救了整座城,最後還是決定自挖雙眼、自我放逐。我們不可能是伊底帕斯,眼睛也不那麼雪亮,想看穿這個城市前,記住,政權征服不了你破冰的決心,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得失,重點是整件事背後的發生、的敗懷。
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一個有份促成多項百年建築倒下的文化高官見記者說,「我也是個文物愛好者」,令我想起英國現代小說家毛姆在民國初年到中國旅行,和當時一個中國部長官員談話,眼看這部長在他面前聲淚俱下地訴說現在中國多無能、多腐敗、自己的心有多痛,但他知道這個部長就是一個爛人、惡棍,口中說一套,實際是會把所有擋路的人剷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把中國淪落到他所悲嘆的這個地步,他本人也難辭其咎」。
歷史,歷史啊,沒有任何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