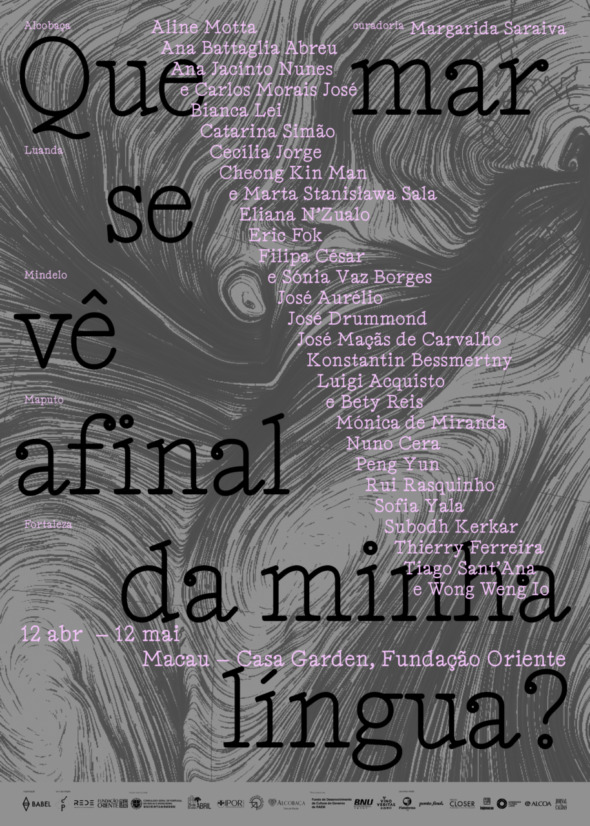嬉鬧聲劃破寧靜的夜、霓虹燈下搖搖晃晃走出幾個醉漢、滿臉通紅的臉上泛著油光和猥褻的笑容。早上是衣冠楚楚的體面人物,晚上卻來這裡享受平日根本不敢宣諸於口的下流玩意…
就是這一個簡潔有力的故事浮現在我腦海裡,宣判了愛都的死亡:愛都必須被毀滅,如二戰後的納粹符號和伊斯蘭國的異教圖騰般,化作灰化作霧化作空氣。
原因,是因為它下流。
這怎麼可能。我走遍大街小巷,卻找不到另一個答案。教堂、廟宇、大宅、然後又是教堂、廟宇和更多的大宅,難道古代的澳門人除了祈禱、敲經唸佛和憂國憂民之外都沒在幹別的事嗎?我依稀記得,檔案室裡塵封的磚頭史書裡,每一頁都是海盜、妓女、賭徒、癮君子和奴隸,現在他們卻如空氣般蒸發在澳門的地表之上,彷彿教堂的鐘不曾為海盜的入侵而敲響,彷彿奴隸的血不曾染紅澳門的海港。99%的澳門史太微不足道也太下流,唯有那最好的1%值得留下。
現在回想起來,文物保育自古就是上流人的玩意。聽說最早可往上追溯到二千七百年前的古希臘。當時的貴族們為向死老百姓證明自己的權力與生俱來,不容挑戰,製造大量家族神話,「兩百年前有隻怪獸經常跑來攻擊村民,全靠我阿爺個阿爺殺死佢,你班老百姓先有今日。」為了更好地證明這些神話,他們挖出長埋泥土下的無名古墳,宣稱這些就是自己祖先的墓穴,要求百姓前來供奉。於是荒廢了的墳墓被「活化」為公共朝聖地點。
然而古物保育為上流人而生也為上流人而死。古希臘貴族爆發內戰時,總不忘搗毀對方家族的墓穴,以消滅對方在這片土地上的權力基礎。在新古典主義氛圍下掌權的阿馬勒總督不可能不熟知這樣的象徵力量。因此當他把澳門人的先祖撒骨揚灰時,目的並不只是為了理順那條貫穿澳門南北的發展主義之路,也同樣是為了把阻擋這條路的(他眼中的)落後迷信和雜亂無章一併掃除;因此他並不滿足於趕走清朝官員,而是要搗毀他的稅關;不滿足於結束清朝在澳門的治權,而是要打碎那塊能證明清朝治權的石碑。在他身後卻又是一系列葡萄牙民族主義的歷史紀念物,賈梅士洞的石像,得勝花園的紀念碑。你看,有些過去是該保留的,有些過去是該被抹去的,由誰去決定?都由上流人去決定。 p>
p>
阿馬勒的時代畢竟是過去了。然而若說上流人和上流人的世界觀確實不再那麼決定性地影響澳門保育的內容的話,這種世界觀的壟斷性仍然深刻反映在保育的方向、討論和詮釋之上,特別是反映在一系列直接繼承從古希臘墳墓到賈梅士石洞的英雄崇拜之上:「葉挺」的故居、「孫中山」的藥局、「鄭觀應」的大屋、「林則徐」的官廟。這種對文物的詮釋呼應的是上流人對自己與世界的期許。突顯那些虔敬、富裕、憂國憂民、樂善好施的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而非平民百姓的市井生活。從這樣的脈絡去瞭解,就會瞭解為何禁煙民族英雄林則徐能擁有一座如此突兀的博物館,而鴉片屋卻遭到冷落;就會瞭解為何鄭家大屋的修復被定調為某民族先知的大宅,而非定格在那個「七十二家房客」的卑微時代;就會瞭解為什麼我們只看到愛都是上流人的下流玩意,卻看不到它是下流人辛勤勞動的工作場所。也許,作為下流人的我們要問的是,如果服務業的血與汗與淚不值得後世紀念那在澳門甚麼才值得紀念?如果剝削和侮辱的痕跡無法警惕我們的子孫那歷史又有甚麼意義?
別忘了澳門原本是一塊光禿禿的石頭,為了生存而周旋在帝國之間,從事著各種令人厭惡的卑微勞動。而正是從這位替鴉片裝箱的工人和那位替奴隸船服務的水手身上澳門一點一滴地為下一代搾出一座座的教堂、廟宇和大宅,下流的勞動與上流的夢於是匯聚於狹小的半島上,密不可分地相生相剋,形成了豐富而複雜的文化內涵。這樣的文明奇跡不只不比「中西文化交融」來得遜色,而且比後者更深刻地銘刻在我們的個人經驗上,至今仍是我們喜樂與焦慮的源頭。然而,我們卻不願意給它一座如此卑微的紀念碑。
唉,為甚麼不能承認城市如我們每個人般總面臨著道德掙扎,既有卑三下四的時刻又永遠無法割捨對道德和夢想的追求呢?澳門以歷史城區申報世遺這個事實,應提醒我們保育工作並不只針對一磚一瓦的保護並把它們切割成單一、空洞、靜態的英雄敍事。重點是如何還原城市裡裡外外數百年間堆積起來的對話和互動,因為正是這樣的過程成就了今天的我們;正是在澳門數百年奮力不被時代潮浪所淹沒的掙扎過程中,卑微的澳門人莊嚴地宣告了人類壯麗的生命力,並以此擠身在世界諸文明之列。
這樣我們自然需要一座歌頌下流人的紀念碑,去紀念這樣一個海港奇跡:即使是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們就是能夠在光禿禿的石頭上開出一片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