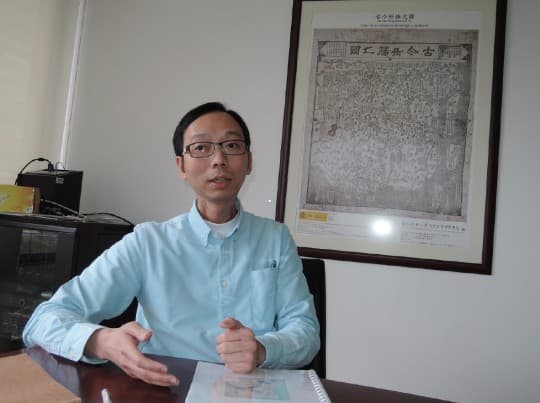2005年,澳門成功申報世界遺產;自此,澳門的名號上增添一項「世遺城市」。十年以來,大家對世遺城區的景觀以至屬於澳門昔日的一磚一瓦,珍愛有加。但世遺建築留下了,是否代表已被成功保護﹖怎樣才是克盡保護世遺的責任﹖今期《論盡》專題邀請了四位歷史文化界別的嘉賓,分享他們的看法。
申遺成功以來文化保育的綜述和反省
本澳申遺成功已屆十個年頭,同時亦是文化遺產的維護遭到前所未有挑戰的十年。政府文化部門在世遺保育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很明顯處於防範、回應式的保護上,遠遠不足以應付澳門社會經濟急速發展時期,文化遺產面臨的危機。在十年前的澳門世遺申報書中,澳門特區政府強調將提交文化遺產管理計劃,保證在歷史建築群及其緩衝區內的任何城市發展計劃,將依照世界文化遺產及建築指引的規條進行管理,並透過立法創造更能保護文化遺產的環境。但是,幾乎是在十年後,澳門才通過了文遺法,而具體的歷史城區管理計劃則仍在諮詢中。
十年來,尤其頭五年是文遺保育的高度爭議期,從下環街市重建計劃、藍屋仔爭議、東望洋燈塔景觀危機、功德林重建計劃、拆卸望廈兵營、主教山景觀問題以及高園街公務員宿舍等等項目,無不引起民間社會高度關注。每一次的文遺危機,幾乎都是由建制外的社區運動和公民抗命的方式,喚起公眾對城市生活空間、文化遺產保育的關注,尤其不同的專業人士和文化遺產保育人士,以新興的網絡工具連結以及創意的公共發聲形式,使澳門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保育傳統。
因此,在最近的五年中,歷史城區的保育爭議雖未杜絕,仍有零星的個案,例如西灣湖夜市事件、下環均益炮竹廠、渡船街一號等,但主戰場已經轉移到新口岸和離島等新區的超高樓爭議中。那麼,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是否可以鬆口氣,尤其是歷史城區的保存就可不需關顧呢?這裡涉及一個文化保育的基本價值拷問,即世遺或歷史城區對澳門人的意義是甚麼?從這個提問入手,我們認為十年來的保育思路有值得反省的地方,無論官方或民間。
要反省澳門十年來的文化保育思路,我們必需回答「歷史城區對澳門人的意義是甚麼?」這個提問。在這裡,引入人類學、地理學以至進步的城市規劃師在空間分析中所關注的「地方(place)」這個概念,加以討論。在最近的社會空間理論中,地方概念經常與特殊性及情感依附聯繫在一起,通常關乎社會關係、歷史連結、身分認同等。在澳門的例子中,不一定是指標性的歷史建築才值得保存,地方指涉的可以是消失了的桃花崗、社區小店。
相對於地方,有兩個概念值得對比,「地景/景觀(landscape)」和「非地方(non-place)」。在理論上,對比地景與地方,前者的主體者通常以旁觀者身分居於場外,注重視覺效果;而後者的主體者一般身處之內、生活在其中。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當一個城市將自己定位為觀光客凝視的對象,地方與地景的差別就不是那麼容易區分。這也是為甚麼十年來澳門民間的文化保育運動,有很大的比例關注城市景觀的問題。而亦有論者敏感地察覺到政府在這方面的傾向,例如《論盡》在2014年底組織的討論官方《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文本」專題中,有文章指出:「諮詢文本」中整體概念仍以「視覺體現」為主,有如從旅遊車或旅遊宣傳片中走馬看花的平面印象。文本中為保護「歷史城區」的街道及開敞空間風貌而加以控制的範圍,亦只有一些屬於視覺元素的街道設施、周邊建築物及廣告招牌等,而且尤其重視「廣告招牌之安裝」。可見,無論民間或官方,似乎更著重景觀的保護,而不是作為生活空間、方式的地方保育。
如果將「地方」和「非地方」的概念來對比,我們更可看出澳門世遺保育的局限。「非地方」在學理上被界定為「人們不必一起生活即可共存或同居的空間」,因而非地方具有一種無歸屬感、無歷史性、短暫感知經驗的特質。由於當代消費主義遊客與貨物迅速流動,現實中存在大量的「非地方」,例如交通的轉接點、商業中心、主題樂園、博物館、連鎖式大型酒店等越來越常見,侵蝕作為生活空間的地方。非地方是一種地方的負面特質,一種地方自身的缺席,停留其中的是消費者而不是公民,不再需要長期的記憶、也沒有責任作出任何承諾或認同。而有趣的是,曾有本地社團精英呼籲將歷史城區打造為主題樂園,也有文化主事者推動澳門成為露天的博物館,正是將地方轉為非地方的例子。但是,在《論盡》同一專題中,另一位作者清醒地質問:總覺得在「澳門歷史城區」,跟在威記的大運河購物中心一樣,在被歷史、西式建築美化包裝的購物街中行走。到底這裡是為旅客而設的「歷史」購物街,還是屬於居民們的文化遺產?
回首初衷,澳門社會當初殷切期盼歷史城區列入世遺名錄,只是為了擁有一張謀取財富的金色名片嗎?顯然不是,特區政府在澳門世遺申報書中強調:高樓大廈已經淹沒了具有相同歷史與建築風格的許多其他東方城市,澳門保存歷史與文化的成果就顯得難能可貴!並承諾「建築群方面注重周圍環境的配合,盡量保持原來的氛圍」。可見,申遺的意義應該在於:保存這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記憶以至原來的生活氛圍。
小城不應建高樓
同是一樣的建築,留下與否,申遺前後大家的態度不一。對於這現象,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有以下的見解:「澳葡年代是殖民統治,再好也不是自己的,但回歸後社會的公共資源是全體澳門居民享有。」而申遺成功後的宣傳,亦讓澳門人對每天擦身而過的建築有更多認識。「當知道這些是重要的文化遺產,自己的子孫後代都可享受,是澳門人的榮譽,責任感也就提升了。」
上升的,還有樓宇的高度。當年,澳葡政府把歐洲保護文物的理念原則帶到澳門,先後訂立多條法令,保護本地歷史建築。法令自八九十年代開始生效,沿用多年,一直相安無事。唯千禧年後賭權開放,城市發展急速,令法律的保護效力一再被挑戰,亦令世遺城區景觀受到破壞。「澳門不應該再建超高樓,二十層也不行。不只令世遺景觀受破壞,也令整個生態環境受影響。」陳樹榮一再強調,超高樓是文化遺產保護的「殺手」,「現在望向大三巴,一幢幢高樓像一支支箭般佇立,破壞了整個天際線。小城長期形成的一種高雅別緻休閒氣氛就如此被破壞了。」
「工務部門都不知怎樣想的。依照法規﹖但沒責任維護文物嗎﹖」陳樹榮歎道。
一方面痛心,一方面也喜見近年民間文物保護意識有所提升。陳樹榮期望,政府官員亦不斷學習關於文物保護的知識,好好保護澳門世遺景觀。「特別是工務局,有好多圖則會否破壞文物就看工務局是否批准,所以政府官員要不斷學習關於文物保護的知識,提升這方面的自覺性。文化局當然也是責無旁貸。」
修補問題的核心
身為建築師的呂澤強,接受訪問時提出了一個較少受社會大眾關注的觀點:維修。「申遺十年,政府有關部門的保護可說做得很足夠──我指的是世遺城區的二十多個建築物。政府定期去維修翻新,不過專業技術上我覺得還有進步空間,現時缺乏了一些有系統的事前研究、維修的方法論證等。」
世遺建築不少已建成逾百年,加上部分屬磚木結構,容易漏水,甚至惹來白蟻蟲患等。呂澤強表示,據他觀察,有關部門一直沿用以往的模式,由自己的技術員去決定維修方案,有時會聘請外來專家或顧問公司意見,但某些方法卻是「治標不治本」,「例如教堂經常出現一油漆剝落。剛回歸時,見有這情況便定期修補。但為甚麼教堂會有這個問題呢﹖其實是地下水的問題。」
呂澤強進一步解釋:「以我知道近年開始在一些建築物的牆腳底部打針去防水。這是一個方法,但以我在法國所學,這方法未解決到另一些問題。例如倘若真的有地下水,而我們只在牆腳防水,水會積聚在建築物的地基,反而走不了。這情況有點像病人發燒,醫生不斷開退燒藥,但不知道發燒的原因,反而耽誤了治病時機。」
其他的還包括措施的專業論證,如該措施對建築物的影響等等。這些都是一門專業,並非一般建築師都可勝任。「所以我說維修技術上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跟專業有關。要一步步去評估、觀察、再決定下一步行動,再調節。措施是否可以逆轉很重要。因為有些措施做了就無可挽回,是對建築物造成永久傷害。」
重視維修,是因為世遺建築只此一座,無可複製。其歷史價值亦使澳門城區有別於主題公園式的景點。「主題公園最主要的目的是帶來經濟利益,但文化遺產還包含了很多,例如文化認同,令這個城市的人知道自己的過去,從而去知道城市未來的發展。我認為這些非常重要,不只是吸引遊客這麼簡單。」
了解是種責任
「申報文化遺產成功意味着這些古蹟,不單純對澳門人重要,是對全人類重要。澳門在這情況下就不只能簡單地看旅遊價值,而是有一個責任,好好保存,讓之後的人類都知道。」訪問剛開始,澳門文物大使協會會長廖嘉豪便扼要道出當年申遺成功的意義。
澳門文物大使協會成立於2004年,比澳門世亦申報成功還要早一年。成員都是一班年輕人,成立以來一直努力向本地人及背包遊客推廣澳門歷史文化,近年在大三巴牌坊、盧家大屋等世遺景點亦有提供駐站講解,宣揚澳門世遺特色。自申遺成功後,保育事件一浪接一浪,更曾有人憂慮澳門世遺會被除名,廖嘉豪認為十年下來,大家的保育關注度比以往更高,是好的發展。「現在人們不只關注度,知識層面亦有所提高,有更多人更了解法例、城規、了解世遺的概念。」而這顯示出申遺對澳門人的影響之大,亦顯示出保護不單是贊成與否的表態,還需要知識的研究。「最大的責任是了解事情的本質是甚麼。任何事你要去保護前,你先要尊重他,尊重前你先要了解他,然後你會懂得跟她共處。」
「表態一句很容易,而了解是種責任。」廖嘉豪總結道。
文化保育也是人心保育
2005年,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2014年,澳門文遺法正式生效,澳門文化遺產委員會亦隨之成立,為政府提供意見。十年以來,社會曾於各個保育事件中反覆爭論;十年過去,林發欽認為,政府的保育力度不斷加強,反應更迅速,而本地保育亦在不斷轉型。「隨着社會和城市經濟的關係變化、訴求的改變,保育去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其中一點很明顯,我們很高興的是,保育已由少數文化精英的倡導,轉型到公民自覺參與。」
民間參與度日高,希望自己的聲音能被重視,亦期盼文遺會的成立能讓政府兼聽各方意見,包括民間聲音。身兼澳門文化遺產委員會的林發欽坦承,委員會是一個諮詢組織,沒具體權限,僅可提供意見,但某些工作如能做得更好,委員就能做得更多。「例如現時諮詢組織的議程都由行政當局提出,但如委員也可提議程,就能關注民間更多。政府傾向發佈這階段我做了甚麼,或透過委員會向你解釋施政面對的阻礙,但對宏觀的保育規劃,我們是比較欠缺。文遺法生效超過一年,當中許多補充性行政法規和清單需要處理。今天有部分已去到諮詢會,但未有具體一一落實。現時大家較關心的是建築文物清單的增補,但文遺法還有很多清單,如非物質文化遺產、古樹名木等等,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面對社會急速發展,林發欽認為下一個十年,澳門要思考的是澳門人的感情與文化的關係。「將來很重要的是一個人心的保育。過去十年的都市化、現代化、全球化,澳門面對這些變動中,我們在文化上是焦慮的,在人文傳統上是失落的。信仰衝擊使我們人心虛怯,所以這不只是技術上保育,而是要從我們社會上的人心角度,去使居民覺得無論經濟怎樣發展,澳門人的精神,核心的傳統是不變的,澳門人的精神會繼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