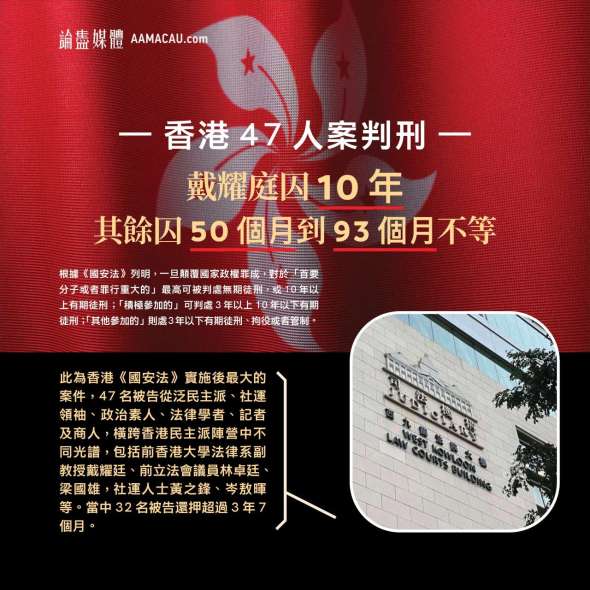沒有窗口,空氣混濁。任裝扮得再時尚、再漂亮,劏房依然劏房,也難逃活在盒子裡的命運。一幢幢密不透風的高樓,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爭着衝破誰會在意的天際線。在職貧困,文憑多張,也不算甚麼。綠意盎然的植物,早已無暇欣賞;冰冷的水泥鋼筋,早已融為一體。在赤裸裸的生活空間,只但求一床寄夢。寸金尺土,石屎危城,蝸居難求。這,就是如今的香港。
困於狹小局促居所,總有一天把人迫瘋。垂直向上的築居方式,早已給洋人淘汰。現代主義風格,不近人情,注定了美國「住宿運動」失敗。1955年,日裔美藉設計師山崎實,試圖安罝2,800戶窮人,設計了Pruitt-Igoe公屋──33幢建築,密密麻麻,每幢高11層,廚房空間超小,電梯隔層開,一半居民須走樓梯,兩層共用的長長樓道,卻方便了罪犯,搶劫住戶。垃圾遍地,滿牆塗鴉,犯罪猖獗,無人願意入住。1972年,於居民一片呼聲中倒下,被說為「現代建築之死」。有人歸根究底,指出貧民窟「像監獄一樣冰冷無情」,與詩意棲居,相去甚遠。高度集中、簡約、洗練現代風格,過度追求功能主義,乃敗筆關鍵。自此,人們不得不反思生活空間和生存意義兩者間關係。匪夷所思,如今香港,乃至澳門,沒從歷史中學習,把人推向另一極致的悲哀。
城市病了。年青公民,看不見家的末來,每天掙扎於糊口邊緣,衣食住行,全方位任由既得利益者魚肉,要麼劏房,要麼背上一輩子的債,淪為現代極權資本主義下奴隸。月入萬四或以下,就是次等公民,別妄圖安居樂業,更遑論生小孩。名校是直資的,沒錢就不用想,一代比一代絕望。一切失衡,皆因欠缺了一公平的競爭環境,機制往往只維護權貴。因此,大家不得不停一停,拿出勇氣,從每天例行公事中走出來,在被標籤極具爭議的公共空間中,表達那埋沒已久的訴求。這場佔中,不是示威,而是吶喊,是悲鳴,是怒號。
也許,小城隔岸觀火,不以為然。百步笑五十,只因有幸庫房甚豐,攤分少許不知來自何地的民脂民膏,取悅大眾,方有冷眼嘲笑的餘地;然而,細心一想,小城情況,或比鄰埠更糟,至少連抗拒「袋住先」的意識也沒有;因為小城(恕筆者直言)充斥着更多活像魯迅筆下「奴隸總管」的嘴臉。這些狡猾總管,從奴隸中選出來的一些順民。每當有主子視察,總管便起勁地用鞭子鞭打自己的同胞,以示對主子忠誠。
任大雨灑下,佔中人士也不忘初衷,依舊席地而睡,留守街頭,無懼被捕、被抹黑,甚至受傷,繼續鼓起勇氣,於公共空間中尋一片海闊天空;然而,面對着年青公民的義無反顧,總有一群甘於向權貴獻媚的人,不分青紅皂白,但求「著數」,不惜以身犯險,推倒鐵馬,高空擲物,呼喝佔中人士,搗亂鬧事,有相為證者可獲重酬,簡直無所不用其極。人類劣根性,又一次淋漓盡致活現眼前,如文革般的批鬥和分化,一如魯迅小說《藥》中,人民麻痺了的良知,相隔了一個世紀,依然如是,絲毫未有反思,依舊有愚民因「血饅頭」蜂擁而至,看那反佔中人士、圍堵香港某報章辦工大樓門外的壯年人、那埋沒良知、抬不起頭的冷漠與愚昧,與昔日以「血饅頭」治病無異。人民的無知與革命志士的犧牲,仍不斷地重複著。究竟,大眾的公民素質,還要等多少個世紀,才能像中國航天工程般踏出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