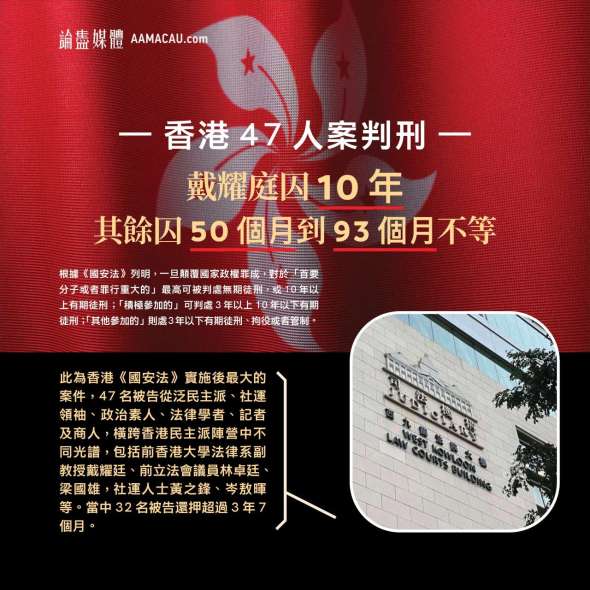二零一四年十月三日 陰
這是我來到旺角街頭的第二天,對現場形勢仍是不太懂得掌握。
從亞皆老街轉個彎,就進入了那條長長的彌敦道,兩條行車線都已因佔領運動而被警察封鎖。那時大概八時多,留守的市民人數其實不多,但散佈在路上。連日來手機短訊、網上消息都叫我們「慎防黑社會」,或「小心六七暴動後的縱火事件會重現」,那刻我在想:為何還是有人不怕死,單人匹馬前來靜坐?
偶爾我在佔領區也會遇上朋友,其實我們都膽戰心驚,因為香港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了。今天的新聞報道才剛說有反佔中人士非禮女學生;在直播新聞裡,我們也眼白白看著指罵他人的反佔中人士站在包圍圈內絲毫未損,和平示威者卻被警方粗暴推走,當中還包括身穿校服打呔的中學生。
朋友也向我轉述他被反佔中人士無理襲擊的過程,一句「你影咩呀你!」便把他的手機摔壞、自拍神棍屈斷了。「嗯,還好,你人沒有事。」我眉頭皺著,因為我更在意他憶述當時的序幕:一名初中生從彌敦道往大台方向拼命地向前跑,後面有數名藍絲帶的人追著他,後來便不斷發生示威者被打的事件了。
當天晚上,我在兩條行車線之間不斷看到市民包圍滋事份子,雙手舉起,呼叫:「咪走!」、「警察拉人!」以及「除褲!」附近雖然有大批便衣警員戒備,卻沒有人前來處理場面。且慢!除褲?為何他們叫除褲了?原來,那些挑釁佔中市民的人,被群眾包圍後,就只懂發難,不斷說髒話:「咩呀?打(數字)我吖!(動作)你(媽媽)!」香港市民為一賭他的氣焰,於是力邀他脫下褲子。當然,這種以退為進的戰術成功令挑釁者節節敗退。
我欲跟蹤便衣警察,起碼從旁聽聽聊說電話,看看他們的會合地點在哪,卻沒甚發現,只好跟朋友在太子到油麻地的範圍巡邏,但回到佔領現場,氣氛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回到家樂坊的十字路口。只見多位男士,年齡從十幾歲到五十幾歲,人數多得令人很懷疑,「唔通今晚真係會開片?」朋友問我,「不知道,我每一天也無法看透。」我答。
突然,有一台黑色私家車停泊在我們身處的十字路口,數名警察上前調查,只見該名叔叔十分鎮靜,甚至任由警察上車檢查,最後確定「車輛無故死火」便離開了。「係咁㗎,每晚旺角都有班司機落黎,落到黎架車就會死左火,幫我地block住啲路㗎,之但係佢地係咩人呢? 我地就真係唔知喇。」朋友解釋說,我立即追問:「吓?但係佢地點樣整到㗎車死火呢?仲要唔係廢車喎,我見係靚車!咁都肯呀?」朋友笑而不語。所以說,香港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了,什麼資本主義,什麼中環價值,現在好像也為人民服務了。
凌晨十二時多,我們往亞皆老街的方向走,天降下大雨來,沖散了馬路上佔領的人群。記得黃色暴雨的那夜,我在中環看到無數留守的人因大雨而離開,我不得不失望地想舊景可能重現:「唉,又落雨喇,可能好多人會返屋企喇。」然而,事實卻是,一陣子雨後,反而更多人出來了,而且是更多男人出來了。他們站在路邊,站在地鐵隧道頂上、電話亭上,每個都像準備好作戰的感覺。
我們在雨勢大時,趁人群離開所以走到了前方,當時警察已與民眾相隔兩方,我們也不得越過防線,只可以默默跟警察對望。期間,左邊街口不斷有市民高呼:「警察拉人!警察點解唔做野!」站在我前面的警察叔叔,沒有一人移動,甚至別過臉去。
他們的漠視惹來民眾的憤怒,我身邊的哥哥、叔叔、伯伯都群起質問:「警察!嗰邊有人打人呀!做咩你地唔做野呀!」、「我交咁多稅俾你地做咩呀?!」、「影吓你地班佈景板先!」、「係咪依家香港冇警察喇!」、「我地唔會再信梁振英啲語言偽術㗎!TVB都唔會播真相㗎!你地同我地一齊啦!警察罷工!」此時此刻,我才發現,周遭已沒太多女士,一整個街口堆滿了人,但每群人裡女性的數目不足十個,真的會有黑社會搞事嗎?分不清何為邪鬼何為神,我既緊張又興奮。
群體裡有一位光頭叔突然挑釁爬上燈柱綁橫額的義工們,他失心瘋地連續使出「(動作)你(媽媽)」三次,然後問他們在「綁乜(數字)嘢」。直至這刻,我才知道,敵人就隱藏在我們四周。我以為會發生肢體衝突,卻出奇地,香港男子組(綁橫額的義工們)全場沉默了十秒,任他疾呼「(動作)你(媽媽)」。那班男生都板著臉,其實以他們的體型和人數,足以圍毆那位放棄治療的光頭叔,只是他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唔!好!理!佢!繼續綁!」、「唔好俾佢挑釁呀!」上一輩開口了,年輕一輩便動手,三名香港年青新力軍出現,在光頭叔叔面前圍了個半圓形,雙手交叉環在胸前,然後默站。他們甚至眼睛都沒有直視他,就這樣默站,最後迫使光頭叔落魄地離開。
「老婆,你唔洗驚,我會保護你」,忽然我左手邊傳來這說話,我轉身看看,原來是馳名中外的MK少年,他手挽著「老婆」與我一樣站在前方,「如果唔係佢地今日打學生,我諗我返咗屋企吹冷氣」他說。「我都唔知點解今日個女學生唔一樣踩落去個男人度!」他老婆回答。後面的叔叔搭訕說:「唔得㗎!你地啲女仔唔夠力㗎!」女生回應道:「得㗎!一隻腳就夠喇!」叔叔笑說:「好,咁你地得閒自己兩個練習吓啦。」
我笑了,所有的不安一掃而空,更添了一份莫名奇妙的安全感。
儘管警察在人前拘捕了那班挑釁和襲擊和平示威的學生、市民,卻又會把他們放走,任由他們在人群間、不同的地鐵出口穿梭,繼續消耗民眾體力,於是我們把他們比喻為「班烏蠅亂咁飛」。於是那天晚上,我們都在捕捉「烏蠅」,每次只要看到一隻,就會有一群市民高舉雙手,用身體包圍他,追足九條街,情況宛如Occupy Central的時候那張1% v.s. 99%的海報。
我曾經反對「香港已死」論,因為真正的死人根本不會說話,不會高呼「香港已死了」。如果是死,香港也不過是在經歷假死的狀態,如同研究假死的學者Mark Roth所說:「假死是一種暫停生命的過程,然後重啟的藝術」。
催淚彈已震撼了我們的心,警棍已敲醒我們的靈魂,我們現在聽到心跳了,醒來了,也因此而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