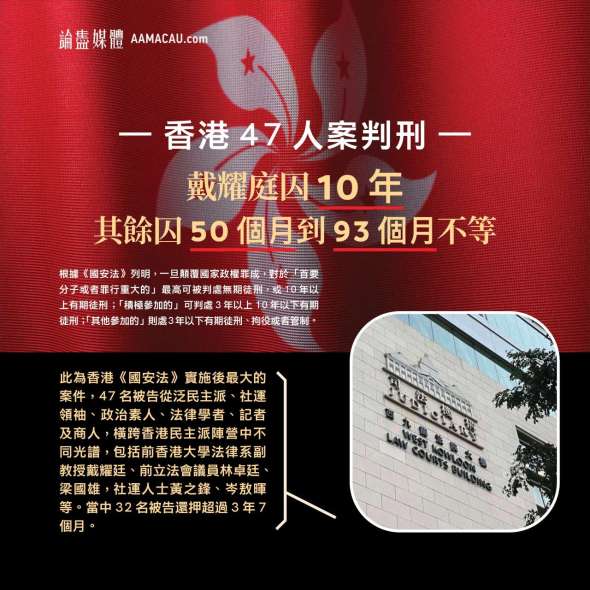我沒有經歷過你們的火紅年代,甚至是天星碼頭、反世貿、皇后碼頭、反高鐵,我都錯過了,但我沒有辦法重來。
整場運動到現在,我都積極地跟不同人聊天,因為我對你們的香港很陌生,甚至是空白。特別是當我們打算死守,人們會勸我們撤退,我更感覺每代人對香港的情感記憶和社會經驗不一樣。從前的香港是怎樣的? 為何後來我的中學會因為普通話教學而被罵成「紅底」?究竟施放催淚彈的晚上,你們想起了六四的什麼?去遊行總會看到很多人舉起港英旗,但英殖時期社會狀況不是很壞嗎?究竟香港是什麼?我認如何理解英國和中國跟我的關係?為何我們之間好像有個斷層?那是怎樣造成的?
我這個愚昧無知的花o靚仔能從書上閱讀歷史,卻無法理解你們的情感包袱。但或許這樣,我們才能以理性批判歷史,然後選擇向前走。而新媒體興起後,我知道新一代的年青人將比我這一代有更多選擇,更能接收多方面的資訊,更能與不同人討論,而非像我那樣「死讀書」、人生就只有升大學。然而,McLuhan 的一句「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警惕著我我,每當一個新媒介出現,社群的生活方式也將改變,我們也得思考這個媒介延伸了什麼、淘汰了什麼、帶來了什麼、過度延伸又會怎樣。
於是這場運動中,我再反思媒介對社會的影響。一部智能電話、一堆apps 令我們興起有即時消息,也開始研發了可攜式充電器,但運動期間的消息卻因而變得雜亂無章,甚至被人用以發放假消息。智能電話也令我們的社交方式改變,但電源被切斷、網路被干擾,我們就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人。這段時間,佔領區出現了人傳人的消息發送方式,也有多個平等的討論小組。縱使我不過是個花o靚仔,分享自己最深刻的香港事件只有沙士一件事,但他們都樂意聆聽,並跟我說更多香港的二三事,他們的小論述是任何一本書、任何一個網站也讀不到的,怎樣與人溝通、作出理性的討論,也是必須練習的。
「每一晚都是最後一晚,every night is the last night。」每當入夜,你總會聽到不同年代的香港人這樣說。如果當初我順著社會設定的理想路線走,我猜我不會發現我們整個香港群體之間的裂縫。Leonard Cohen 曾唱過:「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萬物都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群體間的裂縫,就是我們溝通的契機;每一次的溝通,成就了一場場豐富的交流。我們互相交流成長的故事,也築成了香港不斷延展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