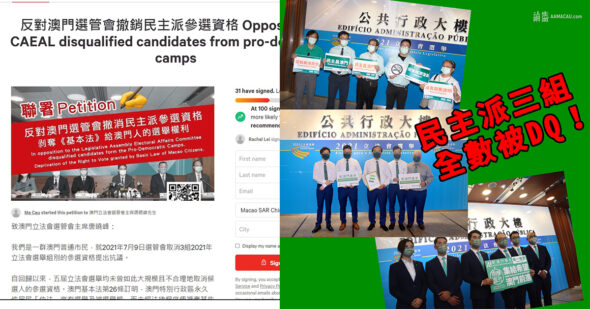上個月,與一位友人閒聊天下事,那時候,立法會選舉落幕不久,民主派失利、商界民粹政團崛起、年青人冷待選舉,都令大家不約而同地感到一點惆悵,也開始進入思考澳門社會未來發展的話題。我們分別來自兩個相距不太遠的世代,但各自在那個世界和那個社會裡的成長背景卻大有不同。
友人回憶開始懂事的當年,正值全球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同時也即將步向尾聲,分別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進行軍事、科技、核武等不同範疇的大規模但非直接的對抗,雙方為了極端不同的政經運作模式而長期對峙,直至全球多個共產政權陸續崩解,資本主義陣營某程度上取得勝利。世人對資本主義充滿熱切期望和無限幻想,甚至有人一口咬定馬克思的靈魂已經煙消雲散之際,友人選擇赴台灣升讀大學,親身目睹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時刻,民間社會風雲色變,歷經幾十年白色恐怖和戒嚴的台灣人,終於能夠初嘗人民當家作主的「神奇」滋味,大家對西方那套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樣充滿美麗的想像,甚至對自家人多年來「勿通匪類」、排除社會主義的堅持深表肯定。友人形容,他成長在一個充滿希冀的年代,儘管在澳門,多數中學老師也會建議學生優先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大學科系,極少人會膚淺得認為只有讀商科才會賺大錢、才是有出色。
聽罷,我笑了一笑,原因是那個充滿希冀的年代似乎已一去不復返,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身處的世界和社會充斥的事物幾乎都較為負面。猶記得,我逐漸懂事的那些年:某天的晚飯時段,電視突然插播特別新聞報導,紐約的兩座高樓被飛機撞擊,人們隨即慌忙逃生,甚至不惜從高樓一躍而下,不久高樓灰飛煙滅,眼前盡是哀鴻遍野的現場畫面,「恐怖份子」這個標籤第一次紀錄在我的認知,隨後便是美軍針對阿富汗發動的一連串戰爭,恐怖襲擊、自殺式炸彈爆炸、炭沮粉末、防毒面具、人質斬首、雇傭兵……這些名詞充斥在當時報章的國際版面,我就是在那個亂七八糟的時刻展開對國際的初次認識。以巴衝突、沙士爆發、南亞海嘯、伊拉克戰爭、佔領曼谷機場等等,鞏固了我對這個世界的印象,無論是天災、戰爭、族群衝突、疫症,總之我當時的刻板印象就是「世界很亂」。至於,在澳門呢?沒有天災、沒有疫症、沒有動亂,大家都認定這是一片「蓮花寶地」,記得首家外資賭場開業當天,墟冚的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身邊認識的親友紛紛排長龍、遞求職信,但求人工高,當中有不少寧願放棄學業,自此,越來越多澳門人穿金戴銀,享受著豐富的物質生活,曾經覺得「做澳門人都幾好」;不過幾年過後,我便深知那是個美麗的誤會:某天,又是晚飯時段,從香港的電視新聞得知歐文龍被登門拘捕,後來麗都天橋下驚動全澳的五下槍聲,還有金融海嘯的撲撃,路氹城工程相繼停擺,打爛不少基層工人的飯碗,對金融財經一竅不通的我,也知道有對不可靠的雷曼兄弟,這一切,伴隨著我過去的社會化階段。以如此角度去認識社會,算是這個世代的悲哀嗎?
正如友人所說,當他踏進社會的時候,年少時的美好願景相繼幻滅:「99%」人民起來反抗資本主義,西方民主制度下,也發動了接二連三的「正義」之戰……那種連環的破滅感不單使人心灰意冷,也令他產生一絲不安,擔心餘生只能看著這個世代的崩壞而無力挽救。相反,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某程度上是身處谷底,感覺自己一出生便對世界和社會沒什麼希冀,儘管有,也只不過是瞬間消逝的。許多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傳統既有價值陸續遭受挑戰和鬆動,勢必掀起世代與世代、保守與前進等不同價值觀之間的論辯與對決,或許這也是大崩壞前夕力挽狂欄、絕處逢左疑鶬銈刉驉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