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花》劇照一
「如果我現在能飛起來,我可能會感覺好一點。」這是Kyo Maclear繪畫關於小說家伍爾芙人生故事的《小狼,不哭》其中一頁。飛起來,也是由李卓媚導演的紀錄片《棉花》最後的畫面。精神疾病走向的死亡,是對飛翔與自由的企求(如伍爾芙),而此外,生的救贖在哪裡?有沒有我們可見到、可履行的真正自由之地? 木棉樹是澳門常見的路樹,疾病、女性、家族、個人,與城市命運,是《棉花》裡的主題。

《棉花》劇照二
影片的開始,晃動扭曲的畫面、被放大的阿姨肌膚,以及講述中的疾病狀態,突顯出精神疾病患者在澳門被避而不談的情況,例如阿姨說到疾病被忽視的痛苦:因心理導致的身體痛苦,就不存在,因為「不存在」,所以也不存在原因與康復。 但阿姨實實在在地,進了九次醫院,也不斷服藥,甚至曾瀕臨死亡。而誰面對了這些?唯有她的手足妹妹。 像是一個迴圈一樣,我看見影片裡三位女性作為彼此的支柱與療傷的對象,她們是充滿著溫柔、自責、對自己的人生無法掌握的女性。這種互相支持,形成了很不可思議的力量。即使是這樣,她們在整個「被看不到」的家族和社會裡,依然充滿創傷,阿姨和媽媽,以那是一種不能逃避的命運活下去,儘管是光華盡散,在彼此的眼中依然活得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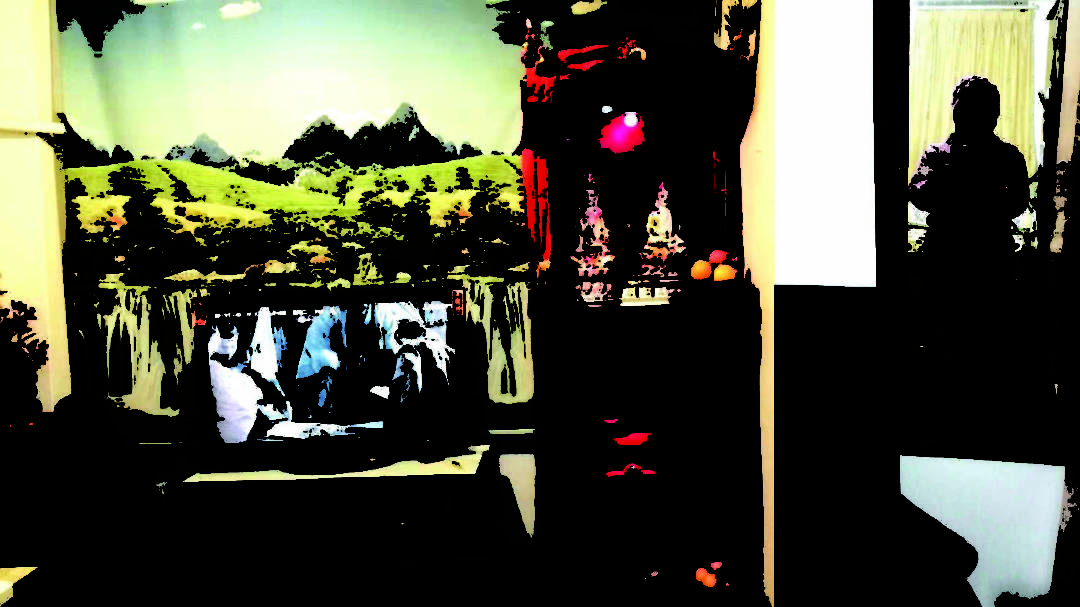
《棉花》劇照三
但身為下一代的導演本人,也是如此嗎? 在開通的大橋,那麼小的人物,著實與時代相連。她們擁著彼此,為終於能離開疾病的陰影而走向遠方的家人鼓勵。這座大橋、這個時代,或與她們身為同時代的你和我,會是疾病背後的支撐嗎? 此時,我聽到幼孩的哭聲與奔跑。在觀眾們節制卻又無法控制的噓聲與辱罵,想起方才在影片中,阿姨叨叨念著自己從前多不喜歡小孩的事:「小妹,我今天想起你小的時候,其實你小時候很可愛,所以阿姨才這麼喜歡你,才重新喜歡小孩。」「那個時候的你,真是天真爛漫,非常開心可愛。」「不知道遇到了甚麼事情,導致你慢慢不開心,從前開心和天真的樣子,阿姨都沒有再看過。」觀眾,始終是戲院裡的人,不是走進電影裡的角色。
影片結束之後,我往車站走去。看見方才的孩子們,原來是SEN熟悉的家長與孩子們,他們匆匆離席,那位媽媽為了爭取一再被政府跳票的特殊孩子津貼連署,一個人在園遊會的人群前方站了好幾天。 我能理解被精神病或特殊疾病打擾的社會,但在大橋(集體利益)上方,誰能支援到這樣一個……幾乎無聲的群體? 我頓時明白到,觀眾裡任何一個人,都依然只是在觀看他人之事。如街邊木棉「身如柳絮隨風擺」,或是機艙窗外的白雲,不幸或幸運,都與我們沒有關係,在秩序之中,大時代的榮善也未曾解救。 「我自己覺得,也聽別人說,童年情緒受虐待,不開心藏在心底,無法抒發,隨著成長累積,負面情緒不斷加深,去到某個程度,身體和思想會承受不住,就會有這個病。」這是阿姨疼愛阿妹而出現的,關於精神疾病與童年情緒虐待關係的意識,她是從回顧阿妹的可愛與成長得到的結論,卻也是一段對全體觀眾發出的警語。
在巨大的時代政策之下,我們正在對下一代人做些什麼? 最後,回到《小狼,不哭》。《小狼,不哭》是Virginia Woolf與姊姊凡妮莎的手足故事。但其實Virginia一直受憂鬱症(其實更偏躁鬱)所擾,家姐就係阿妹一扇看到世界的窗:《棉花》中這對姊妹,是這個情感支援的迴圈裡,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本片卻避而未談。如果家族的主題依然是李卓媚繼續拍攝的主題,這個角色將會是非常明亮之處。









